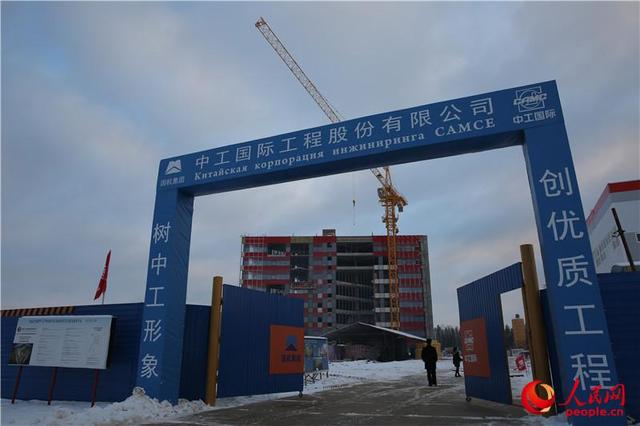作者:一湖,来源:唐诗宋词古诗词(ID:tsgsc8)
他出生于1021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有心人将这个日子换算成了阳历,即十二月十八日,也就是说,到2021年12月18日,这位老人就整好满一千岁了。虽然他只存世六十六年,但是其思想、行为,对千百年之后的今人影响,依然深厚。
细数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对一个人的功过评价最为两极分化的,唯此公一人。后世梁启超先生曾谓之曰:“旷古完人”,现代学者谓之“毁誉参半的改革大师”……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他就是在北宋积贫积弱局面里积极改革变法,却最终黯然离场的临川先生,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
01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小诗流传千年,家喻户晓,是王安石首次出任宰相,着手新政之时所作,这万象更新的气息,不仅是新年即感,也是变法伊始的新气象。
王安石变法中最著名的就是“青苗法”,有点类似我们现代提供给农民的信用贷款;“市易法”则是由政府直接收售物资,参与交易,以平易市场物价,很像现代国企雏形……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不仅改了祖宗法度,还奇想连篇,他这些想法都太超前了,当世人大多理解不了。用现代目光来看,王安石的头衔还可以多一个:务实的“经济学家”。
王安石的所思所想已然超越了时代,也受制于时代。虽然是为国家生利,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但是儒家思想下,文人谈理财是可耻的,因此反对声音巨大,保守派以司马光为首,还有我们都知道的苏轼苏辙,但最初,苏轼兄弟是赞成变法的,只是后来发觉王安石与他们想法有差异,或许更确切地说,苏轼是温和改良派,讲求稳健,他认为王安石大刀阔斧,殚精竭虑虽可敬,但步子跨得太大、走得太快,容易扯得到处生疼,反而影响民生。
神宗在位十八年间,对王安石非常器重和尊重,君臣同心,推行变法,成就中国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相互欣赏、充分信任的君臣关系,虽然迫于压力,一度罢相,但是对王安石的关心丝毫未减。他深知,换个人到王安石的位置上搞变法,也未必有王安石干得好,只不过做实事的人被千万只眼睛盯着看,容易被挑错和指摘。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变法者历来下场都不太好,前有商鞅,后有张居正,到近代戊戌变法亦是如此。王安石还算有善终,死后赠太傅,谥号文,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后又配享孔庙,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政治的变迁,大宋成了南宋,宋高宗想甩锅找个替罪羊时,追溯、迁怒到王安石变法,不仅将其撤出宗庙,还成了千古罪人,至其身败名裂,差一点就编进了奸臣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虽然政见上针锋相对,一个是“拗相公”(民间给的绰号),一个是“司马牛”(苏轼给取的),都是倔脾气,但为人原则上没有不同,轮番上台并不对政敌落井下石。王安石默然去世后,情形非常惨淡,因已失势,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司马光站出来提议赠太傅,这是朝廷给予的极大肯定和荣誉,撰写这个文件的,正是苏轼,苏轼充分肯定了王安石是个“能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才,是个能改变风俗的伟大人物。”
苏轼在“乌台诗案”性命堪忧时,王安石也曾出手相救。旧党上台,苏轼返回朝廷途中折道金陵,看望这位曾经的老宰相,王安石骑了他那头众所熟知的小毛驴前来岸边迎候,苏轼穿着一身布衣而来,为自己身着便装见大人而致歉,王安石哈哈大笑:“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设?”两人互相敬重对方人品,也欣赏对方诗文,共游山水多日,饮酒唱和,成为一段佳话。
如今看来,这一届大人物都是忠心为国为民,不掺杂个人恩怨,一派君子之风,又都是那么才华横溢,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千秋功过,我等亦难以轻论,但不可否认王安石是一代杰出大才,必有后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闪光点——

02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宋仁宗皇祐二年夏天(1050年),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返回江西临川故里,途径杭州时写下此诗。这时他三十岁,眼界已是在“最高层”来俯瞰世界,这种全局观使其胸怀广阔,有雄心壮志干一番大事。
王安石二十岁进士及第,中第四名,好友曾巩从欧阳修处得知王安石本是状元,上呈仁宗御览时,仁宗对文风刚硬的文章不甚喜欢,因此和第四名对调了。王安石根本没把这当回事,终生不曾宣扬,他的关注力,都在做实事上,甚至不在乎官级。他二十岁中进士,三十岁还在做县令,并不是没有进京做官的机会,只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理由都是:还未安葬家父回乡;上有老祖母要奉养,不便远行;家里兄弟姊妹人口多,京城生活成本太高……这些理由的确很充分,另一方面,他第一任官衔曾是一个闲职,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而进京做的文职官也一样是无法施展心中的抱负,因此他宁愿去最基层做一方父母官,放开手脚实施他思想的“试验田”。
就在这任鄞县知县期间,他按心中设想做了几件实事:兴修水利、预演青苗法、兴办学校。换成现代方式看,他主抓了三件大事:基建、金融、教育。这个不寻常的县令吃苦耐劳,干得风生水起,把自己管辖的一方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
任期满后,直到47岁拜相的十七年时间里,王安石数次婉拒朝廷的任命,理由都是家里困难多,婚丧嫁娶等等照顾家族的事务缠身,难以入京赴任。拒绝的次数多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被人误以为沽名钓誉实在有悖内心,在欧阳修的劝说下接受了群牧判官一职。群牧司相当于现代的交通部,当时长官是包拯,同僚有司马光等,都是正人君子,大家相处愉快,这是一段比较闲适的日子,后人笔记中许多王安石只知读书、不修边幅的书呆子趣闻都出自这一时期。
工作轻松、俸禄丰厚的官职是多少人羡慕渴求的,却不是王安石想要的,他要的是做大事而不一定谋大官,因此不断上书请求外放。他始终清楚,大处着眼,必须小处着手,实操起来才能获得真知。
在地方上积累了实干经验后,王安石变法的思想体系逐步成形,神宗即位后召他进京“越次入对”,相谈时政看法,拉开了变法序幕。王安石登上了最高人生舞台一展抱负,一如他年轻时登高望远的雄心万丈。

03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改革变法在风云中落幕,王安石抱憾退居江宁,作了这首梅花诗。冷清的墙角,不畏严寒的梅花独自盛开,暗含幽香,这种孤寒高洁的品行,也是诗人内心的操守。
同一时期还有一首《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杏花本是一种极为普通且有些艳美意味的花,却在王安石笔下有了不寻常的光芒,他把自己的心志咏在其中,也使我们从中领略了他不凡的见识和气度。
作为改革家,古今对王安石看法不一,但作为文学大家,几无异议。王安石对待诗文,与对人对事的态度一样严谨认真。他在二度拜相启程赴京时,有过一首著名小诗《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春风的“绿”字,给整首诗画龙点睛,成了千古传神的一笔,让人暗自叹服。据史载,他当时的手稿流传了下来,这句诗边上圈圈点点有很多字,有“到”、有“过”,凡此等等,推敲程度不输贾岛,最后定了这个“绿”字。这种一字较真是王安石的日常,比如他对南朝诗人谢贞的《春日闲居》不满,认为“风定花犹舞”不符合事物规律,风都停了,花还能在空中舞吗?于是改为“落”字,没有风,花是自然下落的。可惜王安石没有继续往前再进一步思考,不然就没有600年后牛顿什么事了——当然这是说笑。
王安石改了谢贞一个字后,又从南朝王籍《入若耶溪》中找了一句接上,浑然天成:“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流传下来以至于后人早忘了原诗,只记得这一对天衣无缝的佳句了。王安石晚年用这种集句的方式作了不少集句诗,非常巧思。现代网络上也有各种脑洞大开的古诗拼接,但今人还可求助电脑程序而古人全凭学识积累,没有渊博的学问功底,绝无可能信手拈来,又恰到好处。

04
王安石既品行高洁,又学问深广,他是如何长成的,他的家庭,他的人生初期,对他有怎样的影响?他一路走来,烟火生活里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的?我带着这些问题在史料与诗文中进行了寻找。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21岁进士及第,开始流转各地为官。王安石是王益与第二任妻子吴氏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任妻子早逝,留下两个儿子。吴氏对两个孩子视如己出,后面几年,王安石的四个弟弟三个妹妹相继问世。一大家子相处融洽,给了儿时的王安石很好地孝悌仁义的教育,因此父亲英年早逝后,王安石担负起家庭责任,人口众多,不便于去京城做官也是实情。
母亲吴氏品行端正,知书达理,做事很有主意,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比较严格,父亲王益则和蔼可亲,经常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做游戏,说故事,寓教于乐。这样相对轻松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积极影响的。
妇孺皆知的一篇古文《伤仲永》,是王安石少年时有感而作,深刻认识到即使有天赋,后天也得努力学习才能发展天赋之后,他更加认真研读大量典籍,并不局限于儒家,而是博采众长,独立思考,形成了他最初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王益做了二十几年地方官,直至46岁死在任上,他是个有主见的官员,非常注重民生,也颇有政绩。王安石从小跟着奔波为官的父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体察到了各阶层百姓的生存实况,对他以后的思想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母一生相守,共处和谐,也给了王安石正面的影响,他23岁与表妹吴氏(母家亲戚)成婚,终生一夫一妻,妻子给他买来妾室也被他退了回去。他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也如父亲当年那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女儿出嫁后,写信来诉说想家,他回诗安慰:
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
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
还曾写过古风长诗给两个女儿化解忧思,《寄吴氏女子》(大女儿嫁给了吴安持),《寄蔡氏女子》(二女儿嫁给了蔡卞),诗句充满慈爱深情。在外刚冷的变法宰相,内心竟是如此温情细致的父亲,可亲可敬。
我在文字里读出了一个活生生平实的王安石,荆国公,字介甫,晚岁号半山,儿时小名獾郎。卸去他身上所有的标签,暮年寂寞的半山先生,曾是一往无前的赤子,欢实奔跑的獾郎。
-作者-
一湖,一个热爱诗词的简单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