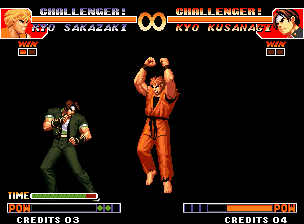围绕李清照晚年被迫再嫁,随即又涉讼离异的不幸遭遇,从宋代开始就对其真实与否各执一词。今人何广棪曾将历代文献裒辑为《李清照改嫁问题资料汇编》,多年后又稍事增补,收入潘美月、杜洁祥主编的《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九编,成为迄今为止最可倚重的专题文献渊薮。然而在旁搜远绍之际,此书也难免偶有疏失。最近翻阅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女词人顾太清的作品,就读到一首与此息息相关的《金缕曲》,何氏虽然已经将这首词收入《汇编》,称其“旨在为清照改适辩诬”,“语意甚明”,却未能依循相关线索再作追溯研讨。

顾太清为乾隆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多罗贝勒奕绘的侧室,原姓西林觉罗,本名春,字梅仙,号太清,晚号云槎外史,别署西林春、太清春,满洲镶蓝旗人。祖父鄂昌为雍正、乾隆年间重臣鄂尔泰之侄,历任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陕甘总督、甘肃巡抚等,因卷入鄂尔泰门生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一案而得罪赐死。太清为避忌起见,遂不得不冒姓顾氏。顾太清创作的诗词汇编为《天游阁集》,词集部分又题作《东海渔歌》,此外还有剧作《桃园记》和《梅花引》,并为《红楼梦》撰著续书《红楼梦影》。其填词造诣最受时人及后世的称赏推崇,被誉为“巧思慧想,出人意外”(沈善宝《名媛诗话》卷八,光绪鸿雪楼刻本),以至“论满洲人词者,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说”(冒鹤亭《小三吾亭词话》,收入《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将她与纳兰容若等量齐观。这首《金缕曲》见于《东海渔歌》卷四,兹据今人金启孮、金适《顾太清集校笺》(中华书局,2012年)先引录全篇如下(原有小序及自注均另加括号):
金缕曲(芸台相国以宋本赵氏《金石录》嘱题)
日暮来青鸟。启芸囊、纸光如砑,香云缥缈。易安夫妻皆好古,夏鼎商彝细考。聚绝世、人间奇宝。太息兵荒零落散,剩残编几卷当年稿。前人物,后人保。
芸台相国亲搜校。押红泥、重重小印,篇篇玉藻。南渡君臣荒唐甚,谁写乱离怀抱。抱遗憾、讹言颠倒。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记伊人老。千古案,平翻了。(相传易安改适张汝舟一事,芸台相国及静春居刘夫人辩之最详)
奕绘、顾太清夫妇与并世名流多有交游,词中屡屡提到的“芸台相国”,即当时的知名学者阮元。阮元,字伯元,号云台,又作芸台。历官山东、浙江学政,兵、礼、户、工部侍郎,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著有《揅经室集》,并主持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籑诂》《皇清经解》《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而那位“静春居刘夫人”,则是阮元之妾刘文如,字书之,号静香居士。顾太清另有《读芸台相国揅经室诗录》《十一月雪后芸台相国过访,谈云南风景》《五月廿五雨中静春居阮刘夫人招同云林、纫兰过天宁寺看新麦,即席作》《瑶台聚八仙·祝芸台相国八十寿》等,可知彼此往来酬赠颇多,阮元之子阮福的妻子许云姜更是太清的闺中密友,足见两家关系之密切。阮元精擅金石考订,赵明诚所撰《金石录》自然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这部宋本为南宋龙舒郡斋刻本,尽管残损不全,即太清词中所说的“剩残编几卷当年稿”,但递经明清两代名家收藏,流传有绪而颇值珍重(参见钱曾《读书敏求记》、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顾太清应约题词,既反复慨叹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颠沛流离之际依然倾注心力于金石文物的蒐集著录,又着力表彰阮元对这部宋刻残本的细致考订和悉心庋藏,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下阕最末数句及自注,特别提到阮元、刘文如针对李清照再嫁的传言曾经力予辩驳,终于使这桩千古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阮元收藏的这部宋本《金石录》其后几经辗转,在同治年间又归藏书家潘祖荫所有。潘氏在《滂喜斋藏书记》(民国十七年刻本)卷一中详细迻录了书中所附各家题识跋语及诗词题咏,有不少内容都可以和这首《金缕曲》比勘参证。如其中所录太清词,在最后有“俚词呈云台老夫子、静春居伯母同教正。西林春”的题款,仍然保留着当时奉命题词的原初面貌。在正式收入词集后,大概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才删去题款而补撰小序及自注,对原先并不需要明言的创作背景略作交代。而在太清词作之前,潘祖荫又抄录了奕绘的一首诗,其中提到“揅经老人著笔暇,颇有闲情及钟鼎。家藏宋椠《金石录》,故纸不是双钩影”,最后题款为“道光戊戌闰月望日丁亥,应云台相国命题。后学奕绘”,由此推知夫妇二人当年是同时应邀,只是一诗一词,各有分工而已。潘祖荫还称全书“鉴定印记累累”,并不厌其烦地缕述所钤各种印文,其中有近三十枚都出自阮元、刘文如夫妇,数量居诸家藏印之首,可证太清所述“押红泥、重重小印”绝非虚言夸饰。
更值得重视的则是《滂喜斋藏书记》中引录的一则刘文如题跋,其内容主要是根据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着重考察赵、李夫妇生平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后世争论李清照再嫁一事,这篇序言是极其重要的文献。文中提到赵明诚病重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有人甚至猜测这位“张飞卿学士”就是李清照后来再嫁的对象张汝舟。经过仔细钩稽梳理,刘文如推定赵、李两人成亲是双方长辈“同官礼部时联姻也”,赵明诚“卒于建炎三年”,“卒年四十九也”,而李清照“作序之年五十二矣”。她甚至还对序中所述“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提出质疑,认为“丁未三月犹是靖康,五月始有建炎之号,戊申方是建炎之元也”,考察之缜密细致可见一斑。刘文如先前曾撰有《四史疑年录》(嘉庆二十三年刊本),在考校系年方面自是当行出色,而这段跋语虽然由她署名撰作,毋庸赘言也必定得到过阮元的首肯。尽管没有明确涉及再嫁问题,可是经过排比考订,李清照当时早就过了知天命之年,是否确有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确实令人生疑,所以顾太清才会发出“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记伊人老”的由衷赞叹。
其实刘文如所作推断并非孤明先发,更不能称作翔实完备。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明人徐■《笔精》、清人卢见曾《重刻〈金石录〉序》等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过李清照撰《〈金石录〉后序》时的确切年龄,清人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收入《癸巳类稿》卷十五)更是对赵、李生平做过巨细靡遗的钩沉索隐。不过考虑到顾太清应邀题词的特殊情况,对她称道阮、刘夫妇“辩之最详”也就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了。倒是何广棪在辑录《李清照改嫁问题资料汇编》之际,虽然注明系根据《滂喜斋藏书记》收录了顾太清的这首词,却令人费解地并没有同时收录更为重要的刘文如跋语,不知为何会厚此薄彼?究竟是一时疏忽而失之眉睫?抑或是未见原书而辗转抄录?

顾太清三十岁画像
顾太清对李清照的坎坷遭际深表同情,对再嫁说则显然是坚决不予采信的。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金缕曲》中所云“讹言颠倒”的情况居然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此事缘起于晚清名士冒鹤亭所写的一组《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收入《小三吾亭诗》卷三,《冒氏丛书》本),其中一首说道:“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前两句均有自注,指出“太平街”为奕绘、顾太清夫妇府邸之所在,“南谷”则为两人逝世后的合葬之地;第三句用“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典故,赞叹太清的风姿容貌并暗示其姓氏;最末一句虽然并未直言,却暗中牵扯上嘉、道年间的著名诗人龚自珍。龚氏《己亥杂诗》里有一首:“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其二〇九)自注称:“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冒鹤亭所云“丁香花发一低徊”即隐隐扣合龚自珍所述“太平湖之丁香花”,令人不禁联想到居住在“太平湖畔太平街”的顾太清。
冒鹤亭随后又着手校订评点顾太清所撰《天游阁集》(神州国光社,1910年),在卷首弁言里提到“少时闻外祖周季贶先生星诒言太清事綦详”,表明自己所言都渊源有自,绝非信口开河;接着便津津乐道自己“刺取太清遗事赋六绝”,得到过前辈沈曾桐的嗟叹称异。而在评点过程中,他又屡屡将龚、顾两人牵合在一起。比如有一首《六月十五日东山苗道士寄来七寸许小猴一双,每当饲果,必分食之,似有相爱意,诗以纪之》,冒氏有评语称:“此亦长安俊物也。”乍读之下让人莫名其妙,实则仍与龚自珍相关。就在上述那篇《己亥杂诗》之后,紧接着便有这么一首:“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其二一〇)龚氏自注中明言这是“忆北方狮子猫”之作,和太清诗中所咏“七寸许小猴”显然了不相干,冒氏所作评议实在有些胡乱截搭的意味。不过龚自珍的诗文自晚清以降便风靡一时,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中所言,“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所以冒鹤亭这些模棱两可、含混暧昧的评语,很容易引导读者勾起对龚诗的记忆,进而产生联翩的遐想。在此之后所谓“丁香花公案”便逐渐流播于世,认为龚、顾二人曾经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情史,甚至牵强附会地断定龚自珍最终暴卒于丹阳县署,其实是被获悉内情的奕绘派人追杀所致。
正在流言腾传众口、愈演愈烈之际,清史学家孟森写了一篇《丁香花》(载1913年《时事汇报》第一期),开宗明义就宣称“余之所以有此篇之作,冀为昔人白其含射,以留名士美人之真相者也”,希望经过深入周详的爬梳考辨,替龚自珍和顾太清洗脱污名。他逐一甄别辨析奕绘、顾太清和龚自珍的生平行事及诗文作品,强调奕绘夫妇“伉俪之笃,两人集中互见之”,“备见家庭之乐,琴瑟之好”,又指出“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而龚自珍恰为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由此对“丁香花公案”的立论依据提出诸多质疑。比如就事发时间而言,在龚自珍创作《己亥杂诗》的前一年,奕绘已经因病去世,“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臆断龚自珍曾遭到奕绘的追踪毒害,无疑是荒唐诬枉之辞。而奕绘去世时“太清已四十岁”,“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荡检之时”,当事双方都已年逾不惑,揆情度理恐怕也难有放纵逾矩的行为。再就事发地点而言,顾太清在奕绘去世后因家庭纷争早已搬离太平街府邸而移居别处,因此龚自珍所说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显然别有所喻,“诗自忆花,乃与其人无预”,绝不能凭空指实为顾太清。可惜孟森的苦心孤诣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丁香花》一文后被收入《心史丛刊》(大东书局,1936年),孟森在文末追加了一则附记,提到冒鹤亭曾特意来访,“至太清事迹,冒君谓无以难我,然终信其旧闻为不误”,对这件子虚乌有的“风流韵事”依然坚信不疑。
冒鹤亭在校订顾太清作品时依据的底本并不理想,据他在神州国光社版《天游阁集》的弁言中介绍,“凡诗五卷,缺第四卷,词四卷,缺第二卷,中多割裂,盖当时未经写定之本”,所以最初出版问世的仅是诗集部分。词集部分经他钞校考评,又转而托付给词学家况周颐。尽管暂时无法访得缺失的部分,况氏还是竭其所能钩稽了数篇佚作补入其中,并在数年后以《东海渔歌》之名另行付梓(西泠印社,1914年)。对闹得沸沸扬扬的“丁香花公案”,况周颐在《〈东海渔歌〉序》中也有过一番不曾指名道姓的评论:“末世言妖竞作,深文周纳,宇内几无完人。以太清之才之美,不得免于微云之滓。变乱黑白,流为丹青,虽在方闻骚雅之士,或亦乐其新艳,不加察而扬其波;亦有援据事实,钩考岁月,作为论说,为之申辩者。余则谓言为心声,读太清词,可决定太清之为人,无庸龂龂置辩也。”所谓“乐其新艳,不加察而扬其波”者,说的应该就是冒鹤亭;而“作为论说,为之申辩者”,自然是指孟森而言。在况周颐看来,藉藉人口的流言蜚语不过是颠倒黑白的恶意毁谤,通过绎读太清词作就足以令人确信其品性,根本不需要再作任何争议辩论。
况周颐整理顾太清词集时依据的是冒鹤亭寄送的批校本,可是据冒鹤亭之子冒效鲁在多年后追忆,“《东海渔歌》是我父假抄加注寄给况蕙风,付西泠印社木刻活字本印行。这个抄本多少年后才由龙榆生先生归还给我,从中发现况蕙风竟然把顾太清的词擅自窜改,删掉我父所作考订、评语,连书后的跋也据为己作”(《〈孽海花闲话〉与〈东海渔歌〉〈天游阁诗〉》,收入冒效鲁著译合集《屠格涅夫论漫话雄狮——托尔斯泰浅谈屠格涅夫叔子诗选与知非杂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可知最终刊行的《东海渔歌》经过大量删改,早就不复原貌了。藉此考察顾太清倚声填词的实际情况,固然不免郢书燕说,但若从中体会况周颐修订润饰的良苦用心,倒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趣事。今人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在勘定太清原作之余,就利用冒效鲁提供的资料,“将况氏修删之处一一加以注明”(《前言》),颇便读者参酌比对。比如这首《金缕曲》,“况周颐改动甚大,几已面目全非,甚至连标题及太清原注亦不得幸免”(张璋校语),兹将况氏改作迻录于下(词序及小注另加括号):
金缕曲(芸台相国属题宋本《金石录》)
日暮来青鸟。启瑶函、纸光如砑,香云缥缈。风雅唱随夸漱玉,夏鼎商彝细考。聚绝世、人间瑰宝。几易沧桑悲散落,剩琳琅小束雕镌妙。揅经室,为长保。
相公白发亲雠校。拥书城、玉台仙侣,况兼同好。南渡烽烟惊琐尾,不尽乱离怀抱。更谁究、言妖颠倒。赖有名言为昭雪,按编年、证取宣文老。蝇点璧,净如扫。(讹传易安改适事,芸台相国及静春刘夫人辩之最详)
与顾太清原作相较,有些润饰恐怕纯属辞章角度的考虑,如将原序中“宋本赵氏《金石录》”简作“宋本《金石录》”,将自注中“相传易安改适张汝舟一事”改为“讹传易安改适事”,显得更为简洁精炼,符合况氏一贯强调的“词笔欲求矜炼”(赵尊岳《蕙风词话跋》,载《蕙风词话》卷末,《惜阴堂丛书》本);另如将“千古案,平反了”替换成“蝇点璧,净如扫”,使直率无余的表述变得委婉曲致,也让人想起况氏所标举的“昔贤朴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学养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蕙风词话》卷一)。而有些修订则似乎另有言外之意,如将“抱遗憾、讹言颠倒”径改为“更谁究、言妖颠倒”,和他在《〈东海渔歌〉序》中所指斥的“末世言妖竞作,深文周纳,宇内几无完人”云云遥相呼应,表面看来是在为李清照蒙受不白之冤打抱不平,恐怕也由此及彼联想到顾太清的类似遭遇,隐约透露出他对“丁香花公案”所持的批评意见。
李清照与顾太清相隔近七百余年,竟然都不幸被“绯闻”缠身。尽管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李清照再嫁尚有诸多疑点有待发覆,并未最终盖棺论定;而顾太清出轨则毫无真凭实据,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诋毁,可是两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遭遇其实殊途同归,在不同层面都展现出女性生存境况的种种困顿无奈。正如甘遯(吴昌绶)《陈士可藏本〈东海渔歌〉题记》(载张璋《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附录三)所言,“才媛不幸,大抵如斯。异代相怜,端在同病”,或如启功《书顾太清事》(载《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民智书局,1934年)所悲叹的那样,“其与易安居士相同,不仅才华已也”,超迈须眉的才华非但无助于这些卓异的女性掌控自身的命运,有时反倒成为她们无端罹谤、动辄得咎的沉重枷锁,这才是令人掩卷之余唏嘘不已的恨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