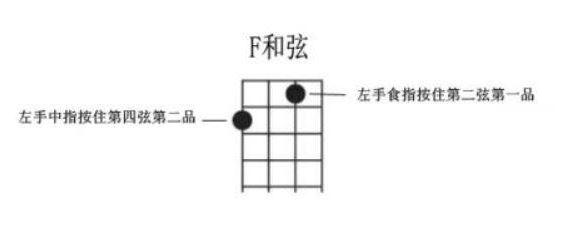都市中存在着流落在街头的显而易见的无家可归者。边缘人群无法寻得自己的安身之处。他们难以找到支持自己生活的经济来源,从而无力承担固定住所所需的经济支出。
除了生活在流浪汉避难所或在街头流浪,承认自己无家可归的人。城市中还有着大量的"隐形的无家可归者",他们可能是沙发客、汽车客、露营者。

他们的居所非永久住房,也无法保证持续居住。
这些无家可归者很难被计入如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这样的官方机构的统计数据中,因而是隐形的。

《弗罗里达乐园》的哈莉一家就是这样的“隐形的无家可归者",住在建于迪士尼乐园附近,因经济衰退而成为边缘人居所的汽车旅馆中。社会学者马修·德斯蒙德指出租赁歧视广泛存在。
社会机能不良者经常被排除在常规租房活动之外,导致他们只能选择短期支付的廉价旅馆。有时,这种非永久性住房的成本比稳定租房更高。

《弗罗里达乐园》中的廉租旅店常客们采取的正是这一住宿策略。哈莉一家还面临了被逐出房间、租金涨价等一系列的窘境。
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是哈莉被迫从“魔法城堡”临时搬走。管理员鲍比为她解释,汽车旅馆不允许住客长期租住,否则会带来相关的法律问题,因此哈莉一家必须每月假装搬出去一次,待到第二天再回原旅馆。

许多作为隐形的无家可归者避难所的汽车旅馆都有这一惯例,这种形式化的清理租客策略是为旅店与长期租客回避法律麻烦的一种手段"。
哈莉带着穆尼走到旁边的廉价旅店,发现这里的房间涨价了,她气愤地请求"魔法城堡"的管理员鲍比来商谈价格。在鲍比与旅店负责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些廉价旅店间会建立协定,双方给彼此的租客一点优惠,好帮助对方的租客顺利渡过"转移期"。

然而,因为管理人员的变更,这家旅店已将协议作废。鲍比愿意自掏腰包来补足差额,但这家旅店仍不愿接受像哈莉这样落魄且粗鲁的住客。
在另一幕中,被哈莉偷走迪士尼入场手环的男人追上门来讨要被盗窃物,鲍比因此知道了哈莉在住所提供性交易服务的事实。

出于管理上的考虑,他要求哈莉的访客必须被暂时扣押身份证,也就是禁止她的外快事业继续运营下去。
与此同时,哈莉发现同一旅馆内的住客都对她冷眼相待,她的旧友艾什莉还用糟糕的嘲讽戳破了她想隐瞒的性工作者身份,哈莉与她打了一架。

翌日,儿童与家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前来调查穆尼的生活情况。哈莉努力把脏兮兮的旅馆房间打扫漂亮,试图在儿童管理局工作者的调查下留住穆尼,但管理局决定穆尼必须被带走。
贝克在访谈中提到,基西米"真实的汽车旅馆内充满了"家庭虐待、药物成瘾和精神疾病""等问题。儿童管理局的工作者基于保护儿童的考虑,经常会介入问题家庭带走孩子。

《弗罗里达乐园》中的哈莉起初从事脱衣舞女工作,被解雇后也无法领到贫困家庭补助。
她倒卖香水给游客、提供性服务、偷窃手环,俨然是个糟糕的城市游民,但她对女儿穆尼有着情真意切的爱,赚钱也只不过为了支撑自己与女儿的生活。为了不失去抚养权,她在与安保人员的争执中把香水全数丢掉,然后背着穆尼回家。

贝克想把一种疑问对准儿童保护机构这样的社会福利部门。影片中的儿童局工作人员虽然使用着文绉绉的、过分温和的语气,颇有条理地进行询问,却完全无法掌握局面。
一名工作人员用一种极其虚假,像是广告般的话术对穆尼许诺未来的生活,被八岁的女孩斥责为“大骗子”。

另一名工作人员请哈莉来劝服穆尼,哈莉立即嘲讽道:让我帮你们把我自己的孩子带走?你的脑子坏掉了吗?穆尼起先是在心猿意马的状态中回应她们的谈话,之后干脆一逃了之。
哈莉在完全无所作为的工作人员面前彻底崩溃。社会工作者们虽然实践着人道主义工作,提供的帮助却有可能造成另一层困境。

这是系统性的支援工作所存在的局限。贝克乐于在影片中设置另一种支援者角色。
例如《弗罗里达乐园》中的管理员鲍比。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给予边缘人关怀。这些支援者与边缘者生活在同一空间,理解边缘者的困境,有些支援者自身也是边缘者。也因如此,他们所提供的支援真诚而有效。

在另一部影片《外卖》中,偷渡者丁明住在一个因众人聚居而极其拥挤,个人空间狭小的房间中。
对于收入有限的打工者丁明而言,“拥有自己住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像是非法的再分隔房屋或共住房屋的非正规住房成了可负担得起的住房来源”。

根据定义的不同,“无家可归者”一词在极度广义的情况下也包括了那些住在低于标准的、不安全的或临时住所内的居民。
但无论使用何种定义,低质量的廉租房与流落街头的现象共存于同一背景下,比如全球化所带来的投机和房地产成本的上升趋势。

贝克的一个计划是通过影片让无家可归的问题更容易被主流观众所理解。他指出无家可归问题的普遍性,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这一逐渐恶化的现状并为改变现状提供动力""。
影片中的志愿者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理想化的行动者。
关注我,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