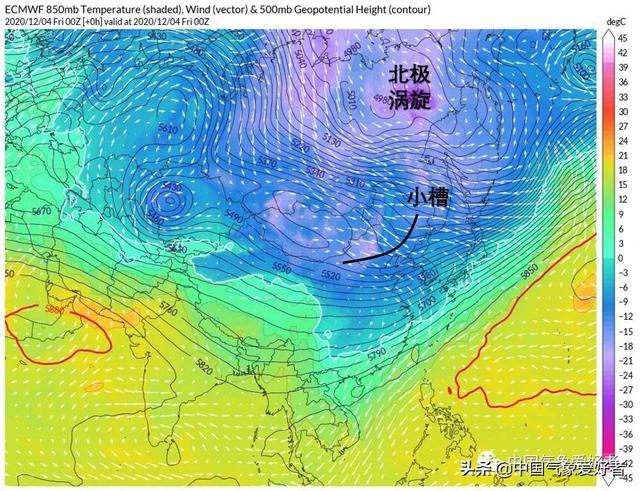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徐利贞先生印象
文、毛晓春
见到的徐利贞先生常常是弥勒佛般充满笑容,但也曾见他有愤愤不平的时候,有次他说,地方有些艺术家私下攻击他说老百姓爱挂他的画,称他为徐葡萄、徐牡丹,并不是他的画有多好,而是觉得他做过县长,是县太爷,古代属于七品芝麻官,有品级的,挂他的画是镇宅图吉利,每当提及此种议论,他都显得有些激动,似乎一个艺术家人格和艺术遭受了玷污和侮辱,哪时的他,完全没了混迹于官场官员的城府,反而是艺术家的单纯和率真。
他有次竟然反问我:“晓春,我的画有(封神演义)里混元金斗阵那么厉害吗?”
然后不等我回答便大笑起来。
在我以为,古代官员都是很有学问的,至少你要经史子集,诗文典賦要熟读,即使考不上状元名落松山的,学问是有的。但是后来的就不尽然,至少逛歌舞厅唱歌跳舞喝酒的时间要比不看书学习的时间多,所以说他们有没有学问,套用时髦话就是,你懂得的。
当时风行于官员下歌舞厅,风行于被打款阔佬宴请,哪有时间和兴趣去玩这雕虫小技,点灯熬油搞这些呢。可徐利贞全不这样,他当初也算一方大员了,一位堂堂区政协主席,区委常委,但他是有勤奋追求的,好几次我去,都见他在画案前握管凝思,挥毫泼墨呢!
第一次见徐利贞先生,还是在董晴野先生驻地,我从北京要请来几位艺术家,商量接待事宜,董晴野老师打电话便叫了他来,当初董晴野先生很自豪也有些买弄地对我说,你别看咋只是个文人,要安全保卫,咋们有玉海,当初闫玉海任公安局长,是董晴野天水诗书画研究院挂名副院长,要官员,我们有凤保,王凤保当初是区委副书记,也是天水诗书画研究院挂名副院长,要车子我们有利贞,徐利贞当初是区政协主席,用车当然方便,对一个还没任何工作,只在社会上流浪的小青年来说,听到这三位地方可望不可及的人物,难免有些诚恐惶恐的。那天徐利贞来,人还没进门,爽朗的笑声和咚咚的走路声已经从门外传进来,由于太肥胖,坐下一个劲的喘气和擦汗。说话也是三言两语,说有啥事需要他干啥尽管吩咐安排。
给人感觉就是当官得就是当官的,办事干练利索,不拖泥带水。
也是从哪次我们就认识相熟悉了,我们两三个搞书画和写作的穷青年,有时相约去他家看他,与其说是看他,还不如说是打他秋风,当初除了我没结婚,爱民兄和老婆狭居在单位一间宿舍里,农村孩子刚上班结婚成家困难可想而知,不要说抽好烟,一般的普通劣质烟常常断顿,每到傍晚,我们敲他家的门,他爱人还是乐呵呵的开门招呼我们进去,他听见院子的我们,照例是大声吆喝:
“一帮碎鬼(天水方言长辈对晚辈亲切的称呼)赶紧往来走……”
然后赶紧吩咐倒茶,递烟,然后是让我们看他画案上正摊开纸画的画,诚恳要求我们指点。他都是用很认真的语气对我们几个说:
“几个碎娃,你们都是将来的精英,宝贝,我就喜欢上进的年轻人,你们别给我这老头子给面子,看我那画的不好尽管说,咋画不好,笨鸟先飞勤奋学会好的……”
夜深了我们在依依不舍离开,临走时,他总要拉开画案旁的抽屉,取几包烟,摔给爱民兄,嘴里还嘟囔:
“碎鬼,拿着,你徐爸当这么个小官,钱没人送,这烟还有人送几包,既然拿来了大家吃了油香香,一个贪吃屁香香,看人家晓春多好,不抽烟不喝酒,将来不受老婆气,一辈子在你老婆面前抬不起头……”
然后是他爽朗的笑声。每次送我们到门口他还要古人似的抱个拳,打个恭,嘴里还开着玩笑,说我们将来成了大作家给他写几笔,不要把他写的太快,然后看我们消失在夜色中,身后传来他闭门拉院灯的声音。
在夜色中我们行走时,心里感受着这种长辈对晚辈厚爱的温暖,也感受着他对我们的期许,当初的我只是一个社会流浪者,连自己亲人都鄙夷的人,和他说的大作家、大画家实在太遥远,觉得能生活下去都不易,一个破旧的院落,有着古墓般的凄凉,除了七八十岁的老娘相依为伴,生活的困顿可想而知,我的出路在哪都不知道,哪奢想大艺术家,大画家的目标。当初只是觉得他开着玩笑,调侃安慰着我们这几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如今我们都已成年,可他却不在了,永远的走了。
从另外也说明着,无论你多大官,多富有,只要你在职在位,你多有钱,只要你能发点善心只要付出那么一点点,后人也会记住你的,因为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举手之劳帮助了一位应该帮助的人。
我的第一本本书出版了,堆在哪里,他比我还着急,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是他,让我跟找他,政府大院挨个单位去推销我的书,用他的话说,用他这张“老脸”去看别的领导脸色,目的,就是出本书不容易,得推销出去给人看,他还边走边给我讲故事,说有个秀才进京考上状元在游街,正好一阵风轿帘吹起,被他老家人看到竟然鄙夷地说原来是村里烂眼子他爸的儿子,由自说明一个地方根本就不抬举一个地方人,他也有生气骂人的时候,当从一个部门单位被别的领导因给我推销卖书被拒绝,他竟出门愤愤地说:“典型的坏怂,平时跳舞唱歌逛歌厅有钱,买两本书扶持下青年作家就没钱……”
好像这许多书是他的不是我的似的,他是那么热心,就是一位长辈在位一位青年奔走呼号,尽心扶持着他。最后见他已经是肝癌晚期,我已经在北京工作几年,听说他病已经晚期,回家时特意去看他,他坐在家里沙发上,右手上插着输液管,我有点伤感,还没等我开口,他还是那么爽朗的调侃,他说,国家主席都害病,何况他,他要真的走了,有人能记住就不错了,他故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晓春,你记住,答应要给我写东西的……”
可是~
这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给他写几句话,可一直不曾下笔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咋样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