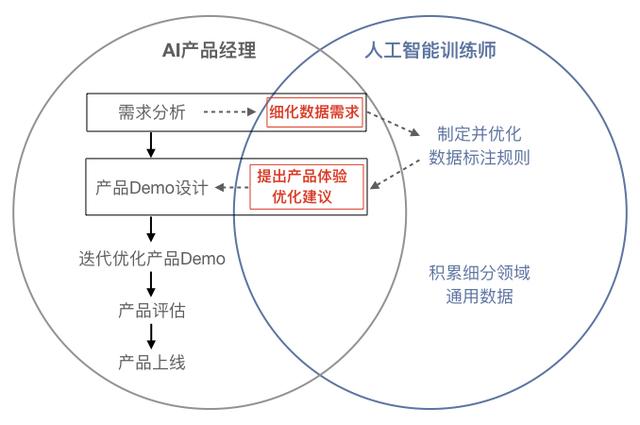1 (1)有关遗世独立一词的语义,最早见之于屈原的《九章•橘颂》,其中有“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之句独立不迁,意为超群而特立、不移不变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意为独立于世、保持清醒、不随波逐流文中以多种比兴赞美橘树的品质(应有屈原以橘树自况之意),其中的“苏世”二字,虽与“遗世”字面上有别,但涵义并无不同,都是意指对浊世觉醒、脱离(保持距离)这也是关于遗世独立一词语义最早、最为切近的表述,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遗世独立般的存在?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遗世独立般的存在
1
(1)有关遗世独立一词的语义,最早见之于屈原的《九章•橘颂》,其中有“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之句。独立不迁,意为超群而特立、不移不变。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意为独立于世、保持清醒、不随波逐流。文中以多种比兴赞美橘树的品质(应有屈原以橘树自况之意),其中的“苏世”二字,虽与“遗世”字面上有别,但涵义并无不同,都是意指对浊世觉醒、脱离(保持距离)。这也是关于遗世独立一词语义最早、最为切近的表述。
遗世而独立作为完整句式表述,见之于两汉时期的李延年的《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但这里的“遗世独立”,却是另外的意思,极言貌美,其中的“绝世”、“独立”与屈原上文所指完全不同。
李延年之后,宋代的苏轼词中又语涉“遗世独立”一词。苏轼《前赤壁赋》中“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里的“遗世独立”,即指脱离尘世、孑然独立,喻指突出、超脱世俗,此乃遗世独立一语的本义,与屈原并无不同。
总括此句语义,“遗世”之意,指的就是弃绝世俗,离群索居。“独立”之意,则指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存在形态。苏轼《前赤壁赋》中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孙绰《游天台山赋》中的“非夫遗世玩道,绝粒如芝者”皆为此意。
以上之所以开篇考证“遗世独立”一语的出处及涵指,是因为遗世独立实际上所指涉的是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于个体人生而言有重要关联。
所谓遗世而独立,当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主动遗世,其二是说为世所遗。遗与被遗,具有内在因果逻辑关系,因为被遗,所以独立。反之,因为独立,所以遗世。遗世——无论哪一种、主动抑或被动,其结果和后果,都必然指向独立。
这里考察的遗世独立,所说的乃是屈原、苏轼的本意,即出自个体的本愿或天性,即主动型遗世,自我超脱世俗,与社会保持距离,不肯同流合污。这与因为被遗而后不得已独立并非等同。世间被遗而独立者大有人在,被动遗世和主动遗世具有本质不同,独立的意义更是大相径庭。
说到遗世而独立,还应提到所谓的隐士一族。隐士顾名思义,就是隐于现实、藏于当世、自行“隐匿”的一类人,通常是指离群索居或遁迹山林之人。隐士一族,与其说是主动避世,不如说是更看重形式,相比于重内在独立修为,他们更在意形式上的弃绝红尘,往往热衷远离尘寰,置身世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此类遗世独立,不在本篇考察的范围。
自古及今,大凡主动遗世而独立者,都是一些品质高洁、自命不凡、具有叛逆倾向的人,多属于人群中的另类,他们不想命运被外在因素左右、操弄,而完全自主掌控、自我主导,我的命运我做主,因而选择遗世独立,远离尘嚣,过着完全从属于自我意志的生活。这种个体生命完全自我主导的存在方式,古今不乏其人,具有重要的人生范式价值和认识价值。
一般而言,大凡遗世而独立者,或多或少都与时代、与社会价值取向有着根本矛盾冲突,属于不相兼容的一种人,因而他们常常也是被时代和社会所冷落的人。他们先于被遗而选择主动遗世,孑然独立于社会和世界之外,自己就是自己的世界的全部。
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基于理性,不如说是基于天性。这正如宇宙中必有一些星体,它们并不遵循既有的轨迹运行,而是打破常规,另辟蹊径,一意孤行,萧然自远,比如彗星,横空出世,遗世而独立,孤独地实现着自我,孤独地走向陨灭。
无论古今中外,所有的遗世而独立者,都是不循规蹈矩者,都是不按既定模式就范者,因而也都不可避免的成为轨道破坏者,他们一生的标签就是四个字:特立独行。
人何以要遗世独立,何以要特立独行?何以要必须如此?
(2)在解析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对人作为社会动物的基本存在方式,做一个大体上的描述:
人作为社会动物,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他就生活在群体之中、社会之中、国家之中和族群之中。这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宏观就位,往往是不由选择的。实际上,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是具体的、共存的、共性的、关联的、共同的。也就是说,作为个体,他的存在形式并非是独立而自主的,他在具体时空中的存在,无论是在家庭中、学校中、社团中、人群中、任何公共场所中、乃至饮食起居中,总之,他基本上无时无刻不在集体中、群体中、大家中、众人中,而很少作为个体单独存在中。即使单独存在,也往往并非是一种出于自我、自主意识的主导、掌控之下,更多的只是肉体暂时性的处于游离状态而已。作为社会中的人,没有几个人的生命,真正从属于自我,处在“遗世而独立”的真实状态。
决定人的存在状态的,与其说是外在的形式,不如说是内在的意识。作为本质上属于精神动物的人,他的生命本质上因何决定,即是他真实的存在本质。
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所有人被一种共同的主体意识左右和操控的共生共在联合体。一般而言,在这里,你所看到的人,外表上看都是一样的,他们并非是作为具体的有独立意识和思维存在的个体,而只是作为符号、作为集体、群体中并无本质差异的个体,他们共同受控于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共同的社会意识。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方法论等)犹如滚滚洪流,裹挟一切,世上的人绝大部分从生下来,还没有明白这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被时代意识潮流裹挟、同化了。
时代意识形态洪流如此强大、强制、专横,不容你思考、选择和抗拒,人在其中是身不由己的。时代的洪流,就是人流,人汇成的洪流。无数人裹挟其中,浊浪翻涌,滚滚向前,荡涤一切。太多的人的一生,就这样随波逐流,被不经意的消耗掉了。
他们固然也都长着自己的脑袋,也都不乏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但他们来不及表达,也不会表达,甚至更没有机会、没有权力表达——这就是真实的社会大众存在状态的一般状况。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被洪流所吞噬、所左右,也有想挣扎着站起来的。他们拼命从汹涌的急流中,试图把头伸出水面,从洪流里站立起来,但阻力太过强大。他们有的也坚持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一任载沉载浮、至死也不再挣扎和反抗……
但也确有不甘就此沉沦者。他们一次次挣扎着试图站起,冲倒了,再挺起,又冲倒了,再挺起……最终,他们挺立起来了,虽然疲惫不堪,但终于摆脱了洪流的裹挟,成功挺立于水面之上。
他们站立起来的身躯,与洪流形成一个垂直对应的界面,形成一种对应的对照的关系,因而即使不是在抽象层面高于现实世界,也至少在现象层面因自身高度差异视界全然不同,他能看到更多水中、水下的人看不到的东西。
此时他们的脑袋不再都是被洪流的水灌注的一个简单的容器了,他自己的思维意识复活了。他用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眼睛感知、观察世界,他也第一次知道了裹挟人们的潮水到底是什么,但同时他也必然地与洪流泾渭分明了。
他抛弃了时代,时代也抛弃了他。作为一个抛弃者和被抛弃者,他最终成了一个遗世而独立的人。这样的人,每个国度、每个时代都有。
什么是遗世而独立的人呢?所谓遗世而独立的人,就是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的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认知世界的人,用自己的嘴巴说话、说自己的话的人,用自己的心去感知、感受善恶、真理、良知和正义的人,总之,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完整的、具体的人,与那些仅仅被叫做“人”实际上仅仅等同于符号的“人”具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个体生命存在的一切真实意义和价值的人。
2
(1)回眸历史,俯察当今,在时代汪洋的水面之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站立起来的人。他们是不同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性格倾向、不同追求取向的人,男女老幼、高下尊卑、健全残缺、各色人等,种种不同。
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在水面之上,把身躯尽可能地挺立着,挺立在汪洋之上,在天地之间,或伟岸、或渺小、或快乐、或痛苦、或歌吟、或惆怅……总之,在现实的汪洋之上,东一个、西一个,杂七杂八地挺立着一些人,一些不一样的人,一些被匍匐在水中的人所厌恶、指责甚至咒骂的人——看那,这些怪物!这些个人主义分子,这些不合群的家伙、这些离经叛道的人…… 但他们全然不顾,熟视无睹,他们就在那兀自站立着,这是他们在天空之下唯一的存在姿势——遗世而独立。
在这些人中间,我们把逡巡的目光,漂移到战国时代的楚国,首先看到的是屈原。
说到屈子,不能不提《离骚》。一般以为,屈原是因怨而有《离骚》,这是也不是。我以为,屈原实际上是因为被遗弃而后才有《离骚》。
因为被遗弃,才会有“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的怨怼,“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的剖白,才会有“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的感喟,才会有“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明志。
试想,如果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得以实现,还会有如泣如诉的《离骚》吗?最能表现屈子高洁之质的,即是寓于《九章•桔颂》中的咏叹。屈子借橘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以自况。然而,即便是“苏世独立”,他的独立或苏世,都有其被动一面,颇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
不能不说,屈原的“苏世独立”之独立,具有被动性、被迫性、他使性的一面,独立固然独立,但给人一种因为外在原因迫使不得不如此之感,而并非是一种出自天性或主动自愿的独立。因此,屈原虽赞美、仰慕橘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之质并以其自况自许,但他自己终究不是橘,虽也“苏世独立”,但却有被遗而“独立”的款曲。
对于屈原而言,他的遗世而独立,尽管独立只因被遗,愤懑而作《离骚》,但能做到“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亦不失“虽千万人独往”的决绝,在他那个时代并非常人可以为之。正因为如此,回溯漫漫历史时空,屈原傲然挺立的身躯横空出世,气贯古今,犹如一尊雕像,矗立在九州大地之上,成为后世中国人遗世独立的典型范式和人文楷模。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与屈原相比,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他们同样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失败者,其道不得以行,郁郁而不得志焉。屈原《离骚》中的“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所阐发的感慨,固然诉诸对象不同,但“误入歧途”是一致的。
屈原固然是在指陈“朕”之“行迷”,他自己又何尝不是,直到投身汨罗以前,政治理想(幻想)依然没有破灭的他,一直行走在自我的迷途上。与屈原相比,陶渊明虽说最后归迹山林,但此前时而退隐时而出仕的矛盾心理无不表明,他也只是在表面上迷途知返了,而其郁郁寡欢的心路历程,仍然是曲曲折折地围绕庙堂在打转转。二人虽然都有“迷途”之警,而实质上都没有真正“苏世”——彻底清醒走出“迷途”,都对政治抱负残存着不绝如缕的幻想,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举棋不定。
就结局而言,屈原的“遗世”是被动的,而陶渊明的“遗世”看似主动,实质上也属于被动而为之,二者之“遗世”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陶渊明的“归去”,由始于官场的排挤无奈的被动,到归隐田园的决绝终成独立的主动。如果说陶潜经过痛苦的炼狱最终醒悟走向生命的自主和独立,那么,屈原则在为世所遗后仍痴心不改念念不忘上下求索,并没有真正醒悟走向独立和新生,最终以死明志发泄对失望以至绝望的怨怼与哀惋。
(2)我们把逡巡的目光,从屈原、陶潜时代,再回溯到盛唐时代。唐朝本是历史上举世闻名的开明帝国,风流万古无出其右。那么,唐帝国遗世独立的人又将如何?当然比之屈原、陶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屈原、陶潜时代,这样的人还是偶尔一见,那在大唐则司空见惯,特立独行者比比皆是,这也反证了帝国无与伦比的开明和包容,所谓大唐盛世,其实正是兼收并蓄天下所归的结果显现。
我们的目光首先锁定的就是有谪仙之誉、旷达盖世绝冠古今的大诗人李太白。李白不仅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人,更是一个大孤独者,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纵观李白一生的际遇浮沉不难看出,他之遗世,既有屈原的一面,也有陶潜的一面,在遗与就之间徘徊挣扎。但就其实质而言,也当属于被遗一族,与屈原可谓同病相怜。
李白无论狂放到何种程度,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为世所遗的苦闷泥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新生。因此,李白与屈原一样,都是孤独只因遗,愤懑始成诗,最终形式上实现了相对的“独立”。正所谓“祸之福之所倚”,因为被遗而独立,因为独立而啸傲,因为啸傲而留下千古文章、一世英名。
相比于以上几位,中国历史上更大、更著名的遗世独立者,可能要数老子了。老子最后辞官归隐不知所终,留下千古之谜。所遗《道德经》如此高深莫测,正可以看作是老子遗世独立之异、之奇的折射和写照。
孔子亦复如此。一生颠沛流离,无所归依,其境况何止遗世独立四字可以形容?当年伫立于泗水岸边,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的夫子,最终亦同样为遗世而独立所成就,没有遗世而独立,何来儒学一脉源远流长……
遗世独立者充斥着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吟咏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陈子昂,孤独立在月光之下“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的苏轼、“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的辛弃疾、“怒发冲冠、凭栏处,抬望眼,仰天长啸”的岳鹏举、“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易安居士……每个时代都有这样那样遗世而独立的人,正是他们构成了历史和文化的脉络经纬……
漫漫历史时空下,汪洋浩瀚的时代水面之上,遗世独立、特立独行者何其多矣!以上只不过蜻蜓点水般提到几人略作表述而已。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文化、文明和历史,与遗世独立者们密不可分,各个时代的遗世独立者们,在自己的时代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没有他们,没有挺立在时代水面上的特立独行者们,我们并不知道何以国家、民族,何以历史文化,何以家国一切。
当今时代,各种各样的遗世独立者同样不乏其人,只不过因时代不同,不为世人关注而已。比如一度隐居终南山、面壁二十年,一鸣惊人的独立学者王东岳,就颇具代表性。
在当代中国学人中,王东岳是我所重点关注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其最具开创性意义和价值的成就,在于其苦心建构的系统庞然的哲学理论学说——即递弱代偿理论,以此阐释世界的本质及其演化——即他的哲学代表作《物演通论》。
这本书推出时间并不长,未曾听到正统学术界任何反应的声音——或不屑关注置评——总之没有任何反响,只是在民间思想界一度引发有限的骚动。作为新崛起的民间哲学家,王东岳进入大众视野的短暂行迹,如同一枚石子,虽然瞬间在湖面上激起些许水花,但很快便消失在死水微澜的表象之下,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王东岳积二十年之力一飞尚且如此,可知在当代中国,并无多少人看重灵魂之事,人们只关心柴米油盐,一个思想家的出世,远不如一个戏子的花边新闻更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
在我看来,至少在中国哲学史上,王东岳应有一席之地。姑且不论其哲学思想能否行之后世,仅以其科学严密的逻辑推理导出的庞大哲学理论体系而论,哲学界并无人能出其右,亦足令当代高居庙堂之上所有哲学教授导师们汗颜。
在当代中国,遗世而独立且具有非凡成就者,可以举出很多人,比如独立学者、经济学家、思想家、作家何新,著述甚丰,影响尤巨,举世公认。即使年已古稀,仍高扬着遗世独立的旗帜,勤于笔耕心作,宣示着自我的独立存在。
更多的遗世独立者,则是在前行的路上。在我有限的生活圈子内,亦不乏遗世独立于孤独中不懈奋斗的灵魂,他们表面看去平淡无奇,各自坚守在自我的天地,如同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过着“不创造、毋宁死!”的生活,从不曾向现实和黑暗妥协。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屋檐下,都有遗世独立的身影。
何谓民族脊梁?民族脊梁不是指肉体外在,而是指精神内在。既然是精神内在,它不应是某个人的精神,而应是一种大众化的、泛化的能够代表民族整体内在品质的品格精神。我以为,遗世独立作为一种普遍的个体精神存在形式或形态,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气质颇为吻合。
3
(1)这里之所以把遗世独立作为存在问题关注的重点,从哲学层面进行一般性的考察,所关注的乃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生存形态、存在状态,遗世独立——乃是人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殊态——与大众庸常的存在形态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种存在状态。
作为人的一种另类存在状态,遗世而独立,强调的是淡化或忽略群体性的存在,而突出和重视个体性存在,使个体在一片混沌之海的群体状态中,得以凸显和浮现出来——遗世而特立,使个体生命不至湮没在群体共性随波逐流之中,独立自主地规划施行自我生命价值取向及其实现形式。它所指陈的,是个体自由、权力、自主、价值、真实等具有本质存在特征和属性的范畴和领域,只有在这一范畴和领域中,讨论个体存在才具有价值和意义。
换句话说,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必须置身于一种有别于他者的遗世而独立的存在形态,遗世而后独立。唯能遗世并自我独立者,方具有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否则作为个体的存在,通常只能是作为一个符号、一个影子、复制品和模糊性存在,不具备个体存在的前提和构成条件,因而也没有任何本体真存的实质性意义。
这里需特别指出,遗世独立这一作为个体真存形态的概念确定,并非指世俗所谓一般意义上的成年或成年人的生存状态,法律上以18岁为个体成年法定年龄的独立个体界定,并不在这里设定的讨论范畴之内。法定年龄只是一个人物理性成熟的标志,而人的外在物理性成熟度与内在精神性成熟度,并非一个概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一个天才少年在精神层面可能比一个耄耋老翁都要高,精神成熟度与肉体成熟度并不必然的成正相关。因此,作为个体存在的一种非常态形态——遗世独立,不包括对自然人的所谓成熟与独立生活状态的关注考察。
这里所谓的遗世独立,尽管从表述上是一致的,但具体而言是各有千秋的。遗世而独立者之有别,在于遗世原因因人而异,即遗世主动还是被动。在我看来,主动遗世者,俗世鲜有一见,那些很早就自断尘缘者,或厕身世外的高人比如宗教信仰中的僧人道士或可称之,但亦不在此考察之列。
一般而言,遗世独立有被动与主动之分。这里关注的遗世独立者,指所谓的主动遗世者,即在世俗生活中,主动选择遗世——远离或淡化世俗生活,遗世而特立——在人生范式和生活方式上,选择特立独行者,但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多。
更多的遗世独立者,属于被动遗世者。虽为被动使然,但也有清浊高下之分,君不见,有人一朝为世所遗,便从此一蹶不振,浑浑噩噩终其所终。而有的人为世所遗,虽不免痛苦挣扎,终究不湮其精神意志,经由涅槃实现生命重生再造,最终在精神层面与形式上超越庸常者,大有人在。
一言以蔽之,无论哪一种遗世独立,都是生命的大课题,都是生命的大解脱,生命层次的大提升。欲成大事者,未有不独立者;而欲求独立者,未有不遗世者。为世所遗而获得独立者,亦有幸于焉。
(2)遗世独立,与其说是一种生存形态,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状态,它所强调的并非在于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在于生命自我主导及其价值取向与意义自我建构。
人是社会动物。依据王东岳的观点,“社会”并非是一种类似组织、机制之类的宏观存在架构,而是一种生态结构,社会是一种广义上的生命体,而非一种无生命的空间形态,打个比方,社会犹如宇宙,人如同其中的行星,行星看似悬置其间,与宇宙虚空并不相干,是一种“悬浮式”存在,其实不然,各种行星与宇宙空间存在内在的、紧密的、既定的因果关系,宇宙中的各种看不见的物质,构成了行星存在的背景和环境因素条件,决定着行星的形成、发展、矮化和死亡。
人与社会的关系,如同行星与宇宙。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无形的网,人则是附着在纵横网格之上的附着物,只是一种附着式存在。人一旦离开社会,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就将脱离斩断,如同植物与根部断开,很快就会枯萎死亡。
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预设和给定,遗世从来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和形式,世上并无为遗世而遗世的人,除非是选择自杀式遗世。所有遗世行为,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即为何遗世,或遗世为何。
遗世的目的性,决定了遗世只是手段和形式,它本身并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和价值只能显现在目的中,或只有在目的中才能显现遗世的价值和意义。
遗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获得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亦即通过对社会、对他者一种时空上的有限的分离和形式上的相对剥离,把个体从一团浑浊的、胶着的、紧密的群体性关系状态中,剥离为清晰的、松散的、脱开的个体存在状态,这种个体存在状态,就是“独立”。
遗世并非与世隔绝。与世隔绝式的遗世固然有,在古代社会或许可以做到,在现代社会并无可能,也无必要。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大凡遗世者,更多在意的是,选择一种离群索居的自我自主的生活方式,为的是获得生命在时空中的相对的独立,而非彻底隔绝人寰。
所以,绝对意义上的遗世者是没有的。所谓遗世的相对性,即排除了遗世的绝对性,使个体与群体形成一种对应和对照,其所强调的是突出个体的自我性、自主感、主导性。
真正遗世者,亦非绝对远离世嚣,不食人间烟火,而更多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获得而甘愿舍弃的抉择。因此,所有真正意义上的遗世独立者,并非在于形式上与外在的疏离,而在于心灵的超然和解脱,把自己还给自己,使自己属于自己,自己成为自己的国王、自己的主宰、自己的监护人、自己的建设者。
由此可知,遗世而独立,作为人在社会中存在状态的一种游离或改变,是有条件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遗世与独立作为两个构成这种游离或改变的要件互为因果,因为独立所以遗世,因为遗世所以独立,要独立必须遗世,不遗世则不能独立,要遗世必须独立,不独立则不能遗世,遗世与独立一体两面,本质同一。
这里之所以探讨遗世而独立问题,是因为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它与个体、种族国家,乃至文明、历史,关系极为重大。我的文明观和历史观认为,文明与历史从来都是由个体英雄创造的,而不可能是由所谓作为“人民”的群体和整体创造的。世间只存在个体、个性、个人,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民”、集体或群体,人民、集体、群体,只是个体、个人之和,没有具体的个体、个人,便没有人民、集体、群体。只有个体、个人的卓越,才有人民、集体、群体的卓越。而个体的卓越,就集中体现为无数个遗世而独立的个体的卓越。
遗世而独立的人,正是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天空,就是由他们孤独守望着,其中一些人最终化为永恒星辰,彪炳和点缀其中,令世世代代仰望。
原创:李耽 总编:王立楠 (版权所有,违法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