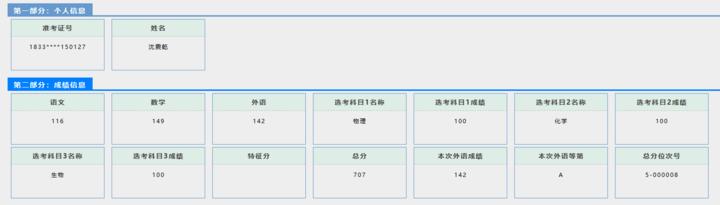作者丨黄宗权
不少当代学者对传染病如何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有研究。比如,认为1348年在欧洲暴发的黑死病,是东罗马帝国崩溃的深层原因。再比如,认为从14世纪到17世纪,每隔几十年一次的鼠疫使得人口剧减,劳工阶层崛起,有条件主张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一步步瓦解了欧洲的封建贵族制度,资产阶级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如果说传染病影响政治进程是间接的,那么对文学艺术的影响看起来更为直接。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诞生于14世纪瘟疫流行期间,借助抨击教会完成了早期的人文主义启蒙。音乐当然没法像文学那样讲故事,但传染病也影响了许多音乐作品的创作。对音乐历史的另一个影响是,传染病让许多作曲家英年早逝,常常让后人感叹,如果他们活得更久一点,音乐史也许就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了。
早期的一个例子是宾根的希尔德加德
(Hildegardof Bingen,1098–1179)
。我曾在去年的某篇专栏文章里提到过她,这个著名的中世纪女作曲家的正式职业是本笃会的修女,她的很多音乐作品的内容都和治疗呼吸疾病有关,比如,教人如何用孜然、肉豆蔻和洋甘菊充当药物。

马肖
和薄伽丘同一时代的纪尧姆·德·马肖
(1300-1377)
写过一首歌叫《纳瓦拉国王的审判》
(Le jugement du Roi de Navarre)
。这首歌的特点是异乎寻常的“长”。全曲用了4200节经文,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描述了黑死病给当时造成的巨大破坏。
和疾病感染有关的题材在后来的音乐作品中,例子也不少。比较著名的是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两部歌剧作品的女主人公薇奥列塔和咪咪患的是同样一种传染病,就是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的肺结核。《波西米亚人》的脚本改编自法国剧作家穆杰
(Murger)
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涯》
(Scènes de la vie deBohème)
,剧中咪咪的人物原型之一吕希尔是穆杰的情人,20岁时得肺结核死了,主角咪咪的名字就来自吕希尔在现实生活中的绰号“咪咪”。
和染病死去的剧中人相比,死于传染病的作曲家更多。尼德兰作曲家奥布雷希特
(Jacob Obrecht)
死于1505年;勃艮第复调乐派的重要人物,名声仅次于若斯坎的阿格里科拉
(Alexander Agricola)
死于1506年;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兼著名教父格雷罗
(Francisco Guerrero)
死于1599年。他们的死因是一样的,都是当时欧洲流行的瘟疫。另外,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死于1643年的蒙特威尔第是因为得了疟疾。
法国歌剧之父吕利,在使用一个长的指挥棒指挥乐队的时候,不小心戳到了自己的脚背,不久后伤口转为坏疽,他于1687年去世,享年55岁。同时代的英国作曲家普塞尔,也同样不幸。一天半夜,他从剧院排练完回家
(一说是从酒馆回家)
,他的妻子生气把他锁在了门外边,可怜的普塞尔挨冻后感冒了,卒于36岁。当然,严格说来,这两位不算是死于传染病。

莫扎特画像
关于莫扎特的死因有各种传闻,甚至“阴谋论”。比如,他是被共济会成员用汞暗杀的,原因是歌剧《魔笛》泄露了某种秘密。该传闻并非坊间碎语,在纳粹德国时期的1936年,有一篇题为《莫扎特的生命与暴力死亡》
(Mozart’s Life andViolent Death)
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说到此事。也有说是被他的远房兄弟霍夫德梅尔
(Franz Hofdemel)
谋杀的,因为他与莫扎特的妻子有染。另一种经常被浪漫主义理论引用的传闻是,莫扎特死于同事安东尼奥·萨利里
(Antonio Salieri)
的谋杀,因为后者嫉妒莫扎特的天才。
当然,没有实锤证据证明这些传闻属实。今天的历史学家和医学专家根据莫扎特死前自己和第三方的各种描述来推测他的病情。最普遍的看法是,莫扎特死于风湿热——当时维也纳正流行这种病。不过,近年出现了一种新理论,认为莫扎特死于一种叫旋毛虫的寄生虫引起的疾病。莫扎特爱吃猪排,他在1791年10月7日至8日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吃猪排的事。研究者认为他有可能是吃了受寄生虫污染的猪肉而致病的。一代天才只活了35年。
相较莫扎特,贝多芬其实是幸运的。他战胜了天花,并抵抗住了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最终摧毁他的是耳聋,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贝多芬给他的兄弟查尔斯
(Charles)
写了一封最终没有寄出去的信。在信中他写道:“我对发现自己的状况感到极大的焦虑……我离结束生命不远了……只有我的艺术阻止了我。”导致他耳聋的原因是各种可能因感染而引起的慢性病。贝多芬死于1827年,几乎可以肯定他死于肺炎和一系列并发症。

贝多芬写给哥哥的信。
柴科夫斯基的死也有不同说法,其中之一是他忍受不了和同性恋有关的流言飞语而自杀了。另一种说法来自于他的兄弟摩德斯特
(modest)
等目击者,说他是喝了“一口致命未煮开的水”而感染霍乱而死的。
和浪漫主义一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肺结核是许多作曲家的重要死因。39岁去世的肖邦,40岁去世的韦伯都与此有关。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得了肺结核几乎等同于死亡本身。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艺术家圈子中流传一种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观点,即,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的那样:“似乎在十九世纪中叶,结核病就与罗曼蒂克联系在一起了。”用卡米尔·圣桑的话说是:“肖邦患结核病之时,正逢健康不再时髦之际”。

《临终前的肖邦》,Teofil Kwiatkowski绘制于1849年。
在那个时代,一旦得了肺痨往往被认为是上流社会优越和有教养的标志,这在当时的文学和传记作品中流露得非常明显。
所幸,现代人对传染性的疾病有了全新的认知,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不再以一种病态的观念如波德莱尔在《元音》中写到的——“苍白与潮红,一会儿亢奋,一会儿疲乏”,将其视为一种典雅的美。
我们在讨论疾病的时候,更多的是感叹人生的无常以及对生命的敬畏,或者如沃森所说:“现在是以还原的方式去理解疾病、癌症和艾滋病的时候了:它们是身体疾病,而没有道德的社会的或文学的意义负荷。”
(彼得·沃森著《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p.771。)
本文原载于《音乐周报》,已获得授权刊发。
作者丨黄宗权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