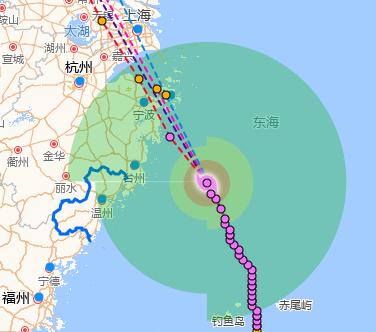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朱秀海

终于有机会讲一讲那一次的读书经历了。
1978年冬末,刚刚非常意外地从作战部队调到武汉军区机关的我更为意外地接到了随陆军某军某师参战的命令。从受领任务到出发报到,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夜,为了是不是带上一本上午才从单位图书室借到的世界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我踌躇多时。简单说来,借到这本周扬与人合译的竖排本繁体字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是我的文学生涯早期的一个稍显悲惨的故事的一个细节。此前因为偶发奇想写了两篇小说并被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我,仓促调进军区创作室后,单位领导与我进行了第一次谈话,惊讶地发觉我几乎连一本真正的西方名著都没有读过,大失所望之余给我开列了一张长长的书单,要我继续写作之前先把这大约二十多本名著读完了再说。我进了图书馆能借到的却只有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从这个细节上看,我和《安娜·卡列尼娜》的相遇也是一场意外。我一页还没有读就开始整理出发的行囊,我将它放进去又拿出,拿出又放进去,最后还是将它留在了挎包之内,虽然并不相信上了战场还有时间看完它。我现在认为我当时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下意识中仍然保留着一点对于生的留恋。
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四天后就上了开赴南线的军列。途中三天并没有想到读它。部队到达集结地域后马上开始了紧张的战前适应性训练,这时我仍然没有想到读它。但是战争居然没有马上开始,从我们抵达集结地直到1979年2月17日战争正式打响,中间隔着在感觉中异常漫长的52天。因为等待,因为战前各种相互矛盾的消息,战与不战一段时间内似乎也成了问题,最早的紧张气氛悄然转换,读书就不但有了时间,而且有了心情。那套两卷本的《安娜·卡列尼娜》被重新发现、取出,在依旧紧张的战前训练间隙打开。
最初的阅读是信马由缰的,写意的,仿佛只是为了消耗那些因为等待和不确定而突然显得空虚的夜晚,而且阅读是不顺利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奥布朗斯基一家全乱了。”身为枕戈待战的军人,虽然有不战的传言但仍然随时可能闻令而起,奔赴战场,“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出不入兮往不反。”在如此的氛围里读上面那样的句子是怪诞的,会突然产生无边无际的距离感。然而还是在读,想知道奥布朗斯基家怎么一切都乱了,然后安娜出现,为出轨的哥哥和痛苦的嫂子劝和,命运让她不可阻挡地遇上渥伦斯基。同样重要的是,另一个男人列文也出现了,开始了他和自己心仪的恋人和婚姻对象吉提这另一组人物纯朴的、追求基督教义下理想主义生活的几乎纯粹唯美的故事。两条线索同时在发展,一条是疯狂的、飞蛾扑火般的、烈火燃烧般而且似乎是身不由己地对于自由爱情的追求,其中充满了巨大的欢悦、越来越多的痛苦、猜疑、忌妒、误解,一条是屡遭挫折的、小心试探的、为基督精神所约束的、对于爱和理想化生活的寻寻觅觅,前者是热情似火的肉体和精神对于世俗乃至于宗教精神的不顾一切的反抗和挣扎,后者则几乎纯粹是人对于理想的和爱的、合乎所谓“上帝的真理”的婚姻生活的追问,对“人怎么做才能真正获得幸福”的追问,其间也充满了内心的挣扎、相当沉重的痛苦,但却是追求“合乎道德的”“高尚的”、理想主义生活道路的痛苦,等等。
战争打响前夕,我几乎读了这部书的三分之二,却觉得读不下去,和我过去接触过的中国传统小说和中国当代小说相比,托尔斯泰书中的故事太繁复,对于人类内心幽微的洞察过于绵长细密,曲折深邃。每一条河只要发源于我们能看得到的群山,就一定会汪洋恣肆,浩浩荡荡,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两岸绿树繁花,令人目不暇接。你看到的不是一条大河两条大河,而是众河汹涌,激流澎湃,即便在你看来只是一条河汊子,也都充满着自己的性情,自成一河,喧哗而灵动。
但这并不是我读不下去的理由,我看不下去的最强烈的理由是我一直觉得这一切和我已经无关了。我仍然在读,仍然在感受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在自己独特的(当然是被作者安排的)命运世界中的奔走挣扎和呼喊,他们在作家的笔下依旧或真诚、聪明、美丽,时而勇敢时而懦弱,即便在走向歧途时也似乎仍然振振有词,然而每一个人也都处在自己的迷茫之途当中,都在用尽洪荒之力寻找那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和爱,但却又是每个人很难得到的,每条大河面前都横亘着另外的无数条大河,每一条大河都充满了力量和渴望,于是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在现实和渴望之间,清晰地出现了绝望。虽然对于某些孜孜不倦追求的人来说,这绝望也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世界上最大的河流随着时光也有可能改道。可是这一切和我这个枕戈待战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于是我把它放下。
战争在1979年2月17日打响。事实上两天前我们就接到了命令。虽然一直在准备,但命令到来仍然在感觉中显得突然。军车开赴战场的那个早晨,大雾笼罩了集结地的所有房屋树木,在视野里它们全成了一丛丛白色的雾的存在。我们就在这样令人震撼的几乎显得不真实的雾的景象中登车前行。上级再一次要求清理行囊,我也再一次下意识地选择将没看完的《安娜·卡列尼娜》放进步兵背囊,带它上了战场。
第一阶段的战斗进行中我一直带着这套书,此外步兵行囊内就是子弹、一枚手榴弹和几包压缩干粮了。整个战争期间真正残酷的战斗几乎发生在第一阶段。我所在的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势如破竹,三天的任务一天半即告完成。我在战斗打响的当天就进入了战场,同行者有写出《谁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著名记者李启科同志。战斗在四面八方进行,雷区内到处可见没有被突击部队爆破掉的绊发引信地雷,它们两个一组被一根草绿色绊线牵着,无规矩地放置在及腰深的草丛中。当时说一句“有地雷,绕过去”并不是玩笑,而是我们在战场上穿行的真实写照。我也就是这一天第一次经历了真实的战斗,我们在枪声和炮弹爆炸中登上了2号高地,进入激战方熄的战场,当晚又和师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位战友一同到了最前沿的11号高地,那里距离敌人阵地只有百米,整整一夜这位战友都在讲述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故事,而这时我俩置身于一道半坍塌的堑壕里,背靠一棵被炸倒的大树,身边是一丛丛被打燃的野草,望着一发发从敌方飞来的炮弹落在我们阵地后方的山林间爆炸开来。
内心中波翻浪涌的时刻,“生存或者死亡是一个问题”之类挣扎的时刻早已过去,现在只剩下对于战事本身的兴趣,连同对于往事的回忆,这回忆也是告别,是向生告别的最后阶段。这个晚上,我们一直等待的反击敌人反扑的战斗并没有发生。第二天黎明撤下11号高地时下起了小雨,阵地上已经没有部队了,部队已经撤了,偌大一个高地上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就被雨水淋醒了,背起枪往山下走,发现下面还是昨天经过的那片不时会发现一组没有被爆破掉的地雷的草地——仍旧说着闲话绕来绕去绕了出去,上了战时急造公路,突然间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暗红色的曳光弹从头顶和身边飞过,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就蹲下,等待战斗结束,然后回基本指挥所去。这时候你是想不到你的背囊里有一部《安娜·卡列尼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