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点击中国民航关注并购买
很久很久以前,很多民航乘客是因为“写作”才翻看《中国民航》杂志的。在热闹喧嚣的网络年代,“写作”这个词本身所隐含的态度就值得尊重。去找寻这个时代有意思、有意义的好文字,它们能在方寸间带我们纵横千年于弹指一挥间,驰骋东西的思维从不受限,览尽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人性生发的爱恨情仇更从未间断。
从现在开始,杂志每周推出一篇写作栏目作者的好文章,也就千把字吧~~~

鞋 的 故 事
文:刘嘉陵
多年前,我二姐一直梦想有一双漂亮的鞋子,为这个,她吃了不少苦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报社当领导的父亲被“打倒”了,全家搬进小胡同里的简陋平房。在那个禁欲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姐姐们还是悄悄考虑起“美”的问题。她们不羡慕反特片里女特务烫的那种鸡窝头,因为自己有飒爽英姿的刷子辫,更不屑于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一套洗白了的仿军装就已足够壮美。


但是鞋子,鞋子的事情怎么办呢?
春夏秋季,她们可以穿方口拉带布鞋或黄胶鞋,可冬季里,菜包子一样难看的地方产棉鞋令她们心有不甘。那时候,洋气的黑趟绒面儿穿孔系带的北京棉鞋已征服天下,且男女通用,男孩子穿上显得学习好,女孩子穿上显得家境优越。姨妈在北京,于是两个姐姐各有了一双“白底黑边北京棉”。二姐穿鞋很费,第二年,鞋子就五成新都不到了。乡下插队的大姐不怎么舍得穿,鞋子八成新。
二姐转学到了一所重点中学,和一群军官女儿混得火热。她们不在意二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被她的口才迷倒。夜晚的学校宿舍或大人不在家的空荡荡宅院里,二姐一惊一乍地讲着“梅花党”的故事,女孩儿们都钻进被窝,蒙头盖脸地享受着恐怖之美。二姐名字里有个“维”字,于是被赠雅号 “维兄”。


冬天来了,军官女儿们纷纷穿上黑亮的军用皮靴,鞋子已旧的“维兄”便回家翻箱倒柜。父母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家里只有回城探亲的大姐。她帮二姐好不容易翻出母亲早年定做的一双黑皮棉鞋,质量不错,只是鞋面图案像孙悟空的猴脸。“维兄”深感美中不足,但聊胜于无。
真正的麻烦是,这双资产阶级式的女鞋是高跟的。“维兄”风风火火从厨房取来菜刀,向两寸长的鞋跟拦腰砍去。她明显低估了对手,奋力砍过多刀后,除了浅浅的刀痕和红红的脸,没什么实质进展。我和大姐也成了帮凶,甩开膀子轮番砍,刀痕却只深了一点点,粗壮的甘蔗若经如此砍杀也早断成多少截了。二姐喘着粗气,没了法子。大姐责怪:“你虚荣心咋那么强啊?”二姐狠狠拭了把汗,不再吭声。大姐心疼小妹:“要不先穿我那双吧,省着点穿。”
每晚回到家,二姐的鞋子都有些潮湿。火炉熄灭后,她就把鞋放到炉边烘干。有一天她回来得很晚,疲惫不堪,按照一向让什么事都锦上添花的习惯,她把鞋子最大限度地塞进炉底的出灰口,就睡了。次日一早大家发现,那双鞋真的“锦上添花”了。

于是大姐那双八成新的“北京棉”自豪地加入到军靴的行列,那段时光无限美好。
二姐蹲在地上哭起来,她觉得太对不起大姐了,更担心让母亲知道。她做梦都无法梦到欧洲童话里那双绚烂至极的水晶鞋,灰姑娘穿上它们,舞着舞着,舞向了英俊的王子。她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许多年后,漂亮鞋子算得了什么。她家门口总是一地鞋子,像是泊舶着千轮万船的大码头。靠墙的鞋柜里更是五花八门,长筒靴,矮腰靴,高跟皮鞋,平跟皮鞋,露脚趾不露脚跟、露脚跟不露脚趾、露脚趾也露脚跟的凉鞋,鲇鱼形,火箭型,松糕形,蒸饼形,熘炒俱全。她当年曾惊异于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克斯有三千多双鞋子,一天换一双十年八年才能换完,一天换十双也差不多能坚持一年。而她和大姐呢,就那么一双好鞋,还毁于残存的火炭。



屋里很冷,一股呛鼻子的炉灰味。二姐哭着哭着大声咳嗽起来。
“北京棉”被大姐用旧棉絮和两块黑趟绒对着茬儿好歹缝上了。二姐变得谨慎而气馁,她越来越不喜欢上课间操和一切亮处。背阴里,她悄悄打量脚下时不免感叹:这样的针线实在难为大姐了。
不久后,“维兄”穿着它们告别了那些军官女儿,随家下乡去了。


作者: 刘嘉陵,男,沈阳人。插过队,当过乡村教师,谱过曲,开过机床,做过扶贫工作队员。198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曾获“老舍散文奖”、“清明文学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著作有《硕士生世界》《记忆鲜红》《自由飞行器》《妙语天籁》《舞文者说》等。

原载于《中国民航》杂志2017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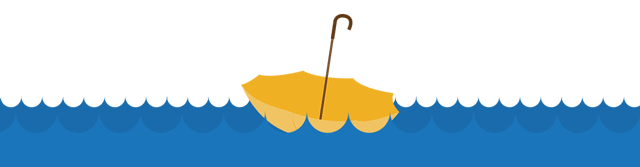
敬请关注杂志的 阅 读 与 写 作 栏目
欢迎投稿与建议——
caacwriting@163.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