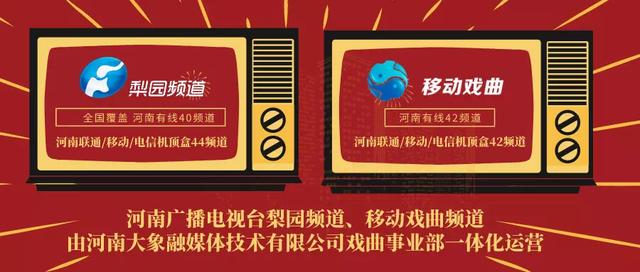来源:【济南日报-爱济南】

一日,陕西巡抚殷学,听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李攀龙有极高的文采,又是山东老乡,就想让他代写一篇文章。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在于为这个事,殷学竟然以居高临下的架势,颐指气使地给李攀龙下了个檄文。李攀龙本是性情中人,磊落坦荡,见到檄文后,顿感受到了侮辱,不由得大怒起来:你命令我写,我就写吗?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写了一篇《乞归公移》报告,送到了殷学的案桌上,要求告病还乡。
真正有风骨的读书人写文章,分为勉强为之和真心流露两种。最不愿写的是阿谀奉承和命令式作文。
殷学不知道李攀龙的心里始终藏着中国文人的端然姿态,只是觉得李攀龙有些矫情。他先是假意挽留,一看不行,就以官位要挟李攀龙。
李攀龙说:“你以为我很看重这个官位吗?”
殷学没想到李攀龙根本不给他面子,更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
也许,他觉得李攀龙会像其他的部下一样,对他的发号施令或言听计从,或百依百顺,满足一下他的专横跋扈。
二人互不相让,闹得不欢而散。
李攀龙以疾病上疏请辞陕西提学副使任。
而事实上,李攀龙当时身体的确不佳,因在任期间受到几次地震的惊吓,又患有心脏病,所以,以回乡养病为由提出辞职。
好友王世贞知道后,曾极力劝阻,但李攀龙去意已定,并把辞官看作是自己更高精神追求的开始。王世贞知道他是想醉心遨游山与水,心思简净诗与文。
于是,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夏秋之交,未等到辞职报告经吏部批准,45岁的李攀龙就拂衣而去,回到了济南。
辞官回到济南,李攀龙先是住在东郊鲍山附近的东村,卧病休养,此处,推窗就可以看见华不注山、大清河和小清河。
嘉靖三十八年,在好友王世贞的建议下,李攀龙用平日的积蓄在王舍人庄东北隅筹建了鲍山南楼,后来改为白雪楼。
白雪楼,以寓战国末期楚国辞赋作家宋玉《答楚王问》一赋中“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意。李攀龙以此表明自己孤高自诩,不同流俗。对于这座白雪楼,李攀龙在《酬李东昌写寄〈白雪楼图〉并序》中记述道:“楼在济南郡东三十里许鲍城,前望太麓,西北眺华不注诸山;大小清河交络其下。左瞰长白、平陵之野,海气所际。每一登临郁为胜观。”
旧时“济南十六景”之一的“鲍山白雪”指的就是这座白雪楼。
一日,因病弱而伏卧在床上的李攀龙,撑起身子,坐起来,望向窗外,此时,雨雾迷蒙,云气弥漫,林间溪水,缓缓流淌。推门走出,登高远眺,孤城在大清河、小清河的拥抱下,越发显得亲切妩媚生动,两条河流向东流去,东面的长白山,被一抹余晖照耀其上。自己就像当年懒散慢世的嵇康、辞官归隐的陶渊明,早已超然物外,把功名和富贵都当成了杯中的过眼浮云。
随即,他写下了这首《白雪楼》:
伏枕空林积雨开,旋因起色一登台。大清河抱孤城转,长白山邀返照回。无那嵇生成懒慢,可知陶令赋归来。何人定解浮云意,片影飘摇落酒杯。
李攀龙自从归隐济南后,心情逐渐变得宁静而愉悦,无官一身轻,少了官场上的许多应酬和烦心之事,身体也渐渐康复起来。就像倦鸟,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巢穴,极目远望,眼里的山山水水都云彩流散、波光粼粼。许多不知名的野花,散落在白雪楼的四周,踩上去,心也变得格外柔软。
古时的文人骚客,每到孤寂绝望的时刻,一定会寄情于山水。他们向往山林的幽静,轻扣月下的柴门,焚香煮茶一小盏,仰观漫天的星辰,垂钓于渭水之滨,高山流水寻知音……正是大自然的抚慰,让他们澄心忘俗,气爽神清,旷达明净,重新唤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飞扬气势,从而,华发风尘过,青山雨雪开。
李攀龙即是这样的人。
他写乡居生活的宁静恬美;他写悠悠碧波的丁香湾;他写云雀在楼阁上婉转啼啾;写老牛车在雨水中不知疲倦地转动着;写蝉语划破天空的辽阔;写田野上一两个往来其中送饭的妇人;写在空寂的深山里“心同流水净,身与白云轻”的感受;写成片的庄稼把大地装扮得油绿滋润。他在闲对山水之时,涤荡了心中的不快,郁结在心中的垒块,也轰然倒塌。诗人摒掉尘间沾染的浮躁,渐渐安静下来,敞开的胸襟也开始辽阔起来。
从此,李攀龙隐居高卧,不再与名利场中的官员与富商来往,尤其对志趣不合者,更是闭门不见。只与志趣相投的文朋诗友听琴赋诗。
一些达官显贵以被李攀龙接见为荣,学人士子更以其品评来衡定自己的身价。因此“闻望茂著,自时厥后,操海内文柄垂二十年”。
白雪楼,俨然成了李攀龙自由自在的精神别墅。
过了几年,李攀龙将此楼变卖,又在百花洲东岸的碧霞宫附近筑了第二座白雪楼,该楼又称:青萝馆。
白雪楼四周荷叶田田,芦荻苍茫。
此楼有三层,底层为客厅,中层为书斋,上层为李攀龙爱妾蔡姬的闺房。
李攀龙在外任和家居期间,身边都是由侍妾蔡姬悉心照料。
李攀龙在百花洲上的白雪楼里,有红袖相伴,沉浸在诗词书画金石声乐之中,怡然自得地过着隐居的生活,只与诗坛旧友、门生故旧以及后来的慕贤者相处,不与权贵往来。
遥想四百多年前,水势浩渺的百花洲上,有一座居水中央的白雪楼,无桥可通,仅一小船往返其间,来访的客人,要先在岸上通报姓名,试其诗文如何,等待楼上的李攀龙许可之后,才解船相迎,累日不倦,诗酒酬答。若是达官显贵慕名前来探访,李攀龙都懒得搭理,只是让仆人回一句“主人不在”,就轻松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此性情中人,活得真洒脱。
这才叫风流。
这才是有风骨的文人应有的做派。
这种从骨子里头透出来的清高,是古今济南文人特有的标志。(济南日报 作者:陈忠)
本文来自【济南日报-爱济南】,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