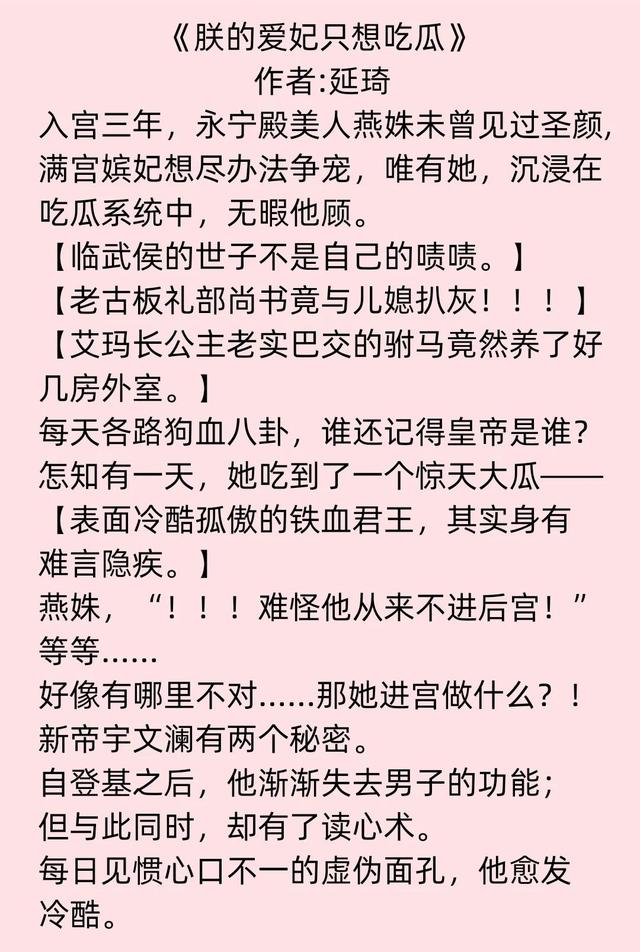“坐班儿”,应是大多数看守所管理在押人员的一项主要内容和方式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放风”时间,绝大部分就是“坐班儿”了所谓的“坐班儿”,就是一个屋里的人按照“大班儿”的安排,分前后几列、左右对齐,坐在“大通铺”上要求双腿盘膝、腰板拔直,就像和尚、道士打坐一样,不许随意说话和走动即便去厕所方便时也要向“大班儿”打报告后才能进行没有过经历的,一个“班儿”坐下来,不让你腰酸背疼腿抽筯才怪,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监狱里的一些往事?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监狱里的一些往事
“坐班儿”,应是大多数看守所管理在押人员的一项主要内容和方式。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放风”时间,绝大部分就是“坐班儿”了。所谓的“坐班儿”,就是一个屋里的人按照“大班儿”的安排,分前后几列、左右对齐,坐在“大通铺”上。要求双腿盘膝、腰板拔直,就像和尚、道士打坐一样,不许随意说话和走动。即便去厕所方便时也要向“大班儿”打报告后才能进行。没有过经历的,一个“班儿”坐下来,不让你腰酸背疼腿抽筯才怪。
“怪兽”们都很主动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黑大胖子则让我坐在了靠墙边的一个位置。我当时并不知道“坐班儿”是什么意思。只学着他们的样子,双腿盘上,老老实实的、耷拉着脑袋坐在了那里。
这个时候已没有了电视的播放、“怪兽”们的吵闹声,整个屋里算是真正的安静了下来。安静的几乎让我害怕,让我感觉就是大战爆发前的短暂沉寂。尽管如此,连日的审讯情形还是有了时间趁机侵入了我的大脑,受人侮辱、诓骗的景象又在脑海里重演。
“不会被抄家吧?、再审问时,我该怎么说?、会不会再连累更多的人?外面是什么情形?父母妻儿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外面的各种消息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难道这样的日子不像人死后被埋进活棺材里吗?里面的看不见外面,外面的又不能看见里面,里外不相见,有如隔世一般?……”一个个没有答案的问号向我纷至沓来。对自己之前表现产生出的种种懊悔、对自己日后种种不可预测结果的恐慌、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悲哀也不约而至。
这哪是“坐班儿”,简直让我如坐针毡!我不仅双腿麻木,就连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和战栗了!
“谁是孙衍哪?”声音一点儿也不大,还有些亲切,但却把我吓了一跳,心里轰的一下。经过那几天几夜的“捶炼”之后,我的胆子极小极小了,稍大一点儿的叫我名字的说话声都能让我心惊肉跳。顺着声音一看,铁栅栏外一位五十左右的警察正拿着眼睛向屋里扫描和张望着。
“孙衍,所长叫你!”“村长”美滋滋的在最后一排的床上喊我。
我不知是喜是忧,但却连忙站起,不顾麻酸的腿脚,趿拉着鞋、慌慌张张地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铁栅栏门前。
那位四、五十岁的警察面带微笑地上下打量着我,问:“你叫孙衍?”
“嗯,是我。”在一个小小的所长面前,我竟有点手脚无措了。
“怎么样,挺好吧?”所长笑眯眯看着我。
“这是什么话?被发配到这里还能说挺好?这是不是在奚落我啊?”我听后心里感到很气愤又很别扭。但我知道他肯定是在慰问我。
“还好。”好长时间没有人那么关心似的和我说过话了,我还得表现得受宠若惊。
“好就好,那就好好待着吧。”所长没有再问我什么,而是别过脸,冲着“村长”招了招手,示意他过去。
“这位得照顾好了啊!上面有交待。”所长用眼睛扫了我一眼,对着“村长”发话,口气毋庸置疑。
“放心吧,绝对受不了委屈!”“村长”殷勤地点着头,回答的也很快,也没有了那趾高气扬的气势。等所长走时,他还调皮地冲着所长的背影敬了个滑稽的军礼。
所长的到来和他与“村长”说的一番话,在我心里折腾了几个跟斗。几个好哥们弟兄的身影同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自作多情的认为,一定是他们打过招呼才会发生那样的场景!危难时刻见真情啊!一股热流注入了我的心底。
所长的话犹如圣旨,马上在我身上起了作用。
上午“放风”回来,“村长”便来到我身边,态度比较温和地告诉我,说当天看在我是他“上级”的份儿上,没让我擦厕所就算给我面子了。有了所长的话,擦地也不用了,每天和那几个老人儿一起把床单抻平、铺整齐了就行。“村长”这样的安排,基本上就等于我不用干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在他们嘴里,由“新来的”也变成了“镇长”。
我的老天!镇长可是对镇政府一把手的称呼,称呼副镇长一般都在前面加个姓或名字。干了三年乡镇的我都没能让人称呼上一个“镇长”。这里一下就把我给“提拔”了。我当时心里还真有点儿小满足和小确幸。
但,这种满足和确幸并没有维持多久,下午的一个传唤便让我的心又是一片拔凉。
“孙衍!”
大约两点半多钟,一名狱警隔着铁栅栏叫我的名字。突然的一声呼唤,又吓的我“轰”的一下打了个激灵。和上午的所长一样,狱警边叫着我的名字边拿眼向屋里踅摸。就在我惊慌失措时,“村长”走到我身边,慢慢地说,“别怕,镇长,你‘提讯’了。”
“‘提讯’?什么是‘提讯’啊?”我嘴上问着“村长”,心里在犯着嘀咕。
“快去吧,不是公安局就是检察院的。”“村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拿眼看着门外的警察催促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