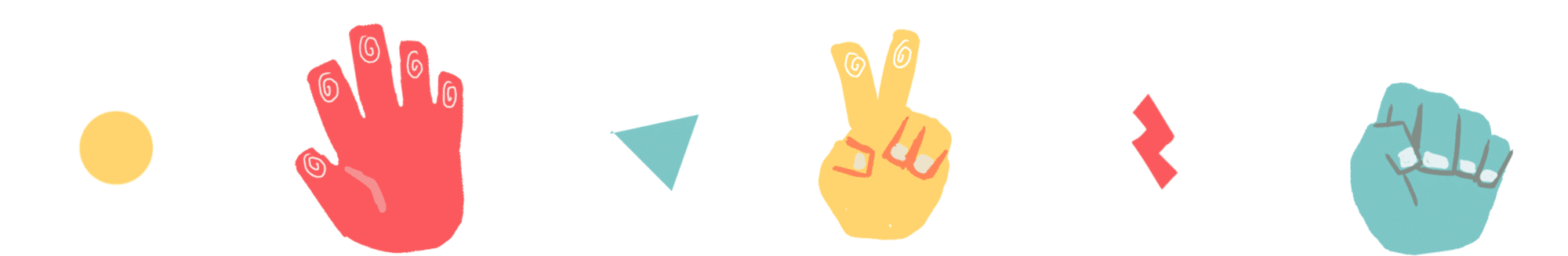冬天是寂寞的,
高楼改变不了什么。
有人枕着黑夜,
听风怎样把世界吹空。
有人走向荒野,
看生命如何真实而陌生。
冬天正在做梦,
梦见更多更严厉的冬天。
地平线上,
仿佛永远有一列火车,
满载空空的记忆隆隆而过,
而过——几点浮游的灯火
令世界恍若失而复得。
撰文 | 三书
塞外风雪像一场梦魇
《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
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
聒碎乡心梦不成,
故园无此声。
长相思,又名“吴山青”、“越山青”、“山渐青”。相思如江水,日夜流未央。流向何方?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相思随着长江水,流向江南的方向。
纳兰性徳却走向山海关之外,在冬天,水不绿,山不青,亦无人为他泪盈。他因扈从康熙皇帝出关东巡而离开京城。
“山一程,水一程”,风雪凄迷中,行军的队伍,跋涉了一程又一程。榆关那边,已觉很远,然而队伍仍朝着那边的那边,不停地行走。此身跟着队伍,向榆关那畔行,这是身的无奈,更是心的悲哀。
寒冬凛冽,万物闭藏的季节,人在此时应该围着炉火而坐,而不是在塞外艰难地跋涉。
天黑前,队伍在旷野扎营。军营之多,远望灯火如点点繁星,这个场景可能有些人为之光荣,但对于诗人,对于一个悲悯的人,那是一种愚蠢的光荣。诗人看到的“夜深千帐灯”,实则是天地无情,是人的悲剧处境。在风雪的威严统治中,千帐灯点亮的不是光明,反而是人类的弱不禁风。点点星火随时会熄灭,一旦熄灭,所谓世界,将即刻跌入宇宙的黑暗。
纳兰平居感怀之词,多哀感顽艳,塞外之作,笔力却异常矫健,境界转而壮观,此亦江山之助也。塞外的粗旷和蛮荒,在词人笔下激荡出一股遒劲的力量。
“风一更,雪一更”,难以入睡,诗人整夜在听,听风雪交加的酷寒,听着长夜漫漫。风雪呼啸,一更又一更,似有无数恶灵,哭嚎飞跑,一群群奔过广漠之野。
祝福在风雪夜安睡的人,祝福他们的梦不要被吵醒。在这样骇人的冬夜,独自醒着是悲哀的。
梦既不成,乡心又被聒碎,叫你无可逃避。不仅因为风雪声音之大,更因这样的声音在故园是没有的。“故园无此声”,绝域之风,像一场可怕的梦魇,把故园吹到天边,把乡心吹散。

纳兰性德像
归梦隔狼河
《如梦令》
万帐穹庐人醉,
星影摇摇欲坠。
归梦隔狼河,
又被河声搅碎。
还睡,还睡,
解道醒来无味。
仍是1682年,仍在塞外行军途中,已至辽东。这个夜晚,队伍驻扎在白狼河畔。
大约东巡行将告终,诗人的心情变得轻松。皇帝入夜大宴随从,大家坐在圆形的毡帐里痛饮,但见“万帐穹庐人醉”。饮罢,踉跄着步出营帐,抬起迷离醉眼,仰望星空,看到一幕奇景——“星影摇摇欲坠”。此景非饮醉不可见,此句非亲临塞外、亲见壮阔星空不可得。
夜里,或许因为饮醉的缘故,诗人顺利入睡。他做了个梦,梦见归家,却半途而醒。“归梦隔狼河”,故园已远,狼河之险,纵使梦魂也难以逾越。
河声喧响,响彻静夜,惊醒了诗人,搅碎了他归家的梦。
不想醒来,却醒来。醒来后,唯有寒冷与孤寂相伴。“还睡,还睡”,不如睡去,不如回到梦中。然而,河里奔腾的狼嚎,能叫他睡着吗!

朱耷山水图
入夜空城黑
《菩萨蛮》
黄云紫塞三千里,女墙西畔啼乌起。
落日万山寒,萧萧猎马还。
笳声听不得,入夜空城黑。
秋梦不归家,残灯落碎花。
此词仍是随帝巡边时所作,不过这次是在近边,是在秋天。
紫塞指长城。秦筑长城,因土色紫,故称紫塞,汉塞亦然。不论后来土色是不是仍紫,云是不是仍黄,“黄云紫塞”这四个字,这两个事物命名,却能让人顷刻感觉到边塞的苍茫气象。
“三千里”,不是夸饰,而是边境在想象中写实的延伸。辽阔真辽阔,难守亦难守。女墙指城墙上凹凸的短墙,乌鸦“哇”地一声飞起。注意是从西畔飞起,时值秋天,西边可是萧杀的方向。近在眼前的女墙啼乌,给远在天边的黄云紫塞,带来一个虚幻的深度。
“落日万山寒,萧萧猎马还”,此二句雄浑莽苍,直追盛唐。此处让人不能不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子昂当年所登若非幽州台,纳兰所在若非紫塞,岂能有此天地悠悠独立苍茫的千古之慨?
入夜,宿于边城。城中并非没有居人,但由于太静,太黑,太冷,因而形同一座空城。荒凉黑静之中,飘来缕缕笳声。听不得,还是不要听了,那笳声把夜吹得更黑、把城吹得更空。
纳兰扈从巡边,思家情切,夜则冀于梦归。然而,偏偏总是梦又不成、灯又尽,独醒愁坐,无聊赖地呆看“残灯落碎花”。
黄云,紫塞,千里,啼乌,落日,萧萧,猎马,笳声,空城,残灯……词人对这些事物的看见和命名,精确地呈现出塞外秋天与边城寒夜的质朴面貌,以及自身在客途中与之遭遇的他者心情。

董其昌《枯木寒林图》
当时只道是寻常
《浣溪沙》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以上三首边塞词,均作于其妻卢氏亡故之后。故可想见,词人归梦难成的心情并非完全起于绝域的外境。据说卢氏多才多艺,与纳兰结婚才三年便撒手人寰。这首《浣溪沙》为悼亡词。
任何一段欢乐时光,失去以前,谁不道是寻常?即便当时并不尽是欢乐,即便卢氏并不多才多艺,当那段时光永远逝去,隔世回望,一个个平凡的细节,无不绽放出惊人的美。
家里添一个人不觉多多少,走一个人却立刻空很多。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西风吹起,词人伶俜独立,身心俱凉。然而更凉的是“谁念”,更无人念其凉,才是彻骨的凉。
萧萧黄叶,如风中的言语,如孤寂的记忆,片片飘向紧闭的疏窗。残阳余晖,一贫如洗,时间正在生锈,往事的碎屑闪闪发亮。
那是春天,当他喝醉了酒,她总是轻轻说话,轻轻地走,怕惊醒了他的醉眠。但他当时只是半睡,所以记得她轻轻的样子。还有赌书泼茶,此类日常生活的闲情雅趣,李清照与其夫有之,沈三白与其妻亦有之。概神仙眷侣皆有之,亦皆难得长久。
笑影犹在,茶香犹在。一阵冷风,只是瞬间,黄叶就落满他的身边。只是瞬间,家就成了一座废园。

吕纪《寒雪山鸡图》(局部)
写在冬天的悼亡词
《临江仙·寒柳》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
疏疏一树五更寒,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
湔裙梦断续应难,
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清代词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此词曰:“言之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并推为纳兰词集《饮水词》压卷之作。
此词借柳伤怀,所怀者谁,说法不一,分歧在于谁是湔裙人。关于“湔裙”,典故有二:
一为李商隐在《柳枝词序》中所记之事,即洛中里女子柳枝与商隐之弟李让山相遇相约,谓三日后她将“溅裙水上”来与他相会。如此则暗指情人,此词所赋便为艳情。
二为《北齐书·窦泰传》所记,窦泰之母有娠,期而不产,大惧。有巫告之曰:“渡河湔裙,产子必易。”泰母从之,俄而生泰。后成风俗,谓女子有孕,至河边洗裙,分娩必易。如此则喻其妻卢氏难产而死,便为悼亡词。
以纳兰对卢氏的深情,以及词中似淡实浓的思念,在此取悼亡说。
弱柳的飞絮飞花,如浮世一场春梦,空缱绻,徒风流。在冬天,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更有“层冰积雪摧残”,仿佛连梦痕都被冰封,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疏疏一树,孑立于五更的严寒,明月下,清晰如一个故事的骨架,一艘沉船的残骸。然而痴情者“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虽已憔悴,却仍相关,仍是当年明月,当年柳枝,仍是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繁丝指柳叶,柳叶比眉毛。与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样,失去后以缺席而从记忆中复得。柳叶落尽,转而更忆春山,亡妻逝去,她的样子也在追忆中愈加清晰。
湔裙梦断,李商隐的典故似更浪漫,不妨拿来用在这个梦里。天上人间心有灵犀,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盼望在梦里相见,聊慰相思,然而好梦易断,再续应难。
“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西风萧瑟中,愁眉独坐的那人,似他,似她,似一个早就把有情众生都写了进去的故事。
纳兰性徳出身与皇族沾亲,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十七岁入国子监,十八岁中举,次年成为贡士。后殿试考中二甲,二十二岁即获赐进士出身,深受康熙皇帝赏识,并作为贴身侍卫多次扈从出巡。
纳兰虽以词名于今世,然其学识广博著述颇丰。一生笃意经史、书法、诗文,建藏书楼“通志堂”,坐拥古书万卷。曾耗资四十万金,编辑宋以来诸儒学经之书《通志堂经解》共1860卷。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推崇纳兰词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称其词之好,在于“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 故能真切如此。”
《浣溪沙》词曰:“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夜半闻笛,月胧明处,暗自惆怅落泪,此中深情,对谁也说不明。他悲伤的不止这个叫纳兰容若的自己,从横笛的断肠声里,他听到千千万万个人,在把各自的平生追忆。
纳兰一生荣华,却似全不在意,唯情重如此,读《饮水词》可知。年仅三十,终以情死。
作者|三书
编辑|张进;李永博
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