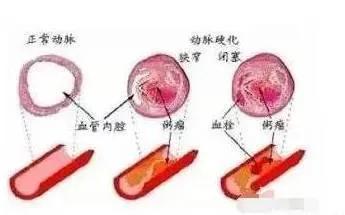从柳子厚的《渔翁》到梅庵琴歌《极乐吟》——藏着一个中国古老的哲学意蕴
柳宗元素善以山水为诗,孤高峭拔,清俊落寞,世人谓"独钓寒江雪"者,子厚者也,人间少有之痴子也,笔者素来爱读《江雪》、《渔翁》之诗歌,嗟叹之余,觉诗中有一画,画中有一人,此人是谁?渔翁,抑或是柳子厚?似乎柳宗元的诗歌宛如一幅自画像,而笔者却读出了千百年来的一个人间,一个读书人的命运之轮。
笔者想写下自已的感想,以《渔翁》一文为例,其文如下: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首先,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天际间,一叶孤舟,江流,渔火,夜泊,在西山之岸。晨晓,炊烟,汲湘江清水,燃孤楚之竹,生火果腹,渔翁也。一昼,一夜,交替也。渔翁撑起篙,此刻,炊烟散去,旭日升起,欸乃一声,唤醒山中猿鸟,水中游鱼,不见人影,早已顺水流下,空闻山间回响。只一片孤云。
民国时期的梅庵琴谱将《渔翁》收录,改名《极乐吟》,并为之配上古琴曲,曲末评语:"本曲聊聊数句而音节刚劲,风格甚高,恰如子厚文气,不同凡响,峰回路转,别有天地,于此曲见之。"诚如是,"峰回路转,别有天地",是气象、境界之大,落笔即心声,亦是诗人命运自现,如岑参"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初",不是为了写"峰回路转"而写"峰回路转",其中意蕴,别样深沉。"音节刚劲,风格甚高",柳宗元风格也。
其实柳宗元《渔翁》的诗歌中,可以看见中国的一个哲学背景——"儒"与"道",抑或是说,这是这是千百年的文人无法摆脱和承载的命运之负担,是一个悲剧。现在笔者开始正文:
一、《极乐吟》之"极乐":众窍自鸣,而悲从中来正如文章标题所写——从柳子厚的《渔翁》到梅庵琴歌《极乐吟》,何以就换了一个名字?,极乐者,乐极生悲也。中国文学早早显示出此端倪,自《楚辞》以来,《九歌》便有"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于相逢之际的乐极生悲,魏晋更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之忧,以及陈子昂"独怆然而涕下"的落寞……《渔翁》看似描写了一个"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被遗忘的至美人间,实则,恰是柳子厚欲求超脱而不得,悲中求乐,乐极生悲之吟游天地之挽歌。
柳子厚是一个儒家卫道士,但是这篇山水诗歌却写了出了道家"天籁"之境界,这就是"极乐"哲学悲剧的根源所在:我们来看诗歌"欸乃一声山水绿"一联,借用王国维之语可以说是"境界全出","欸乃"渔翁之高歌声,这一声恰巧在黎明和黑夜交替之际,昼夜转换,山水明朗,似生机乍然复苏,可以说是全诗歌的高潮部分。在这个部分之中,"欸乃"之声虽然是人声,但是不是可以人为,不是借助外力,而是人发自肺腑之声,是山水天地的代言,声落景色明,"山水绿"一诗眼,可谓是动态与静态之美水乳交融。是"大音希声,故听之不闻,大象无形,故视而不见",用在这里,意思是说人的"欸乃"之声自然到感觉不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似乎就是其中一部分,也感觉不到了。郭象说:"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为何?因为人融入自然,拥有了天地,又有了一切,是最高层次的美,所以人间极乐,此景只应天上有!
然而庄子的"乐"是忘了社会才能到达的,柳子厚是一个儒家卫道士,他忘不了人间,所以,儒家和道家的矛盾就在这里浮现,借庄子的话说:"山林与,泉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哀又继之。"

《渔翁》看似描写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但是却到处留下的人间的足迹,甚至是作者自己的心灵轨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从物我关系的表现效果的角度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主观性含蓄隐蔽,虚浑冲淡。可以说《渔翁》里全然看不到作者柳子厚的悲喜交集,展现一片天地万物与人融为一体的境界,是无我之境。但是,王国维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在"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两句中,谁在看?柳宗元。云"无心"?其实是柳子厚对于无心的写照,不排除他真的沉醉自然,但是就当时他被贬的境遇来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恰是他内心"郁结"的写照。所以,即使人工描绘再完美无痕迹,还是让我看到他欲得解脱的一面。
这就又是儒道的矛盾所在——这种"有我"来自哪里?来自"人间",一个背负着各种名与利,社会责任的世界,摆脱不了,才导致诗人歌颂自然,歌颂自然而处处"有我"之影子。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和韩愈一样,体现了中世文学分化时期诗文分化局面,他一面作文拥护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面又写诗歌放逐自我,这种矛盾的存在,也导致诗歌处处有社会价值失意的色彩。

在西方文论里,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说":是构成一种超给新内阁的共同心理基础,而且普遍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前面在第一标题和第二标题分别以道家和儒家为视角、出发点,写了两者之间矛盾根源。其实,就像荣格"集体无意识"说的那样,儒家和道家的矛盾,不仅体现在柳子厚一个人身上,还体现在千千万万儒家道家合流的哲学背景下的文人。
儒家和道家的合流是在百家争鸣的末期,也就是秦大一统到来前夕开始出现的,在东汉时期又经过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改变,魏晋思想动荡的变迁,最终形成确立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命运的悲剧——历代文人看不到"人"的价值地位,一味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但是每逢失意落寞,却又将自己寄托在"文"的世界,一个自我的形象的投射。前百年来,左思、鲍照、谢灵运、李白、关汉卿、纳兰……他们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但是,始终没有走到将顺从"人"出发去思考一生,只能活在个体和群体的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