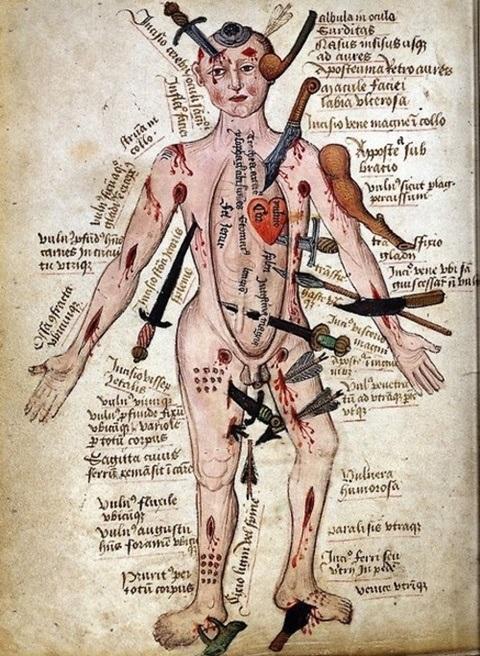激素的副作用是很大的,在平时生活上,我们要是去长期使用一些外用激素类的药物,还是会因此造成身体的皮肤之内吸收进入血运循环,引起糖尿病、高血压、骨质疏松、无菌性骨质坏死、肥胖、多毛、痤疮、钠潴留、水肿、血钾降低、月经紊乱、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等病症。
较长时间或短时间大剂量注射或内服激素,可对肾脏本身造成一些损害,如加重肾小球疾病蛋白尿、加重肾小球硬化、易致肾钙化或肾结石,诱发或加重肾脏感染性疾病、引起低钾性肾病与多囊性肾病等。较长时间给予较大剂量的激素还会引起机体糖、蛋白质、脂肪及水电解质等一系列物质代谢紊乱与体温调节紊乱,会破坏机体的防卫系统和抑制免疫反应能力,严重抑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因而可引起一系列更严重的副作用和并发症,有些并发症可以直接威胁到病人生命。
虽然患有肺纤维化,虽然明知抽烟会加重肺的负担,但方渤依然烟不离手,他需要通过抽烟来释放自己的苦闷。
他们是300多名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定点免费治疗和生活补助
每周四下午,望京医院二楼骨科门诊最南侧的诊室门口总会挤满不少人。这些从北京各区县汇聚而来的患者虽然年龄、性别各不相同,却有着一样的病症:股骨头坏死。
55岁的杨志霞就是其中的一位,如今,她的病情已经扩展到三期——股骨头已经开始塌陷,在不少医院这意味着已经需要进行关节置换。
杨志霞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非典”。
事实上,这个每周四下午的门诊正是专门为杨志霞和她的“非典”后遗症病友们开设的。这些闯过了生死线的非典治愈者并没有能够逃脱“非典”的阴影——治疗时激素的过度使用使他们患上了“非典”后遗症。
“‘非典’后遗症患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医务人员,一种是社会人员也叫非因公人员。”门诊负责人、望京医院骨科大夫陈卫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统计名单上的非因公患者大概是150多人,因公医务人员患者人数相仿。
尽管人数并不是很多,但这并不应成为杨志霞们被遗忘的借口,相反,他们更加需要获得社会的关注——这些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饱受创伤的人们不仅要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还需要面对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而无法赚钱养家甚至连生活都无法自理的窘境。
几年来,政府也做了包括定点免费治疗以及进行生活补助在内的诸多努力,但这并不能打消杨志霞和她的病友们对未来的忧虑。他们自己也在努力着,希望能够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有一种可靠、长效的机制可以给予他们足够的保障。
“你说这一家子这日子怎么过。”
当记者第一次见到刘平的时候,杨志霞正在和她说话。和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刘平也是因为“非典”后遗症才认识的杨志霞。
不过,患有“非典”后遗症的并不是刘平本人,而是她34岁的女儿吴洁。自从女儿身上的骨关节开始慢慢坏死甚至生活难以自理之后,刘平就挑起了照顾女儿的担子。
“我女儿是2008年生的孩子,孩子全是我带的。我不光是得带孩子,还得伺候她。穿衣服、端饭、上厕所、提裤子都得是我,就这么伺候这一大一小。”
刘平说,如今属于重残的吴洁全身多处骨关节坏死,不仅不能负重,几乎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包括给孩子喂奶。
“有一次我女儿给孩子喂奶,我在厨房炒菜,她胳膊抱不住孩子,孩子就掉地上了,就哭。她趴地上,抱不起来孩子也哭,我在厨房听见都哭了就顾不上关火了赶紧跑出来,把小的抱起来,把大的牵起来,结果菜锅就着了。你说这一家子这日子怎么过。”
由于自己的身体也渐不如意,63岁的刘平担子挑的越来越吃力。而现实却是,每周四从位于北京西南角的卢沟桥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位于北京东北角的望京医院拿药,几乎可以算得上一周当中她最轻松的时刻了。
杨志霞住的要近很多。从前两年开始,杨志霞就离开自己在东四的老家搬到望京儿子家和儿子同住。因为儿子并不放心母亲一人在家,而且母亲的身体也在每况愈下。
除了股骨头坏死,杨志霞现在身上还有十多种病,“双肩坏死、肺纤维化,这些后遗症是‘非典’直接导致的。还有子宫肌瘤、乳腺增生、严重骨质疏松、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是肝囊肿,然后去年有了胆囊肿,而且头两年查都是一个,今年我住院一查全都是多发。”
杨志霞每次吃药也是一把一把的,她掰着指头跟法治周末记者算:生脉胶囊一顿是三粒,钙片一天一粒,阿司匹林一天一粒,血脂(音)一天一粒,参松养心(音)一次两粒,补心颗粒一次一袋,还有一种中成药一次是10粒,都是一天三次……
“还有一些我就不敢吃了,吃了睡觉就不行了,因为我睡眠不好,还得吃安神的、调节神经的,因为我是重度抑郁症,要吃强制安定的药。”
“就那一年多,我就觉得活不起了。”
抑郁症在“非典”后遗症患者中普遍存在。据他们自己统计,像杨志霞这样的重度抑郁症患者能够占到整个“非典”后遗症群体的五分之二。
在“非典”中失去4个至亲的杨志霞曾经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我真的特别愁,我自己疼我都能忍,思念亲人我就不提了,这个按说在别人那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在我这都不成问题,排不上号。我的子女教育怎么办?俩孩子都处于没爹的状态,一个孩子还有病,将来我们养老怎么办。”
杨志霞说,在没有孙子之前,一度觉得活着没劲。“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挺着呢,是因为孩子没工作、没娶媳妇,那会有劲,得顶着。孩子娶了媳妇以后,就那一年多,我就觉得活不起了。”
小孙子的出世为杨志霞带来了希望。杨志霞笑着说,自从有了孙子,感觉自己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比以前强了很多。但失眠的状况仍旧没有改观,长期失眠使杨志霞看起来一脸的疲态。
方渤也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这个年过60岁的男人在这个群体中扮演着带头大哥的角色,他手里有着一摞厚厚的有关他们这个群体的各种材料。很难想象,这个带着一股子责任感的汉子曾经自残,甚至想过自杀。
2009年临近中秋的一个夜晚,方渤做了一件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在小酒馆喝酒的他砸碎了酒瓶,然后重重地朝自己脑门上戳了下去。这次自残扎伤了方渤的眼角膜,虽然不会导致完全失明,但他却无法兑现承诺,在死后捐献眼角膜了。
如今坐在望京医院的骨科病房里,方渤额头上的疤痕依然清晰可见,而曾经受伤的右眼,眼球已经变得浑浊。
“其实我觉着我活着一些承诺实现不了,但是我有些东西在死后能实现,我捐献我的遗体跟眼球角膜,我觉得这就是我死后能做的事,但是没想到就我那么一个不明智的做法,把我死后的承诺也给打破了。”
方渤说,他曾以为“非典”是一场噩梦,但是他错了。“最大的痛苦来自‘非典’之后。”
就在采访的当口,方渤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他原本已经戒烟,虽然知道抽烟会加重肺的负担,但他说他离不开烟了。即使上午他带氧气管的时候也依然抽烟,浓厚的烟味弥漫整个病房。偶尔有护士进来检查,什么也没有说。
“大家都认为这个病是疑难病。”
方渤是陈卫衡这里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在髋关节坏死之后,他的肩部也坏死了。
据陈卫衡介绍,股骨头坏死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迄今为止仍被公认为疑难病。
方渤曾经为了寻求“解药”,做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2004年,方渤接受了全国首例双侧股骨头植骨手术,不过,这例可能为骨坏死患者治疗带来破冰的手术并没有能够遏制住骨坏死趋势,“股骨头还是塌陷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方渤陆续接受了两侧股骨头置换手术,将人工的股骨头植入体内,替换掉已坏死的部分。而目前,150多个非因公患者中,有大约百分之十的患者像方渤这样,换了关节。
“这个数据不像普通患者人群换关节的比例那么多。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诊断早治疗早的原因。”陈卫衡解释说。
陈卫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股骨头坏死分为四期。四期最为严重,必须要换关节;三期的时候股骨头就已经塌陷。“大部分医院认为三期就已经该换关节了,我们医院还是尽量的保住关节、留住关节。”
相比之下,一二期的症状要乐观一些。“一二期的患者通过治疗能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没有症状,就是不痛了,另外一个就是功能保持的比较好,力量也够,活动量也够,走路没问题。”
不过,对于方渤来说,一轮接一轮的手术没有重新换来健康。“双膝骨坏死”、“双肩骨坏死”等症状接踵而来。这一次住院就是因为入冬之后方渤感觉肩很痛,所以来治肩。“我早上起来洗脸,都不是手找脸,而是脸去找手,因为胳膊抬不起来。”
虽然方渤的病情很重,但陈卫衡说,相比普通同类病的病人,“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病情恢复的还是要好一些。
“当然了,每个人的病情轻重本身也不一样,确实也有一部分病情已经比较严重,已经换关节了,但大部分的关节还保留着,大概处在一种基本生活还是能自理,但是劳累、变天时还会有症状,比如疼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还会来这里拿点药吃一吃,但平时也都没事。”
“但这些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
在陈卫衡这里住院,方渤是不需要花钱的。
“治疗费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国家全包,也就是说本人不花一分钱。”陈卫衡说,费用主要出自医保和财政,比如有医保的病人,医保中心报销公费的部分,自费的部分则由卫生局报销。
2004年3月,卫生部成立了一个6人专家组,并在随后发布了一份“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名单。“名单是动态的,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定期诊断,如果确实有“非典”的病史,又有股骨头坏死的病的,就可以进名单。”
如今,在这个名单的人数仍有300多人。像方渤这样的非因公患者比前几年又增加了一些,但杨志霞说,依然还有不少“非典”后遗症患者因为病情不够严重而没有能够进入名单——比如她的侄子。
进入名单的人可以报销治疗非典后遗症的全部费用,但仅限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及精神抑郁症三种被政府认定的后遗症。方渤他们来看病的望京医院就是专门治疗股骨头坏死的市级定点医院。
方渤说,起初并没有设立市级定点医院,而是在各区设立的定点医院。但是他们发现区定点医院的医疗水平并不尽如人意,治疗也不够专业。“这些医院比较起来还是望京医院治得最好,因此我们这帮人从各区县的30多家定点医院看完了都转到这里来了。”
望京医院也专门为“非典”后遗症患者们辟出专门的门诊,“这样一来他们看病也比较方便。医院也是只给他们挂1元钱的号,就是象征性的收费,因为没这1元钱电脑没法开出名字。”陈卫衡说。
除了免费治疗,方渤和他的病友们还得到了生活补助:有工作单位的每年每人补助4000元,无工作单位的补助8000元。
从2010年起就因病失业在家的吴洁每年可以领到8000元的补贴,但这在刘平看来只能算杯水车薪。“我们那姑爷一个月就挣3000元钱,托儿费2500元。就靠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养活这娘俩。”
刘平说,老伴去年掉了好几颗牙,因为镶牙需要全部自费,为了省钱,至今也没有去镶。
杨志霞每年则只有4000元,办理了退休的她每个月还可以领到1000多元的退休金。不过,杨志霞同样觉得生活拮据。杨志霞说自己身上10多种病,只有3种认定的后遗症可以免费治疗,其他的只能走医保。
“政府是做了一些事情,但这些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
“也只有这两种力量联起手来,他们才能真的被温暖。”
方渤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没有工作的患者一年8000元的补贴,平均下来一个月才600多元。如果需要额外的治疗费用或者请护工,这笔钱根本不够。此外,他们的股骨头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像脆弱的石膏一样继续的塌陷下去,直到他们死去。
“我们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家族式的。一大家子人都有“非典”后遗症,谁照顾谁?”方渤说,他们现在就只能是病人照顾病人。“我们需要雇人,小时工、保姆、护工的费用不是我们自己能负担得起的。”
刘平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如果自己有一天真的老了,动不了了,该怎么办。“女儿子伺候不了我,她需要人照顾,需要我伺候,等到我动不了了,谁伺候我啊?没人伺候我。况且我女儿才30多岁,现在年纪大的后遗症患的都这么多病,以后怎么办啊?”
“我就觉得我早点死了,好别拖累孩子,反过来呢,我又怕死,我死了没退休金了,这娘儿俩吃什么?你说我心里多大的压力啊?我是想死不能死,想活活不了。活着我拖累孩子,我死了孩子没饭吃。”
刘平希望他们这个群体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帮助。“我们希望社会起码能关注我们。我们需要照顾,我们需要志愿者、需要义工。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资助。”
方渤也在寻求能够为他们这个群体提供足够保障的一种可靠、长效的机制。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专项基金,来为他们今后的治疗和生活提供相应的支持。如今,基金的事情已经开始着手。“一个是为了自己,一个是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方渤还跟记者列举了香港在SARS后的援助措施。香港政府于2003年成立SARS信托基金,非典后遗症患者最多可获援50万元。2006年,香港政府又建议取消50万元的上限,并计划向立法会申请,继续向基金拨款。
“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按有关的法律文件依法办事,对我们进行抚恤和补偿。”方渤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专业教授郑功成也希望政府能够为这些幸存者建立单独的救助机制,包括治疗计划和足够负担他们下半生的财政预算。
“大多数后遗症患者失去了工作和劳动能力,他们不能救助他们自己,所以只有政府和社会能够帮助他们。”郑功成说。“中国的医疗保障总的来说是在逐渐变好,但是我认为这些受害者要求更多的照顾是情理之中的。政府应该慎重考虑他们的请求。”
曾经也有媒体在评论中建议,建立一个长久的制度性的“后救援”,让“非典”后遗症患者感受人性的温暖和关怀。在建立来自政府部门的制度性保障的基础上,由民间组织完善至最细微的温暖与感动。“也只有这两种力量联起手来,他们才能真的被温暖。”
最近,除了基金的事,方渤还在忙着为一个白血病孩子捐款的事。“我们也是在和北京市残联沟通的时候才知道的。我们是一群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们也愿意去帮别人。”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平、吴洁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