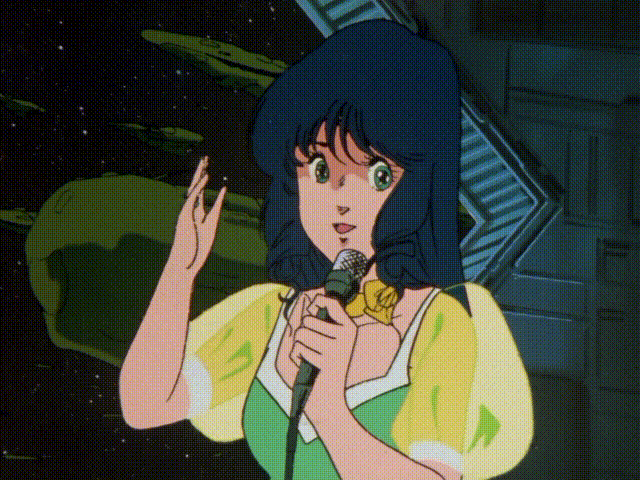初冬的北京,阳光是金色的。
坐在751偶然咖啡馆,姚谦回忆起十几年前,华语唱片最衰落的时期。那些日子,每一天,他都在“开人”。
时间有些遥远了,他还能记得当时台北的阳光,但他心里,对音乐,早就没了阳光。
今年62岁的姚谦,最近在做两件事,一是考虑自己的遗嘱。他没成家,没孩子。曾经的作品,版税、收藏,他打算交给自己弟弟妹妹的孩子们接手管理。
“我得承认自己老了,剩下时间和精力,更想用在旅行与阅读,家里有三个女孩子,她们需要学习点艺术史,不至于将来搞不清楚状况下,很低廉地把我半生苦练细选的收藏卖掉。”
另一件事,姚谦在逐渐找回,自己进入唱片行业之前,对音乐最初的爱。
比如,他以旁观者的心态关注音乐综艺,不再感慨歌手唱得怎样,或抱怨制作单位的水准高低。有作品邀约时,他选择与国外高水准的音乐人合作,完全抛弃对歌手现有人设的想象,“要回到最初的状态”。
过去三十多年,流行乐坛很多著名歌曲,都有姚谦词作。《鲁冰花》《我愿意》《原来你也在这里》《如果爱》《公转自转》《味道》《最熟悉的陌生人》……与此同时,他经历了华语唱片的发展、黄金时代与衰落。
期间,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其实误会了音乐,对唱片行业,不能算是正确的音乐产业的判断。
这些年,姚谦淡出乐坛,生活重心从台北转移到北京,双城生活转眼也十八年了。
他喜欢北京的阳光,“最喜欢背对着从窗口照进来的阳光看书,背被照得暖洋洋的,阳光把书上的字照得清晰异常,眼镜都可不戴。”
音乐之外,搞收藏、拍纪录片、写专栏、写剧本、出书……每个思考的片段,都是感受的重述,都是一首歌。
别人在他的歌里回忆生活,他把生活过成了歌。
“时代在变化,希望对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价值。虽然我并不富有。”

|经历唱片的衰落
“我最近看了《串流先锋》,很不错,我给好多人推荐。”
这是一部半传记半虚拟,讲音乐流媒体Spotify创业故事的奈飞剧。
20年前,台北维京唱片公司。姚谦坐在办公室,眉头紧锁,对面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进来,一个一个离去。一天又一天。
作为当时唱片公司总经理,姚谦每天都在“开人”。
同时,他和自己好友、雅虎在台湾的负责人,正打官司。
她以前曾经是歌手,后来到雅虎当总经理。雅虎上架了可搜索和下载音乐的程序,公司的音乐被侵权了,他要保护。
那些年,互联网盗版猖獗,人们轻点鼠标,音乐就飞进了千家万户,大家不再买唱片了。唱片公司的日子自然不再好过。
已在唱片公司工作十几年的姚谦,也不知道音乐的未来在哪里。
多年以后,姚谦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以为自己在做音乐产业,其实是个误会。
“我是用唱片的第一视角、思维在思考应对。我发觉很多判断是错的,我必须调整。”
2005年,姚谦开始渐渐淡出国际唱片公司,成立大熊星纯作音乐和音乐人经纪工作,逐渐回到做唱片之前的爱乐者。

画家刘小东为姚谦画的肖像,姚谦觉得很像少年的自己
|黄金时代, 每天都是惊喜
进入唱片行业之前,姚谦在台南昆山科技大学读书。
虽然学的是工艺设计,但他从小对文学、音乐更有兴趣。用他的话说,“音乐最涟漪。”
姚谦听了大量卡带。“尤其台湾版权比较松动的时候,听了很多西洋歌曲、日文歌。听凤飞飞、邓丽君,也喜欢听李泰祥。”
上世纪8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兴起,“大学生不听流行音乐,觉得那是靡靡之音,low,主张自己写音乐。”
但姚谦很喜欢,认为流行音乐有入世的浪漫,“凤飞飞唱琼瑶电影主题歌,我都听。”
今天谈起凤飞飞,他发现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那个时代,凤飞飞的口语化,独树一帜。当时的歌平仄对仗比较严谨,甚至俗套,她尽可能使其口语化。而邓丽君还是在老式平仄起伏里找唱的韵律。”
大学毕业后,姚谦在台南做汽车展示员。这份工作,他并不开心,还得了胃溃疡,回家躺了三个月。看电影、阅读、听音乐,等身体好些了,他一个人徒步旅行。
边走边思考,“年轻时,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开始投简历,从唱片公司、杂志、出版社到电影公司。
谁知简历寄出后,杳无音信。
“我意识到一件事,这些公司的地址都在台北,他们不会用台南的人。因为太远了。”
他跟父母说,“我必须到台北去。”
到台北后,姚谦住在朋友家的小阁楼。凭所学专业,他很快在一家餐馆,找到一份美编的工作,“设计海报、印刷。”
同时,他继续投简历,第一个就寄给了唱片公司。
三个月后,一家叫海丽的唱片公司给姚谦寄来了offer。
二话不说,他立刻从餐馆“撤了”,直接去了唱片公司。
海丽原本是家做卡拉OK的公司,有机会签了一个女歌手叫江玲,因为和有妇之夫谈恋爱,她此前沉寂了两年。
签约海丽后,江玲唱了一首名叫《分手》的歌。
谁料这首并不为迎合市场而作,更像江玲对自己感情宣誓的歌,再次翻红。
这是海丽第一次签约歌手,第一次做流行音乐。有了资金,海丽需要宣传人员。恰好看到姚谦的简历,公司觉得合适,就发了offer。
进入唱片公司后,能做喜欢的事,“每天都是惊喜,从选歌、录音、设计、包装、发行、宣传、接触各媒体等一条龙所有工作”。
当时《外婆的澎湖湾》的曲作者叶佳修也进入了这家公司。
叶佳修制作海丽的第二张专辑,名字源自席慕容的诗《无怨的青春》。这是姚谦第一次全面负责一张专辑的宣传,从文案、电台宣传……“那时没有分工,什么都参与。”
接着,海丽又签了其他主流歌手,从民歌进入到流行音乐。“那时候做了一些传奇人物,例如潘迎紫。”
海丽唱片,在一栋高档居民楼里。除了海丽,楼里还有其他唱片公司。
姚谦常在电梯口碰到其他唱片公司的人。也是后来姚谦工作最久,长达十年的“点将”唱片。
有一天,电梯打开,正好碰到点将的老板,他问姚谦,愿意来点将吗?
“为什么?”姚谦问。
那时点将旗下歌手张清芳,在第二张专辑时遇到一些债务、家庭,甚至还有官司问题。
“我们想找你来负责宣传,帮我们度过这段尴尬期。”
“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总是笑着,在公司和歌手关系最紧张时,也许是最好的事。”
多年以后,回想当时的情景,姚谦笑说,“这回答像赞美。”
不过,当时媒体评价姚谦,“就是一个笑面虎,其实心眼儿很多,永远无邪,见人就笑。”
台湾节目主持人张小燕评价姚谦的歌词,“最懂女人心”。实际上,从张清芳、王菲、林忆莲、萧亚轩……只因姚谦碰到的歌手,大多是女性。
但从与张清芳合作开始,姚谦不再满足宣传工作,他开始词的创作。
比如,江淑娜的专辑在收集歌曲时,童安格谱好了曲,公司等不及词作者交稿之际,姚谦已经写出了《今生最痛的歌》。
在点将工作近十年,姚谦合作了江淑娜、伍思凯、江蕙、林慧萍等红极一时的歌手。
1993年,姚谦为王菲量身定做歌词《我愿意》,不仅让王菲奠定了歌坛地位,也让姚谦成为一线词作家。
创作上,为了避免雷同,姚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比如林夕最强的时候,我一直想我不要那种很漂亮的对仗句,我一定要用叙事,然后结论,不要‘鱼在天上飞’,这的确很炫目,但这种技术要很强的文学阅读和能力的人写。第一,我没那个能力,第二我还是想忠于小津安二郎或者侯孝贤似的叙事法。”
姚谦写《我愿意》,是当年他在飞机上,看到报纸上刊登王菲回到北京,住胡同,倒痰盂的照片,有了灵感,想象这个歌手谈恋爱的心境,于是创作完成。
后来,点将唱片被百代唱片公司全资收购。姚谦去了新力(现在的索尼)唱片担任华语部总经理,造就了李玟、庾澄庆、王力宏等一批在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歌手。

|乐坛血雨腥风,差点跳楼
“台湾的黑道曾经很猖獗,曾有一个美国唱抒情摇滚的歌手,在后台被枪顶过脑袋,这种事都发生过。”谈及那段时光,姚谦直叹“血雨腥风”。
乐坛没那么好混。看上去有多光鲜,就有多不为人所见的险情。
姚谦担任唱片公司管理者时,每一两年,公司通过版权代理商,跟卡拉OK比价。
有一次,姚谦从公司下楼,一个绅士向他走来,送给他一个“礼物”。
姚谦抬头看他,“我不认识你。”
对方很礼貌,“帮帮忙,我们真的很好,这是老板叫我带给你的。”
姚谦打开一看,一颗钻石,很大,亮亮的。
“我坚持不拿,这等于给你现金。”
他转念意识到,自己的停车位被别人知道了。
这是姚谦少有害怕的经历。
比外界压力更可怕的,是他曾深陷抑郁,却不自知。
1998年,百代公司下属的维京唱片在亚洲投资分公司,邀请姚谦担任总经理,负责整个维京体系华语音乐发展事务。
新人推一个红一个,专辑出一张红一张。姚谦被外界誉为“乐坛伯乐”。最有名时,也是他最迷惘时。
当时姚谦面临几重问题,除了创始人意见不合,他签约了三个新人,萧亚轩、江美琪、侯湘婷。
尽管当时互联网盗版下载日益严重,并未影响维京唱片的业绩。
但面对时代的快速发展,歌手的更新换代,外商唱片公司对于营业数字的严控、艺人和公司人员增长的内部管理,姚谦工作繁忙,“那时心理压力很大,大到严重失眠快撑不下去,真的。”
“每天带着100个烦恼,喝酒昏沉沉睡过去,等醒过来,再把问题清晰地一条一条列出来。如此重复。”
有一天,姚谦突然想,“为什么要这么生活?”
睡不着,他干脆起来,到办公室处理事。那天,是凌晨四点。
楼很高,他走进办公室,就恍惚了,“如果跳下去,就没这些烦恼了。”
做卫生的阿姨看见有人在站在窗口,以为进了贼,大声地质问,“你是谁?”
阿姨的工作时间里,压根没见过姚谦。
就是这句“你是谁”,让姚谦瞬间清醒。
当时,姚谦在外界享有盛誉,“实际上,在公司要承担很多,你没办法分析、分享烦恼。如果纯粹就是逆境,反而是激励。但不是。”
压力如何大?
“外面说你过得很好,出一个歌手,红一个。有时,并不如意。比如公司一手打造的萧亚轩,曾红极一时,后有孙燕姿、蔡依林超越。这像宿命般,做张清芳时遇上黄莺莺、苏芮,做李玟时过到张惠妹。看似光鲜却从没轻松过。”
还有歌手在创作理念上发生了改变。“林忆莲前两张专辑卖得很好,到了第三张,她养孩子,对平淡生活有感悟,我也必须接受、尊重。尽管(这张专辑)很不商业,但也成了我至今最喜欢的一张林忆莲专辑。”

2001年,姚谦和维京唱片的同事们在北海道
|双城生活,双重观察
50岁后,姚谦退休了。
那年,他第一次尝试长篇小说,写了《脚趾上的星光》。他把故事架构在他居住多年、月月往返的台北、北京,两个家,同时也叙述了他近20年来,赖以为生并深刻观察的音乐与美术。
与其说,《脚趾上的星光》描述的是一对情侣相隔台北、北京的双城爱情故事,不如说,是姚谦寻找自己的一次回望。
正如姚谦本人的经历,从美术到音乐,从唱片的鼎盛到衰落,从台北到北京,从音乐里到音乐外。一明一暗,一暗一明。
751见面几天后,姚谦从北京回到台北。
这些天,台北小雨。多云转阴,阴转多云,多云转晴。
|对话实录
「文娱春秋」:怎么看如今的音乐综艺?
姚谦:纯粹从音乐流量考量,歌曲重复被使用,更多是为了造就视觉表演,太多过于技术炫耀的舞台反而虚无空洞了,没有了音乐最迷人的内在。所以我现在不从音乐工作者的角度看待节目,更多从节目分工,考虑他们的难处,比如一期节目八首歌怎么分配,一切与音乐无关。
「文娱春秋」:怎么看如今的音乐平台?
姚谦:国内网络音乐服务的营运方式,造成了目前国内华人的音乐状态,现在不是有才华的歌手消失了,而是平台造成的——互联网把音乐人的差异稀释掉了。音乐只是服务表演,国内网综和平台让纯听音乐和纯音乐人慢慢散去另找出路。
「文娱春秋」:《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落幕了,觉得怎样?
姚谦:枯燥乏味。但也有我很喜欢的歌手,比如郝云,他在节目里唱京剧,与张淇不同,更有血脉里的真实而非加油添味地演。比如郑钧参加综艺,我相信他是爱音乐的。摇滚是忠于自己生活的书写。特别是有了孩子后,男人不再是自己的人。郑钧永远是松松的,但他内心的汹涌还在,只不过,他把力气转移到修身养性,比如做瑜伽。我现在也做瑜伽,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他身在其中维持旁观的不亢不卑。为郝云被忽略了抱屈。
「文娱春秋」:关注周杰伦今年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了吗?
姚谦:周杰伦刚成名的时候,正好跟我住同一栋楼。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一个创作者到中年后,并不是努力与否的问题,而是自我心理上的设想,要在那些痛苦或挫折中再定义,特别是男性。周杰伦这几年有些变化,可能来自身边人的影响,比如喝什么酒收藏什么画——那些很虚无主义的需求。迷失是合理的,我也迷失过,但他在作品上怎么突破?人生的起伏,必须要坚持。当你是唯一的“王”,很容易被保护,也很容易被蒙蔽。
「文娱春秋」:为何说,多年来对唱片是误会?
姚谦:我曾以为自己进入的是音乐行业,其实并不是,我进的是唱片产业。音乐产业里以前最主流的是唱片,唱片把音乐产业变得价值化,无论CD、黑胶,还是卡带,都是通过“工业复制”把作品量化。当网络下载风靡后,不再用唱片的时候,又回到歌手用音乐的本能来产生收入。当音乐从音乐产业消退后,音乐产生的产值,有了很多方法。其中一个是商务定制法。互联网平台,只分给比如周杰伦、五月天等头部歌手,其他独立音乐人根本分不到钱。他们只有继续出作品,增长流量让自己有更多机会,或争取商务合作。
「文娱春秋」:最近李玟在《中国好声音》指责节目组不公平,怎么看这事?
姚谦:我从来没觉得不公平,事实上没那么不堪。节目要维持比赛的好看度,有自己的考量。现在找人才参赛,越来越难了,有人愿意参加,就提出条件。我跟李玟太熟了,她为人温和,不是一个强出头的人,以前出什么事都是她姐姐在前面,她不敢出来说。这次应该是工作结束后,李玟回去跟导演抱怨,被工作人员录下来放了出来。流量高的事,未必是事实。
「文娱春秋」:为何推荐《串流先锋》?
姚谦:这个剧特别好的原因,提出解决音乐人与平台之间矛盾的必要。音乐人在互联网平台是弱势,是贫穷者。如果未来法律制度可以更客观,音乐人有能力对抗平台的时候,创始人需要自我审查。目前国内很多音乐平台都在赔钱,事实上不是赔钱,而是你把钱分不均。当你把钱90%给了一个人,他两年交一张专辑,你都得乖乖认。但那些天天不停在平台上经营音乐的人,不容易被看到。音乐网站要服务投资人,需要达到数据指标,他们思考的永远不是音乐人和听音乐的人。更何况,我们现在中国音乐产业的经营者,基本上对音乐不尊重。
「文娱春秋」:《串流先锋》的最后,独立音乐人和Spotify的创始人对薄公堂。国内很多独立音乐人,也一直在找出路。
姚谦:音乐平台在国外就是本着科技产业服务音乐的运营平台,是以音乐版权的运作为本。国内则更复杂。早年唱片成产业是从演出开始,音乐人为有权有钱的人服务。平民百姓的音乐在民间散播,则通过民歌方式散播开来,民间自弹自唱不叫产业,是生态。直到机械工业革命后,唱片把它变成一个产业。现在互联网平台,把产业又解构掉,重新定义。定义的过程,影响了科技的变化。比如国内音乐网站,一直很难成熟、成功,因为平台的人建立音乐平台的目的,有的是“我的产业需要一个音乐来(支持)网站”,需要影射,要服务其他互联网产业;有的,则太理想,自已喜恶为主,又把情绪加进去,做人事的审判;要不然,就是交给奇怪的人管理,最后财务分析不挣钱,就被处理掉了——曾经有小音乐网站,生龙活虎,苦苦经营还蛮有趣,却活生生就被科技大鳄和金融高管给玩死了。
「文娱春秋」:回想过往唱片行业的经历,最迷惘的时期?
姚谦:裁人那件事情,我很不能适应。当时分三周,每一两天逐渐地裁,裁完再做人事结构,给老外确认。那的确很痛苦。我真的迷惘,是我在维京的后段、大熊星刚成立。我离开(维京)唱片公司前,我要让跟着我十年的这些工作人员一一拿到资遣费;以及我几乎把所有艺人的合约都做完了,最后我离开。我完全没有拿任何资遣费。那段时间,我开始经营大熊星,是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进入所谓的中年思考,也是最迷惘时。也是那时,我用了更多时间待在北京,台北、北京月月往返。男人的中年迷惘,事业,身体,还有一些自我的重新认识的焦虑。那时起,拍纪录片、出书,以及我开始把一些预算,更多放在旅行上,都是那段时间渐渐成型现在的我。
「文娱春秋」:怎么看一个词作者的社会责任?
姚谦:对他人有影响,我永远觉得这是一种很强烈的自觉,也是作词者的社会责任。人家把它(歌词)当信仰,当作生命的指引,是因为信任你。所以一定要小心,不小心就会变成别人的判断方法。
社会责任,是在我中年那段迷惘期,一个很大的人生思考。我还在做唱片公司的时候,那时MTV音乐录影很流行,有一次去餐馆排队时,看到连续三个M TV不是车祸,就是殴打、血流满面,要不就是癌症。那一餐之后,我回到公司,正好开主管会,我很慎重地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我说从今之后,维京音乐的MTV不能有打架到头破血流,不要有车祸死亡哭天抢地,不要有癌症,来博眼球这种事。我们要针对摄影美术,用好的艺术形态去创作。
「文娱春秋」:创作上,受哪些文学影响较大?
姚谦:诗、小说。我很喜欢张爱玲,她的故事又残忍又冷。而且我总觉得她是一个随时要对男人负责的女人。她文笔的经验,略带技巧,又不是只有技巧,她要说的很深刻。我写歌,我会从张爱玲文章找一些(查考),由景到情,是我常用的,对写歌是最好的方法。像现在窗外看起来天气好,突然下了雨,先说窗外,再说你昨天分手的时候忘了带伞。张爱玲的结构,光线移动,光移到靠着桌子的女人,然后开始写那个人在想什么,就像拍电影。我到今天为止,每次写歌之前都看很多诗,没目的地看,放松地看。
这些年我写的东西不多,尽可能往内发展,而不是煽情流量的角度。最近我又重看了朱天文的书和纪录片,她真的很深刻。
「文娱春秋」:最喜欢的诗人是?
姚谦:我很喜欢顾城,虽然偏执,他的诗是一个内向的人对生活感想的书写。我不是那么内向,内向的人是迷人的生物,他们产生的音乐,写的诗歌文字都很迷人。
「文娱春秋」:眼见无数明星高楼起,又楼塌了。怎么看他们的起伏?
姚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静默期,对当事者未必不好。如果以世俗或商业角度来看,都是很艰辛的心理自我调整过程。我自己也面对过这些事,所以我在看这些事时,我更多在想,也许是一个漫长的过渡,也许瞬间,你就要过渡,面对自我修炼调整。
「文娱春秋」:音乐之外,对艺术收藏,有什么观察?
姚谦:现在很多画廊、博览会的人,吃饭喝酒,拿到活赚钱,艺术品市场如同流水线。艺术市场比较复杂,有点像音乐产业从唱片到音乐平台的过程,收藏本来是少数人的爱好,现在变成全民娱乐,甚至更多年轻人进来。很多年轻的艺术家,画廊的经营,拍卖公司的经营已经进入了Instagram,这是很重要的宣传,拍卖行制造一个假数据,就像唱片、电影票房一样,来造成网络的口碑,变成大家都以为买了(画作),将来可以挣钱。
我喜欢美术,喜欢看美术史,艺术是我很大的阅读,比如收藏者的传记,上一代收藏的故事,我特别喜欢。甚至我会接手他们的艺术品,这种艺术的传承很有趣。同时,艺术让我增加了旅游,到全世界的美术馆看艺术,艺术又让我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世界。
撰稿|茜文
策划 | 文娱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