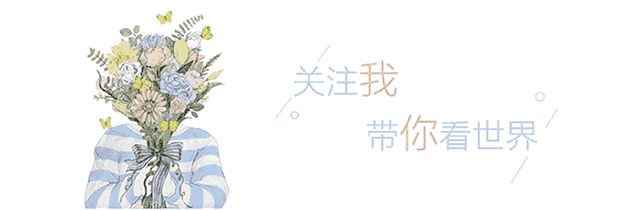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论语中的经典语句及体会?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中的经典语句及体会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卫君:姓蒯名辄,卫出公。
子:对人的尊称。这里是尊称孔子,老师您。
奚先:先干什么。奚:何,什么。
迂:本义是指曲折,绕远,引申义是言行或见解陈旧不合时宜,不切实际。
阙如:阙:阙疑。对疑难不明的事不妄加评论。
无所措手足,即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无所苟:没有一点随便、马虎的地方。苟:苟且,马马虎虎。
子路说:“卫国的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里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没礼貌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他的言论,容不得一点马虎。”
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公元前496年,卫灵公的太子蒯聩伺机刺杀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失败后,蒯聩逃奔宋国。不久,又投奔晋国的赵简子。
三年后,卫灵公去世,蒯聩的儿子蒯辄(卫出公)继位。赵简子想送蒯聩回国,蒯辄派出军队进行阻击,不让他的父亲蒯聩回国。
公元前488年,六十四岁的孔子在卫国,跟随的弟子有冉有、子贡、子路、高柴等,正赶上蒯聩与蒯辄父子争夺国君之位,史称父子争国。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卫出公蒯辄抛出“橄榄枝”,孔子会帮助卫出公做事吗?孔门四科政事科的高材生冉有,都不知道,其他的人更是难以明白了。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篇》)(冉有说:“夫子会为卫君做事吗?子贡说:“嗯,我去问一下。”)
也许子贡当时咨询这个话题的时候,子路不在老师身边。于是才发生了本章句《论语》记载的内容——为政先要正名。
蒯聩与蒯辄父子争国的过程中牵涉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孔悝。
孔圉(孔文子)娶了蒯聩的姐姐为妻,他们的儿子叫孔悝。孔文子去世后,孔悝执掌国政。卫出公十三年,孔悝的舅舅蒯聩悄悄返回卫国,和孔悝的妈妈串通,胁迫孔悝召集群臣发动政变,于是,蒯辄逃奔到了鲁国。
蒯聩与蒯辄父子争位的结果是蒯聩胜出。公元前481年,蒯聩取得了国君之位,即位为卫庄公。
了解了上面的情况后,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经文,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
子路问了:老师,卫国国君假若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里做起呢?
子路的问题是一个假设,如果用您的话,您该先做什么呢?我们一看,子路不愧是孔门政事科的高材生,一问问题就是关键性的。做政治,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譬如,国家发展方向、领导班子建设、军队保障、粮食安全、民生问题、区域建制、税收政策、外交方略等等。在这些问题中,到底该先做什么呢?
我们看孔子的回答:“必也正名乎!”孔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首先必须正名分。”
“必也”两个字,也就是毫无疑问的意思。孔子老师的答案太震撼了——“必也正名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正名。正什么“名”呢,或者说“名”该怎么正呢?这是本章句《论语》的核心!
一种理解就是“正”蒯聩和蒯辄父子之间的名分。
卫灵公死后,就位的应该是卫灵公的儿子蒯聩,由于蒯聩的刺杀南子被逐出,早已不是太子了。论资排辈就位的话应该是公子郢,但公子郢早已经看透了现状,决定不做卫国的国君。于是,南子等人就立蒯聩的儿子蒯辄,也就是卫灵公的嫡长孙继位,这种安排还是比较符合情理的。
最出人意料的事儿发生了:蒯聩想回到卫国当国君。一呢,他认为;这个国君应该由他来担任,等他做国君做腻了,再让给儿子也不迟啊。本来自己就不是太子了,自己的父亲死了之后,自己的儿子继位,对他来说也是最好的慰藉,但多年的逃难生活让他明白,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利,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二呢,他身不由己,自己在逃难期间,受到了赵简子的帮助,自己回来当国君,也好给对方一些补偿啊!从蒯聩来说,这就是“父不父”,父亲不像个父亲的样子。
蒯辄继位的时候,当时父亲已经不在卫国了。更何况自己已经就位,生米煮成熟饭了,名正言顺了。这时候,他的父亲回来争夺国君之位,该怎么办呢?摆在蒯辄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呢,派兵阻挡父亲的回归,这样自己就成了不孝之子了,一个不孝之子当了国君,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呢?这难以服众啊;二呢,自己让出国君的位置,让父亲来做,这样呢,晋国赵简子就会迫使父亲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会使卫国的利益受到一些损伤,这是对于国家的不“忠”!所谓自古忠孝两难全,这时候的蒯辄选择了派兵阻挡父亲的回归!对于蒯辄来说,这是典型的“子不子”,做儿子的,不像个儿子的样!
就这样,父子争国一下子持续了十三年。而这则《论语》发生父子争国的第五年。
正“名”的第二种理解;就是先正人心,正人的思想。人心正了,所谓“名”自然也就正了。
蒯聩蒯辄父子争国,根源在于他们的心!他们心中已经失去了人伦之道!父慈子孝,这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规律,是儒家提倡的伦常之道!按照儒家的观点;他们父子应该做到父慈子孝。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蒯辄刚当上国君的时候,派人迎接父亲回来做国君,一个人怎么能不让父亲回到自己身边呢?否则就是不孝。蒯辄做到了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大家一看,这么孝顺的人担任国君,这是老百姓的福啊,大家才会心服口服啊;如果儿子蒯辄做到了这一点,蒯聩会怎么想啊?自己的儿子那么孝顺,现在已经是卫国的国君了,是名正言顺的。自己该如何做呢?他早已经没有继承国君之位的资格了,还能忍心来抢夺吗?他会先还清赵简子的人情,然后选择一处地方养老,颐养天年!这就是父慈!我们看他们父子,父慈子孝了,还会争国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行为符合父子有亲(父慈子孝)、夫妇有别(夫义妇听)、君臣有义(君仁臣忠)、长幼有序(兄良弟悌)、朋友有信(朋友有信)这五伦关系,这叫有德。违背了伦常关系,就是没有德,没有德就是缺德!逆天理而行,也许会有一时的得志,但最终会遭受因果报应的。从蒯聩蒯辄父子俩的结局来看,也是符合这一点的。公元前478年,赵简子围攻卫国,卫庄公出奔,后来,客死他乡。公元前477年,卫出公蒯辄返回卫国,复位。
儒家的学说,其实就是伦常之道,就是讲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包括如何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蒯聩蒯辄的一念之差,父子争国,一闹就是十三年,受苦最多的还是卫国的老百姓。如果蒯聩行父慈之道,蒯辄能够行子孝之道,让老百姓买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历史没有如果的。所以说;圣贤的教育,是全社会都需要学习的教育,统治者更需要学习。
三呢,是正名分,也就是正国家管理的名分,包括典章制度,外交方略,经济发展等等。一切按照周礼的规定行事,引导社会上所有的人敦伦尽分,各守其位。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卫君让孔子帮助去治理,首先得给孔子一个名分啊,是做大司空、大司寇啊,还是出任国相啊。如果让孔子担当司空,这是掌水利、建筑工程之类的官职,你再让他去管理国家的刑罚,这就是名不正!谁会听他的啊?相反的,人们还会说孔子是六个指头挠痒——多那一道子!
我们知道;恢复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切需要从正名开始的。
听了老师的话,子路同学的反应太让人吃惊了——“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或许是子路同学没有完全领会老师的话!他所理解的,大致是,老师,人家卫出公请您帮忙治理国家,您说先正名!意思就是让卫出公放弃国君的位置,心甘情愿地履行好自己当儿子的角色,这怎么可能呢?
子路脱口而出:“有是哉?”
“有是哉?”是一个反问句,无疑而问,有这样做的吗?有这样的事吗?
我们要注意;一个人脱口而出的话,往往是力道十足的。就像同样是见到秦始皇出巡的车队,刘邦脱口而出的话是“大丈夫当如是也。”而项羽就截然不同了,他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接着子路又来一个陈述句,内容颇刺人:“子之迂也!”子路说了;老师您啊,真是太不切合实际了。这几个字十分传神,十分口语化,好像我们今天说的“你真是!”这很符合子路的个性。子路反讥的确有一些过分,意犹未尽,又来一句“奚其正?”如何正名,表面上是一个疑问句,骨子里仍是一个反问句。
由于子路仅比老师小九岁,与孔子的年龄接近,加之性格直率,口无遮拦,对孔子多有不敬。这么来看子路的话,真的要为子路点个大大的赞!如果换做一般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自然不在话下,回答子路可以说是“治大国如烹小鲜。”我们接着看。
子曰:“野哉,由也!”“野”最初指周代王城外百里的区域。《说文》:“野,郊外也。”这里是蛮横不讲理;粗鲁没礼貌。“野哉”这两个字,出自“文质彬彬”的孔子之口,可以说,相当精确的传达出当时的情境,那是震撼式的教育。
在这里,孔子先说子路说话没礼貌!接着再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啥意思啊?子路有勇少谋,孔子在这就教导他,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你不明白就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你发表的都是谬论,“盖阙如”就是讲不要说,话说多,不如少。这是孔子批评子路不知“正名”的重要性。
接下来孔子的话,可以说像唐朝诗人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水一样的,气势磅礴,奔涌而下,语意连贯,义脉连通,真可谓千古流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我们再来看“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句话
孔子为政的关键,不是“先之劳之”再加上“无倦”,也不是“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而是“正名”,这事关国家兴亡、社会安定!正名就是明确权力的责任和要承担的义务,有“名”也得有“实”啊,这叫名副其实!“名”简单说就是给你权力,你需要明确的责任;“实”就是你该履行的义务。如果一个人能按照职责去行使权力,这就是有“作为”,有作为了,老百姓就会信服。大家信服你了,大家就会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国家就会井然有序,社会就会和谐。相应地,你在职位上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像前一段新冠病毒疫情之际,由于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防控措施不力,给武汉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带来的那么深重的灾难,等待你的结果只能是换“蒋”走“马”。
“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说话不顺当合理,那么,很多的事情就办不成。
譬如,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担任“国老”一职,这是个闲职啊,没有任何的实权,谁能听你的啊。《论语·宪问篇》记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陈成子以下犯上,杀了齐简公。身为国老身份的孔子建议鲁哀公讨伐!鲁哀公说;你去跟三位大夫商量吧。结果,孔子去找季氏三桓,季氏三桓和陈成子一样的货色,当然不同意出兵了。结果,孔子想讨伐陈成子的事情自然没有办成啊,因为他有名无实啊!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孔子说啊;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兴盛不起来,礼乐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
《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孔子崇尚用礼乐治国,“礼”是维持秩序的,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规矩不乱,这就是“礼”;“乐”是来维持和睦的。一个国家讲究礼乐教化,等于这个国家上轨道了,老百姓都按照礼乐制度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社会自然和谐。反之,这个社会就是一团糟,像卫国的父子争国一样的混乱!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孔子接着说;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
“礼”代表能够长幼尊卑,有秩序;“乐”代表大家可以和谐共融。礼乐不兴,秩序与和睦都没有了,制度的执行也不会恰当。因为制度的执行要靠秩序来维护,要以和睦为目的,这就叫“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再一个,大家都不讲礼乐了,没有羞耻心了,即使是触碰了刑罚制度,他们也不会感到羞耻啊。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
最简单的理解,国家的刑罚乱套了,形同虚设了。小偷偷盗没有刑罚制裁了,那你说天下人不都得学小偷啊。别人养个鸡,给他偷走;别人家养头牛,给他拉到集市上卖掉。你说说,这样的社会岂不是一团糟吗?结合历代农民起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官逼民反,民不聊生是主要原因。大泽乡起义,农民田间的秋作物还没收呢,统治者偏偏让农民去修长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又因全国大旱,不仅农民颗粒不收而且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孔子最后总结;君子,这里更侧重有地位的人,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首先要正名,定下一个名分,你说出的话才顺理,不会悖理。顺理的话能说得出,那也就能够行得通。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苟是苟且、随便。孔子说;君子对于他的言论,容不得一点马虎。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就不能随便,不说就算了,说了,就得合乎道理,一切按道理来办事,大家才会效仿你。“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主政者的品德好比风,老百姓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
孔子谈为政,第一要务是正名,要想名正,首先心要正,其次才是权责相符!说到做到!说到做不到,等于等于放空炮!儒家学说不谈高深的理论,就是讲在现实中如何切实可行!蒯聩与蒯辄父子争位的闹剧,名不正言不顺,成了大家的笑柄!一切皆是受到利益的驱使,忘记了人伦大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夫子争来争去的结果自然不会好!
为政,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名”。“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治理企业同样也是如此,先正名,权责相符,才能顺利地开展其他各项工作,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