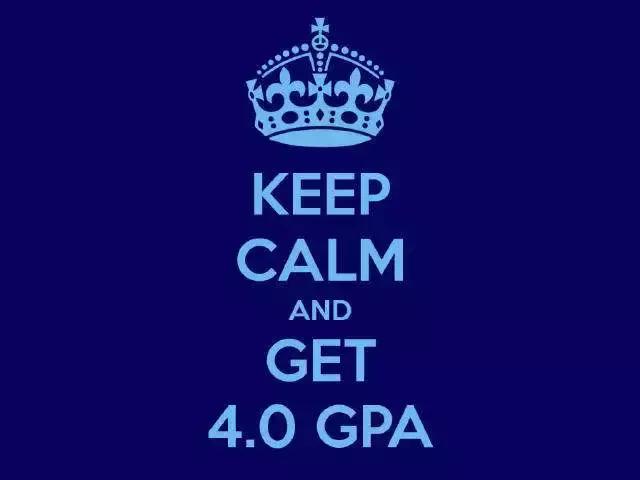文/詹世萍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中有过我” ——《萍聚》 ,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我没有写错字。是的,回纺。她的全称是桐城县棉织布厂(大河边)回纺车间。
(一)
我是1987年年底进的棉布厂当了一名合同工。
回纺:即是从各地服装厂、裁缝店里将制衣服的边角料回笼重新打成棉花,再经机器压制,使其纤维密集不松散,再纺成纱,织成可用的织品。一麻袋一麻袋山一样的布角运进仓库,再被运进铰棉车间。铰棉车间是一大间很高很大但和一般批量生产的车间比起来又很小的车间,所谓车间也就一个人一台机器在里面,其中的一面墙上靠近屋顶的地方有三个方洞,两个安装了排气扇,一个权且作窗户。师傅名叫:张小由?,是个身材很瘦小,声音宏亮,很喜欢笑的一个人。除周日法定休息日外(我已记不清那时周末是休单,还是双休),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开机,张师傅全副武装,戴着帽子,穿上牛仔工作服,解开一大麻袋的布角,用力将它们成抱的塞进机器口里,高大威猛的机器迅速吸入这些来料,齿轮破碎布角发出的撕裂、韧劲的轰鸣声让人头皮发麻,头脑发懵,血压上升。棉絮满天飞舞,站在铰棉车间看热闹的我们马上一轰而散的逃离,铰棉车间的大门旋即被合上。于是,山一样的装着布角的麻袋,满屋飞舞的棉絮和一台机器和机器的噪音都留给那个瘦小可怜的男人。

张师傅铰出一定数量的棉花之后,会主动拉开专属于他的车间大门,他的满脸满头满身都是粘着汗湿的棉花绒绒,鼻子里可能也有,戴了口罩都不可能阻止这种无孔不入的物质。他大声地喊着小双的名字,让他们赶快把他铰的棉运走。小双是管梳棉的“头头”,所以张师傅一旦有了些产品就喊他,而他听到喊声会从纺纱的小妹们身边走开招呼他的手下,再将张师傅的产品装袋拖拽进梳棉车间。
铰棉机如同打稻脱粒机的话,梳棉机形象如碾米机,事实上也是如此。铰棉机庞然大物,梳棉机相对要小很多。将打碎的棉花一大把一大把匀速地塞进梳棉机内,机器的下方就会流出一整片压得方方正正的半成品,小双和他的手下会手拿两块有柄的木板,——木板一面光滑平整,一面有柄,他们就一只手拿着一个这样的木板,弯着腰,将左手的木板对着刚出来的板正的棉花用力一压,再顺势用板子一翻,右手再一压,如此三四次,右手的木板在梳棉机下口的托板上对准出口一阻止,左手上的木板就势托起一板棉花,迅速两块木板一夹,一整张棉花梳好了,再由人搬进大车间。大车间有大台面桌子,这些梳好的棉花一摞摞的堆在那儿,由人拿上桌子,卷成合适的圆筒,再装进固定器里面。说是固定器,其实是一个简易工具:它的前端是三根铁丝的爪子,后端是手柄,手柄可以控制前端爪子的开合,手一捏一使劲,爪子张开,左手把卷成筒状的棉花放进长爪内,手一放松,长爪握紧。左手再拿起一个中空的薄铁皮圆筒(圆筒内径约五六厘米,长约二十厘米)。右手一张一弛,左手运物,一番如此这般的操作,一卷卷棉花就被装进棉筒里,然后就一抱一抱的被送到机器旁。纺棉机器一台是前后各一大排,运转起来是沙沙的响声,一台机器声音不太大,一个车间机器同时开始工作,噪音还是很大的,相对着说一句话都要用力的喊。——这些装好棉花的圆铁筒被插在机器的底部,一个圆筒一个位置,上面有细铁丝做好的固定,从棉筒里拧出一小段棉条,用一个前段有叉的引针穿过通道,再赶快接上上面的将要断线的线头。装着棉花的圆筒在不停的快速旋转,上面的铁皮圆筒也在不停地稍慢一点的绕着圈,棉纱就不断的往上抽。一饼棉纱绕到多得没有位置再容纳的时候,就将它换下。这些棉纱被打包装进大硬纸盒里,纸盒再装进硕大的蛇皮袋中,这一大袋一大袋的经过回纺的棉纱运到西门的总厂车间织成需要的织品。

我在那一年多里装过棉筒,做过纺纱工,开始是每个月36块钱工资,三个月后按劳取酬,纺了多少的棉纱,按斤两发工资,当然要比原来的工资多一点,也多不了多少,最多的,手疾眼快的一个月五、六十块钱。正式职工除外,他们是按进厂时间算的工龄。技工是按几级工算工资,级别越高,工资越高,高的一个月有一百多两百块钱。有个将要退休的老工人,他是八级钳工,工资在那个车间是最高的。
我写过一首诗,记得有这两句:
一个大甩胯,好潇洒!
断了的银丝又长了
从洁白的棉花里抽出
洁白的棉纱,洁白的希望!
我记得当时有个人给这小诗还改了两处,还给发表了。
(二)
回纺车间出的产品是棉布厂新兴引进的,其实也没多少技术含量。技工都是从总厂各车间调来的,负责修机器,给长时间运转的机器上上机油。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装筒的也是从总厂打纱、挡车工中年龄较大者抽调来的,回纺纺纱的车工大多是桐城各乡镇的小姑娘,二十出头、十七、八岁的样子。每一个人进厂都有一个背景,——那个时候,进城打工赚点“活”钱,还是要“人托人,保托保”的。
车间主任姓李,是位温文尔雅的中年人,说的话是西乡的口音。
从我进厂子开始,我将我的信件地址都改成桐城棉织布厂(大河边),没有一次丢失过,写过几篇小稿寄给桐城广播电台,大约除我自己之外,没有人留心听桐城文艺广播时间。但褚黄色的大信封上印的大红字体:“桐城县人民广播电台”赫然在目,大信封寄过几次到厂部的传达室,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标明回纺车间。李主任几次递给我信件,我都内心激动一下,眼光不由的向上看几分,其实信封里只是一张广播电台的稿费领取通知单,两块钱、三块钱的。李主任对我很是看重。大约进厂两个月的时间,车间陆续不断的进人,机子开了三十几部,连技工、纺纱工、梳棉工等等有四十五十多位,车间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李主任自己拟定车间规则,诚蒙他看得起我,让我用毛笔将他写的《规则》誊在一张雪白的宣纸上,并贴在车间的醒目处。

纺纱工都是小姑娘,技工都是小伙子,还有装筒的大妈。车间里每天都在上演情景剧。小王姑娘的姨妈全家都在棉布厂工作,她很容易的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她长着一张容长脸面——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看到她第一眼,就自然的想起《红楼梦》里描写鸳鸯的容长脸面。不几天,小双就和她很熟的样子,常常的工作间隙到她身边,帮着她搬棉筒,给她接线头。张姐打趣的说:小双嘞,累死着,现现三条筋,又害相思病,把人搞屁掉着。所有人哄堂大笑,小双脸不红心不跳的迈着八字方步,该干啥干啥;小王姑娘抗议了几回,根本不是阿姨、大姐们的对手,如此几次,最后就装着没听见,只在她的机子旁伺候着她的机器。
有个梁姐,当时三十出头的样子,白白胖胖,一直说着她的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婚姻,好看的小女儿,特别善的公婆,特别好的父母。她一直更正着我们对她的称呼,她让人家叫她姨,而不是姐,几次更正之后,我们只好叫她梁姨,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不知道她为什么受之不却,答应得脆脆的。
梁姐无疑是有神论者,常说些她发现、经历的蹊跷事,说她爸生病了,有一天她好好的听到她家厨房一声炸响,她去一看,平风静浪,根本就没有碗打碎,水瓶也没倒,她就心里打鼓,果然她父亲不久就去世了。说着,她滚下两行泪水,大家于是都劝解她。
大双是小双孪生的哥哥,长得比小双高大、威武些,他是技工。他好像对徐姑娘有好感。徐姑娘个条适中,一头乌黑的批肩长发,用一条发圐圐着,齐刘海下面是一对乌黑明亮的眼睛,眼睫毛很长,眉毛很黑,鼻子上有几点雀斑,看上去很是魅人。大双荷尔蒙被激发,常常的就在她的机子旁站着不走。大双还是很有一套的,请看电影都是请好几个人一起,记得电影《红高粱》就是大双请看的。
徐姑娘知道自己很美,她还要自己更美,常常的自觉不自觉的不吃早饭。有一天,正上着班,身子往下一倒,晕了过去,头发立马被转进机器轮子里,幸亏大双当时在跟前,马上关掉电源,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事后,车间所有女工一律剪头发,我们几个剪发之前还去照了张集体照,非常可惜的是,几年之后,这张照片混在其它东西里,全都做了我青春时代的随葬品,被烧成了灰。车间又来了一位女孩,瘦高挺拔的身材,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开阔的额头,满月的面容,刘海烫成美丽的云朵堆在头顶,长长的鬓角,俏俏翘翘的恰到好处,后脑一根粗长乌黑的发辫,直拖到腰部以下,真是一位美人儿!
他们的故事最后怎样的发展我不知道,因为第二年我就到另一个乡镇企业去上班了。
小李姑娘很高很瘦,好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样子,黑黑的面庞,精精刁刁的,很成熟,说话:你家娘,你家老子怎样怎样,很是让人吃惊。她跑到我跟前说:小z嘞,你把我写一篇文章哪。我笑了,说你好好表现,给你写一篇。一直到我离开回纺也没有给她写一个字。现在为她写了几句话,不知道她会看到吗?
大只优秀的女副主任,初次相见她穿着一件黑色丝绒的礼服,骨头样的纽扣自领下斜斜的扣到腋下,很端庄。后来听说嫁到外省,丈夫很高学历,祝福她!
我离开回纺几年后,听说当年铰棉车间的张师傅已离世,很是唏嘘了一阵,愿他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享受关爱和温暖!
(三)
春天,有消息称某天什么时间可以看到日环食。张姐从家中带去一块玻璃,用蓝墨水涂上,到了那个时间,张姐就拿着玻璃对着天上的太阳,张姐不停地招呼我:小z,快来看,快来看。我把玻璃拿过来,对准太阳,果然,太阳中心位置在慢慢消失光芒,最后只剩下一圈红红的光圈。我们又大呼小叫地让别的人来看,大家围拢在一起,用玻璃片对准眼睛,望向天上的太阳,个个称奇。梁姐却在说些怪话。

那个盛夏的一场豪雨真是叫人没齿难忘!狂风怒号,漫天扯地倾倒的雨水借着风势横扫一切有形之物,真个是断壁折枝。高高架在电线杆上的电线突然光芒万丈,火花四射,所幸电工及时拉闸,没有造成其它不好的状况。雨还在持续不断的下着,白色泡沫包装盒随波逐流;院子里平时用来浆纱的大缸在水中漂摇;树木的断枝在水中走走停停。让人真正领略了什么叫“水火无情”。真的是惊心动魄,心惊胆颤。心中想着,这样恶劣的天气里,还好是在上班时间,还好有许多人相伴。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雨似乎有点下累了,慢慢的小了下来。我看看天,天上依然有厚重的云,雨势却小了,心中想着家里,问过同事,确定今天不会继续上班了,我准备冒雨回家。张姐他们都劝我再等一下,我还是坚持卷起裤管走进雨中。
棉布厂就在桐城桥的南边桥头。我刚走到桥中间,狂风暴雨再次来袭,路上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我本来走在道路近中间的位置,被风雨裹挟着一直向旁边行。一个巨风刮来,我蹲下身,双手赶紧扶住桥栏杆,透过模糊的眼镜片,桥下浊浪翻滚,水已淹没了大半个桥墩。一阵头昏目眩,赶紧站起来,又到路的中间,狂奔。

雨水砸得人身上生疼,手不停的抹着眼镜上、脸上的水。桥那头河堤上有一家卖石灰的小屋,我使劲敲着小屋的门,一个慈祥的老人将门打开放我进去,一边拿着毛巾让我擦擦脸上的雨水。稍息,雨势小了些,我走出小屋,走到河堤下的大孙庄,王伯伯在他家小店的门口喊住我,让我躲躲雨再走,我谢绝了,王伯伯拿过来一把伞高低让我打着,我打着王伯伯的伞,终于回到家中。我娘看我回来了,说:你回来了呀!
不到一个小时,有人从街上回来,说大水已是漫过桐城桥的桥面了,有人在河边涝着从上游料行(卖木材的露天市场)漂下的木料……
结尾也是开端
大双们的爱情是怎样的进行下去的,我没有问过人。人到中年,平安健康最好!
那年冬天,我失去了一位好友。那天“她”送给我几张邮票,第二天,天人永隔。痛心、难过,不敢提起。
我还常常做个怪梦,我总在寻找一个什么东西,那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很用心、很着急,急着急着我竟流下眼泪,然后我就醒了。
第二年农历四月,我的妈妈弃我而去,到天堂享福去了。
我看向天,天蓝蓝,白云苍狗,没有地震,没有海啸,路上行人络驿不绝,人人都像刚满血复活的样子,忙忙碌碌,朝朝暮暮,车水马龙,生龙活虎。
村庄每年有十几二十个婴儿出世。经济宽裕了,他们不像我们小时候穿旧衣、吃得孬,他们穿色彩多样的衣服,营养均衡,他们脸上的肤色像苹果一样好看,笑起来像花儿一样可爱。他们是命运的宠儿。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追着你、赶着你,逼着你按下你的怯懦、你的恐惧、你的伤心。
抬头看天,天蓝;低头看路,路在脚下。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走也就成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