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品质
——读《井台戏台》
文 | 逄春阶
上了岁数,爱到处逛。包里塞本小册子,就选平装的。在机场、车站和码头,在机上、车上和船上,埋头随便翻。这趟去甘肃,带的是《井台戏台》,刘致福先生的散文集。

《井台戏台》
刘致福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我看书有个毛病,喜欢从末后翻。《井台戏台》“后记”不长,可干货不少。“老实”“扎实”“朴实”,三个词儿揪住了我;还有个词儿“真情实感”,我缩成“真实”二字。上车下车、上机下机,断断续续,六天,翻完了。心里冒出一句:作者践行了散文观——“四实”。
老实,是态度。老到、实诚。致福先生写散文三十多年,早年的散文,一眼就能认出来,收入集子里的如《希望的光亮》《看望蒲先生》,有奇崛之气、峥嵘之姿、曼妙之韵,但底色是老实。上高三,为了能多学会儿,借住在山顶上一间透风撒气的小屋,遇到几十年罕见的大雪,“早上一醒来,我们都呆了。被子上盖了厚厚的一层雪。炕洞里的火早已经熄灭,炕上、炕下,跟外面一样,白花花的一片。三个人都从被窝里探出头,呆呆地看了很久”。他们“从雪底下将压在被子上边的衣裤掏出来,龇牙咧嘴地穿上……”“龇牙咧嘴”,多传神,多老实的话儿啊。用大写意,刻画蒲松龄故里,弥漫着一股仙气。不料,结尾笔锋陡转,一下子拉回现实。戴眼镜的才子说,先生活得太累。作者来了一句:“听见狐仙‘呸’的一声,极尖酸地喊,你懂什么——”老到、实诚。随着阅历增长,作者是越写越老实,越写越结实了。

《父亲的脚步》开篇,写母亲出门摔了一跤,母亲说这是父亲绊她,父亲托梦,埋怨鞋不跟脚。据母亲讲,父亲走时给他买的鞋号码不对,有点大。“母亲让二哥去县城比着父亲生前的鞋号买了双新鞋,去坟前烧了。母亲说从那以后再没做梦。估计是父亲收到新鞋了。我听后心里一阵发酸:父亲在那边还是那么忙碌?“父亲在那边还是那么忙碌?”这句老实话,碰得我眼窝发湿,我也想到了父亲,父亲走时,好像那双鞋子也大。“按母亲的说法,父亲在那边还是闲不住。只是不知父亲是不是真能收到那双新买的鞋子,父亲穿上是不是跟脚?”这是孝子的中年之问,无解的问,剜人心肺的问。
扎实,是语言。活的语言,是活的树,根扎得深,果实,籽粒饱满。保持语言鲜活,需要耐力和定力,这是一种抵抗,抵抗惯性,抵抗干瘪,抵抗程式化、概念化。致福先生定准下了番炼词、炼句、炼象功夫。井台是小村的灵魂,“改邑不改井”,寒来暑往,井台边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每一担水挑出井台,都盛满了一家老小的渴望与期冀。走下台阶,肩上的担子一摇一颤,清清的井水晃溢出水桶,花花搭搭地洒落到白净净的泥土路上。一串串一行行的水花润湿了一条一条的街巷,又分叉到各家的庭院,像一幅幅生命的血脉图谱,让人感受到湿润鲜活的生机,感受到干爽的土地与水的亲近。让人怀疑,倘若有种子播撒下去,明晨这一条条街巷都能长出庄稼,长出生命。”水洒了一地,想到了种子的播撒,“洒”与“撒”,密密麻麻,点滴在故乡的泥土上。

水灵水灵,有水则灵。好的散文,让人心长翅膀;好的语言,让人如含在嘴里的薄荷,清爽满口。《国哥的爱情》,写国哥聋哑了,被爱情抛弃,但他不抛弃爱情,痴心如火苗,一直熊熊在心中燃烧,他苦苦等待了大半生。“国哥大部分时间都打发在了村口。原来是站着,现在腰腿不行了,或坐或蹲,但一双浑浊迷茫的眼睛,始终一眨不眨地凝望着村口通往山外的路。那里有他未知的谜一样的世界,那里有他五颜六色的梦想,那里有他等了一辈子的爱情。”国哥酸楚的一生,用简约的文字描摹出来。我想起了孔孚先生的话:“句上有句,句下有句,句中有句,句外有句。那不写出来的外句,还不一定是四句,说不定是多句,出一句而略其他,这就是提炼。”作者用减法,削出了国哥的圈圈年轮。
朴实,是风格。素朴、自然,让人感到踏实。不做作,不炫耀,不花哨,更不诘屈聱牙。引经据典的章节,一点儿也不见,就是干干净净。原汁原味写出自己看到、听到、想到、悟到的。在《母亲的作品》中有个细节,母亲爱种菜,看到空地就种。其中有一块在邻居才叔的房后,“哥嫂都劝她别刨了,在人家房后种地,担心人家才叔才婶不愿意。母亲说这是咱的地块,我和你才婶说好了,她同意。”这个细节,很温暖,儿女担心邻居,母亲呢,想得更周全,早递话了。怎么递的?略去了。我感叹,忠厚家风,原来是这样形成的。

还有《蟹殇》,我觉得这篇可入中学课本。买了几只河蟹,煮着吃了,不知怎么跑出来一只,那么高的水桶,它咋跑出来的?为了活命,这只蟹不知做了怎样的挣扎,简直是一只“蟹英雄”。“我把它拿到厨房,放进一只水桶里,倒上水,我说:‘这是只不该死的,就养着它吧。’”妻子也同意放它一条生路。作者第二天上班,跟同事说了,同事都觉得蟹子该活下去。可是一回家,水桶空了。孩子见到蟹子,非让妈妈煮了吃,怎么哄也不行。作者是怎么表现的呢?“我说:‘吃了就吃了吧。’弯腰抱起女儿,女儿将蟹腿放进我嘴里,我却怎么也吃不出滋味来。”没有暴跳如雷,把自己的情感压抑住,以一颗平常心待之。最后感叹,“人生实际也一样,面对那些无法征服的东西,人有时就是蟹。”写得节制,没有渲染,更无矫情,朴实无华。慈父有一颗宽厚的恻隐之心。

唯有真实最可贵。真情实感,最难呈现。老实的态度,扎实的语言,朴实的风格,都附着在真实之上。《井台戏台》中的域内域外游记,人物品评,亲情散文等,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最大限度地靠近真实,贴近真实,贴紧真实,走到现场,挖掘现场,看到多少,就写多少。知止,难能可贵。比如《圆头山的风声》写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发生地葛底斯堡小镇,作者发现“所有的宣传与展示,都透出一种主题,就是国家意识,不论南北哪一方,不论正义与非正义,都是在联邦统一意志下的争战。战争的代价让人痛心,也让人深思”,这是历史之真。然后,“要下山了,我忽然感到一阵发冷。山风掠过树梢,从山的四周吹来,发出呼呼的声响,像呐喊,也像低嚎。”这是艺术之真。

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作者写的实,其实有艺术的虚来支撑的。就像天空碧蓝如洗,突然飞来一片白云,这就有了虚,有了幻,这就是诗意。写着写着,猛不丁地,荡开一笔,让人惊喜。《一杯沧海》写青岛的咖啡屋,写到酒吧里的红衣喇嘛和美女在细语,气氛神秘,看来,有故事要发生了。自己缓步进入,坐下,“茶几前方,窗台前一个小木架上,放着一只硕大的水滴状收口的玻璃杯。视线稍微放低,那圆鼓鼓的杯腹,竟如一个硕大的放大镜。先前窗外的景致,大海、小岛以及红岩和楼宇竟全部装进了杯中。一杯装沧海,一杯盛世界。正如这小小的咖啡屋,虽然不露声色,却装下了多少让人想都想不出的故事,装下了多少人间的爱恨情愁、酸甜苦辣。窗外的雨声和身后的低语混在一起,如一种深情的浅唱低吟……”一只杯子,就如蓝天飘来的白云,它的介入,就虚了,就是折射,而颇有味道的是“窗外的雨声”与“身后的低语”,那分明指向的是红衣喇嘛和美女。他们在说啥呢?作者猜,我也在猜,瞥一眼绵绵细雨。
《井台戏台》伴我一路,从济南到甘南,从甘南到天水,从平原到高原。它很适合我,对我的脾气。我的井台、戏台仿佛都被装在了书里,我也等于携着故乡远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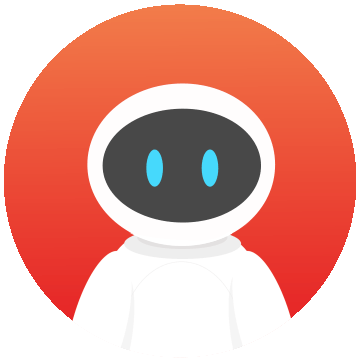
AI小壹
我是齐鲁晚报智能机器人小壹,欢迎向我爆料新闻线索哦~
爆料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可以直接点击上方“爆料”按钮,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全省600多位记者在线等你来爆料!你提供线索,我们来曝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