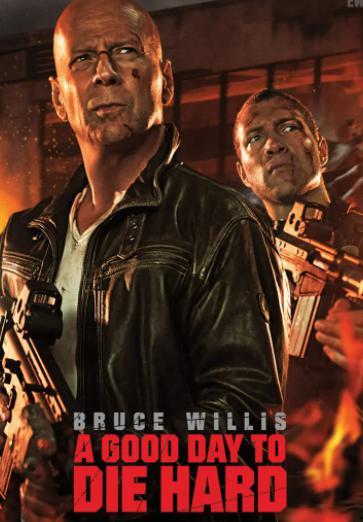《“女博士”沈琼枝》王嘉琦近日读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读到第四十回,发现一个有趣的人物——沈琼枝。一位女性,要在男性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文学作品里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位沈小姐究竟是何方仙女,却又这般本事?不然,她不仅并非仙女下凡,还差点成了娼妓。书 第四十回讲到:沈父将女儿许嫁扬州宋府。可到了扬州,却发现宋府竟不是把她当作正室。沈琼枝一怒之下出走,来到南京,以卖诗过日子。然而,“南京城里是何 等地方!四房的名士还数不清,还那个求妇女们的诗文?” 凡到她那里的,并非求诗,而把她当做倚门之娼,少不了遭到恶少的调戏。好在天下第一豪士杜少卿慧眼识才,出手相助,她才讨个了不好不坏的结局。却有一处, 知县审问沈琼枝:“既是女流,为甚么不守闺范?”。“闺范”一词既出,着实让人惊呼,纵使东西方相隔万里,文化千差万别,在女性问题上,真还有相见恨晚之 感。英语词Domesticity,有“家庭生活,爱家,顾家”之说。其形容词domestic更有“家养的,驯服的”之意。不正于“闺范”契合吗?所 谓“闺范”,无需多么繁复的定义,取一西方文化中的典型形象即可表达:家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家庭天使的理想形象表征了西方传统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一,女性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其二,她理应像天使一样相夫教子。女性主义批评家桑 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文,对西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流变进行了梳理,解释了“家庭天使”的来龙去脉。在 中世纪,她是圣母玛利亚。而到了十九世纪早期,世俗的浪漫文学中,她代表了纯洁和无私。乍一听,这是对女性何等的夸赞。但若细读,却发现其深处是男性话语 的权力操纵。纯洁(purity)意指女性即一张任人涂画的白纸。无私(self-less)这意味她没有自我(self),没有行动,没有故事,唯有服 从。由此可窥见西方文化中典型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前者闯荡江湖,远渡重洋,开疆扩土,升官发财;后者深居闺中,相夫教子。等老爷满身飞尘回到家中,她 端上一碗热茶,给老爷安安心,暖暖床。

然 而,纯洁无私的天使面孔下,藏着一张可怕的鬼脸。无私,无欲无求,没有自我,没有行动,没有故事……这些“无”和“没有”不正是死神的专属吗?所以,在维 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中,带着死亡面孔的女性神出鬼没。除了家庭,她又多了一个活动场所:死亡的国度。 女性死神附体,并非说她大开杀戒,而是说,如果原先作为天使的女性拒绝行善,拒绝舍己救人的话,转身即为魔鬼,以及她的各种变体:巫女,妖女,阁楼上的疯 女人,妓女,女作家,女工人……男 性作家和艺术家刻画的天使形象好似一个蛋糕模子,女性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蛋糕模子中难以脱身。而魔鬼的形象却暴露出男性的焦虑:被压抑的女性会不会起来造 反?在十九世纪的艺术圈中有一个传闻,讲前拉斐尔派画家兼诗人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爱妻去世,悲伤至极,便将一篇诗稿与爱妻一同埋葬。1869年,他掘开 坟墓取回诗稿,却见妻子漂亮的金发依然疯长,填满了整个棺材。此情此景,天使与魔鬼在这既唯美又骇人的画面中戏剧般的呈现。西 方女性为了跳出天使/魔鬼的牢笼,真不知流了多少血,撒了多少泪,到如今战果累累。当下中国,流传着一种“人类学”,说世上人分三类:男人,女人,女博 士。女人/女博士的对立与天使/魔鬼却有几分相似,或者说是现代中国版的天使/魔鬼。甚至还能套用于《儒林外史》中的沈琼枝。女博士为何人?不还是那句 “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四房的名士还数不清,还那个求妇女们的诗文?”以此看来,沈琼枝小姐也好似清代的“女博士”,有几分学识,有本事抢了文人雅士的笔 杆子,更有独步天下的能耐。若与同时代的西方小说家相比,吴敬梓将女性问题的描写深刻得多。不仅把沈小姐褒奖了一番,借此讽刺那些个伪君子,还暴露了当时 中国的女性问题。可惜的是,我们与沈小姐只得一面之缘,南京一晤,从此了无音讯。这也不能怪罪于吴敬梓先生。他必然受困于当时的语境,纵使他天马行空,也 真不知道如何给“女博士”沈琼枝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而当下的女博士又会落下个怎样的结局呢?
李银河公众号刊出作品,ID: liyinhe6666, 或:李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