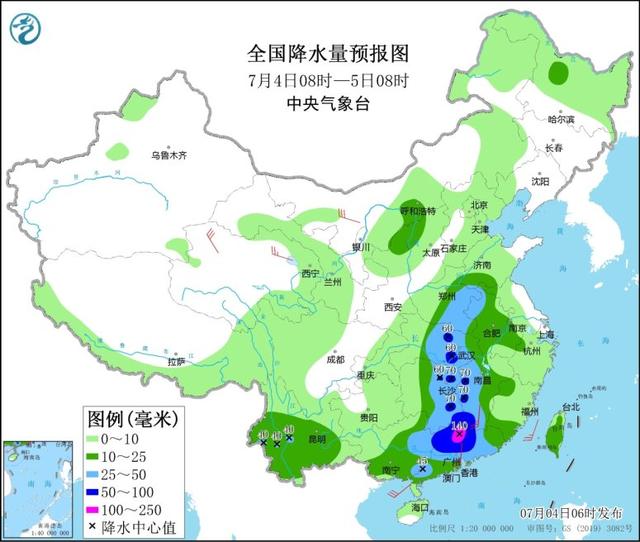文/浔阳
"不管你是谁,我总是指望着陌生人的慈悲。”
——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
某个灯火阑珊的夜晚,我一个人踏入了《风之旅人》的旅途中,一段疾驰而下的速降后,画面陡然拉远,浓郁而不刺眼的落日余晖,明暗交杂的昏黄沙漠与几十倍于旅人的高耸石柱,“美”,大抵不过如此。

风之旅人
然而每个完成这趟旅途的旅人并非因为沿途风光而对其心心念念,镌刻在记忆里的更多的是某位萍水相逢的陌生旅人。
陈星汉在空旷、荒凉的世界里喂养人的孤独,然后用人与人的相逢来消解,一期一会是每次邂逅的注脚,不断贴近的身体是沉默的言语。在那一刻脑海里蹦出了《欲望号街车》里布兰琪最后的呢喃:“不管你是谁——我总是指望陌生人的慈悲。”
在陈星汉七年雕琢的《Sky光·遇》里,我像那些用善意铸就白袍的旅人一样,在黑暗中拥簇光明,在雨林里相依取暖,我依旧指望着每个陌生人的慈悲能够解锁星之门,抵达星辰的归宿。
无论是孤独的《风之旅人》,还是被更多的给予与爱包围的《Sky光·遇》,我不愿简单地将其称之为“游戏”,它应该是什么?一次情感体验,或者是一项艺术。
乌托邦幻想陈星汉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情感体验类的游戏。
无论是利用心理学的心流理论来提高沉浸的《Flow》,还是利用好莱坞的三段式来强调情感的《Flower》,抑或将三段式渗透到人生不同阶段的《风之旅人》,它们都讲究在两三小时的沉浸体验中调动人的情感,通过强烈的情感冲击在人的脑海里烙下印记。为此,他借鉴了不少心理学层面的理论,从《Flow》的心流到《Sky光·遇》的Nudge。

但人性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心理学并不总是研究人性的善。
“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吗?是我们的游戏让我们变成了混蛋。”
2015年Eurogamer的记者Simon Parkin采访陈星汉的时候他如此说道。激发人的情感是陈星汉制作游戏的一面,但核心却是挖掘人的善性。
“玩家第一次进入虚拟世界时就像孩子一样,他们寻求那些给予了他们最强烈的反馈的行动。在社交压力与复活的侥幸心理下,把某个人推进深渊所伴随着的动画、声音等巨大反馈会让他们觉得这比把玩家推进风里更令人愉悦。”
陈星汉不止一次在访谈里提到宫崎骏,它用孩子纯真的目光去抵达一个温暖的世界。然而威廉·戈尔丁却在《蝇王》里告诉我们,即便是孩子也可能成为迫害同类的野兽。“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是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恩格斯《反杜林论》)
意识到这一点的陈星汉开始在游戏里制造一个没有伤害的乌托邦。《Sky光·遇》是一个全年龄、全家、全性别的游戏,是个“可以让你和你爱的人一起玩的游戏”。

他甚至不希望游戏中的人被利益推着走。如果游戏里的行为没有任何奖励,玩家还会去做吗?被日常、周常任务缠身的玩家们是否还拥有玩游戏的自主性?在长达七年的制作中,《Sky光·遇》的团队抛出却又抛弃了不少想法,即便是两个人在雨林能共撑雨伞的设计也被舍弃,理由是它会让玩家为了得到雨伞而与他人构成临时的伙伴关系。
“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丘吉尔的话显然无法动摇陈星汉的创作理念——只有最真挚的交流才能带来真正的回报,而构筑在利益基础上的欺骗就只会破坏情感乃至整个交流环境。
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这种幻想我曾在《Minecraft》里的Exarch流浪帝国见过,他们拒绝了所有肆意挥发天性的未成年人,将违背规则的玩家驱逐出境,塑造一个假想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世界。
这种幻想我也在《星露谷物语》的田园牧歌里看过。对于其他对抗性或者赏罚分明的游戏而言,它成了玩家心中远离喧嚣的精神桃源。
《Sky光·遇》同样是这种乌托邦式幻想的产物,作为一款有别于《风之旅人》的社交游戏,它抹去了所有引发负面的竞争性的游戏内容,更加注重与其他玩家的互动,如果是烛火,那么靠得越近,感觉也会温暖,如果是光,那么光源越多,世界也会更明亮。
但蜡烛会消耗得更快或烫伤自己吗?这恰恰是乌托邦回避的现实。
深度交流的社交平台“两个人在一起相遇了、握手了、拥抱了”,这就是“光·遇”。
相比《风之旅人》中刻入骨髓的孤独,《Sky光·遇》希望为家庭搭建一个情感互动平台、为陌生人搭建一个真诚交流平台。
《Sky光·遇》是个社交类游戏,只是它跟其他游戏里的社交都不太一样。

对话框一按,麦克风一开,别人就能听见你的声音,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与价值,游戏里往往还设置了“世界频道”等功能,这是MMO社交的常态。而在《Sky光·遇》里,每个人都被剥夺了言语交流的自由权,动作是他们最初的交流方式。

当世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人们体验到同样的孤独感时,他们直接的反应是跟人接触和建立联系。”《风之旅人》的孤独感来源于苦心孤诣营造的场景对比与极其克制的社交元素,到了《Sky光·遇》,玩家的孤独来源于与己无关的热闹和没有任何回应的呐喊。
“四个人提供了更多的社交元素,额外多出来两个人将会破坏两个人之间独一无二的连接。”三个人就是一个社会,在多人游戏里构建情感链接要比双人游戏要复杂得多。于是《Sky光·遇》在剔除游戏负面因素的同时,对交流做了各式各样的限制。
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人在《Sky光·遇》里被迫返老还童,回到人类最原始的年代,简单却蕴含旋律变化的单音是他们最开始的声音,从先辈那学到的动作是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而点燃烛火、照亮他者是彼此接触的开始。
在没有为他者点燃烛火前,你所看到的一切旅人都是单调的灰色,是温暖照亮了人与人的多彩。即便如此,你与ta的交流依旧局限于简单的动作,所有话说出口都不过是长短不一的“……”。

唯有给予他者库存极少的蜡烛才能换来下一步的交流,你渴望牵手去游荡这世界的天涯海角,你渴望以拥抱来表达谢意或亲昵,你渴望,你渴望听到ta的言语与心声,渴望过客能够为彼此驻足。
当交流不再以廉价的方式出现时,不再与利益挂上钩时,坦诚的情感就成为了扣开门扉的钥匙。
共鸣是玩家认识游戏的开始,即便没有确切具体的言语交流,你依旧可以从他者的行为来为其下定义,“写剧本式一个真正可信的角色,你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他的选择定义了这个人的本性。”
当ta回应了你的歌声,紧随着你的脚步,与你摆出相同的动作时,情感的共鸣就这样触碰到了人柔软的心房。《Sky光·遇》就是通过一种单纯而美好的方式把人性善良的那部分给放大了,而在匿名的情况下,“你会把想象中最好的一面给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
乌托邦式的世界让我打消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的念头,开始寻求与他者互动所能带来的纯粹愉悦,当我与另一个小伙伴依靠彼此的能量补给飞上“云野”的高崖时,被隐匿的言语表达让彼此的行动打上了信任、默契的光辉。
陈星汉希望《Sky光·遇》给予玩家的,是一个深度交流的平台,而不是萍水相逢、江湖再见的表面交流。
“即便你可能认识100多个朋友,没有深度交流的话你仍然会抑郁。”
被数字化世界包围的现代人面临着大量可供选择的社交平台,不少被现实搁置的人试图从网络上寻找到情感排遣的出口,但这些社交往往难以做深、做真。“在2009年,当Facebook兴起时,社交游戏也爆发了。但这些互动的机制设计,不是关于社交的,而是关于交换数字和资源管理的游戏。”
当有玩家在《Sky光·遇》中相遇到成为终生伴侣时,陈星汉确信这条路是对的,它从一开始的游戏蜕变成今天的深度社交体验。

人与人的交往是这部新作的主题,它从游戏层面的“沉浸”过渡到社交的“沉浸”。而这种来源社交互动的沉浸性,也是玩家驻足于游戏世界的原因。“在游戏中,我看到有玩超过2000个小时以上的玩家,他们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帮助新玩家结交朋友。”当《风之旅人》走出弱联网向《Sky光·遇》的多人世界迈进时,曾经的白袍将会点亮更多的烛火。
这样一个异样的社交平台与现实生活中的聊天软件有着天然的差异性。去功利化与纯粹的浪漫化让留在《Sky光·遇》中的玩家有一种趋于向善的特性。按照陈星汉的观点,它就像是一个迪士尼公园,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让它与普通的嘉年华区分开来。也正是如此,他才相信被打开的文字交流的潘多拉魔盒底部一定存留着人性的希望。
不是游戏的游戏陈星汉的作品看着不像是一个游戏。
它们大多没有太多的操作,没有太多可以称得上是玩的要素,看风景是玩家的常态,他们在这里收获的是情感的洗礼,而不是强反馈、重快感的游戏消遣。当《Flower》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收藏至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的游戏时,玩家清晰得感觉到,陈星汉的游戏与他们以往对于游戏的认知有着不一样的维度。
即便是《Sky光·遇》,依旧延续着他的艺术之路,情感体验、社交被摆在了更为显眼的位置,而非游戏成其为自身的游戏性。
但这不意味着《Sky光·遇》不是一个游戏,恰恰相反,它比陈星汉以往的任何一个作品都更像一个游戏。

《Sky光·遇》的整体玩法类似于《风之旅人》,无论是从旅程的变化、场景元素还是游戏功能的设计都有不少重合的部分,但是它的场景更大、互动元素更多、叙事的意味更浓。
《Sky光·遇》中的关卡虽然有固定的重点,但行进路线却是自由的,但它们更像是一个支线的存在,即便你没有任何探索、收集,径直往终点奔去也是可行的,除了解开最后的星门。
从游戏设计角度说,《Sky光·遇》鼓励玩家对游戏世界做更多的探索,从走出云野的第一张小地图开始,游戏的行进路线就被分割成了数个大小各异的岛屿。有明确区域划分的云野,零散破碎的雨林,在速降里直线疾驰的霞谷,游戏里分散与收束性的关卡分布讲究张弛有度。

陈星汉在访谈里反复强调细节,“真正在行业做到大师级人物,一定是非常讲究细节,执着做别人做不到的。”
游戏里的细节并不是纯粹的装饰品,它带着某种设计的意图。“希腊的柱子下面有一圈粗一些的基座,这是为了让人看到基座的时候,马上抬头寻找另一端对应的圆圈,从而意识到场景的宏大和自己的渺小。所以你们要把基座加进去。”
从《Flow》到《Sky光·遇》,陈星汉的作品走的都是极简艺术的路线,极简造型与大模块的色彩冲击力远大于精致、繁复的画面,在巧妙的色彩、物体安排下,玩家更容易注视到那些凸显的事物,比如每种色彩的过渡,比如在云层掩映中孤立的白塔,比如位处画面黄金分割点的山峰。

《Sky光·遇》的互动元素比以往的作品加起来都要多。这种多不仅仅是指社交互动方面的,还有游戏操作方面的。更大的地图、更开放的世界给予了玩家更多的自由感,除了沙地里一溜到底的速降,雪地里的滑雪,游戏原型《Cloud》中陈星汉的飞翔梦在《Sky光·遇》里有了更好的演绎。
有谁不向往我们头顶的天空呢?陈星汉必然是个深受宫崎骏作品“毒害”的设计师,他在《Sky光·遇》里沿袭了宫崎骏对于飞行与蓝天的狂热。大片大片的云朵将澄净的天空泾渭分明地分隔开,遥鲲自东边跃起,透明而以金色描边的身形围簇在你的周边,你的耳畔是呼啸的风声,《Sky光·遇》并没有复杂的操作,反倒以纯粹赋予他们瑰丽的幻想。这或许也是极简主义的理念,它以最原初的物自身或形式展示于观者面前,意图消弥作者借着作品对观者意识的压迫性。

除了社交与游戏层面的互动外,《Sky光·遇》也有着更多的叙事。比起《风之旅人》的壁画,《Sky光·遇》利用收集要素来实现碎片叙事,而这一切叙事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语音,无论是符号式的壁画还是短暂的人物动画,玩家只能依靠既有的认知去揣摩世界的样貌。
把游戏做得不像一款游戏的《风之旅人》实际上反倒成为了不少游戏借鉴的典范,有人从中挖掘它的美术设计,有人提炼出情感体验,还有人看到那些极为微妙的互动反馈。
在高速路上,直线才是驾驶员视觉疲劳的诱因。同理,在沙漠里最先杀死旅人的可能是毫无变化的绝望感。强调通过游戏反馈去挖掘人性之善的陈星汉在反馈上做的很微妙。
日照下的阴影,起伏的山丘,越过狭小甬道后的世界,有目的地四散在地图角落的烛火(能量补给物),画面与玩家操作的反馈形成了愉悦的体验。

每次速降总会不自觉地想要穿过这些窟窿
这些反馈往往也伴随着玩家的情感变化,“做游戏的时候其实是做情感曲线”。即便是简单的飞行、滑行、滑翔,它都有可能引起玩家的情绪起伏,但情感,却来源于玩家对于游戏世界、故事的沉浸。
比如操控着自己走向死亡的《风之旅人》,比如《最终幻想7》结局里徒劳的挣扎。而弱化了单人要素的《Sky光·遇》则把这种情感寄托在了社交上。团队在社交系统上做了大量的测试与打磨,因为他们考验的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搞懂的人性。即便是在线隐身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设计,它也引发了团队的争论。
从某种程度来说,《Sky光·遇》就像是一个一切从零开始的人性实验游戏,它把每一个可能产生反馈的设计都当做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从基本的互动到付费模式的探讨,这种对细节的雕琢与思考或许才是游戏研磨七年之久的关键。

也是源于这些来自细微处的思考,才会让这款游戏看着不像是一款游戏。
它是一个把游戏的形式剔除掉后剩下来的纯粹物,它依旧是游戏,但你在其中感受不到任何来自于游戏的压迫力。游戏里面没有没有任何地方是逼着你要和他人合作。
“我们现在正做一个非常彻底的清零,不能让任何玩家觉得这个游戏在数值上如果“给予”的话会更赚,必须要做到完全看不见才行。”
陈星汉的这些想法不仅仅来源于玩家的反馈,同时还有各种跨学科的知识养料,以及来自现实世界感觉的捕捉,而爱这种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则是让他贯彻到底的支撑。
“你就怕身边的人都是在混饭吃,这样的作品是不会有爱的。”
走向大众,改变陈念“当我们的作品真的进入博物馆以后,我发现绝大多数的纯艺术,真的是只有在象牙塔的那群人才可以理解和享受其中的价值。”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才让陈星汉意识到他们要把游戏带给更多的人,不仅仅是2亿的主机用户,而且是20亿的移动用户。每个被他的作品感动的玩家驱使着他继续这一项英雄般的事业。无论是在游戏里结成良缘的情侣,还是从父亲的逝世里释怀的玩家,他们的回忆也构成了陈星汉的回忆。

“比起成为艺术家,我更在乎的是能够改变人们对于游戏的看法。”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诱生了《Sky光·遇》。
人的欲望来回驰骋在天堂与地狱的轨道上,在被压抑的社会与人性的幽暗面之前,每个玩家是否能在《Sky光·遇》找到那一位慈悲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