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篆刻,我建议一定要研习一位篆刻大师的作品。没错,这位大师就是赵之谦,为什么呢?
1、他的作品并不多,一生下来,流传有绪,被认为真正是他的篆刻作品并为各方面专家认可的,只有不到400方,这比那些一生刻印二万、三万方的篆刻家容易精读,一天一方,一年就可差不多学完他所有的印;

(赵之谦坐像)
2、他为数不多的作品,却几乎方方都是精品,如果仔细研读,或多或少,必有收获。他后面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三路主流印风,都在赵之谦大师这里汲取营养,他可以说是这三派印风的源头,这是学篆刻真正的“正”路,值得一学;
3、他的篆刻是“皖、浙横站”的。即他的作品是融合了中国篆刻界南北两派主流印风的集大成者。他先学浙派丁敬、黄易、陈鸿寿(曼生);又学皖(徽)宗邓石如、吴让之,紧接着又将皖派和浙派的精华进行有机的组合,并在远追秦汉古风的创作思想支配之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印风。
4、最需要说的,是他过人的自信,也正是由于他的自信,他才有可能师法百家而又自成一格。因为,一个艺术家,最最重要的是自信。
一、自信的赵之谦
赵之谦的自信时时体现在他的作品和语录里,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证实这一点,比如他早期学浙派,在咸丰四年(1854)刻了一方自用印,印面文字“益甫手段”,益甫是赵之谦的字,我们可以想见他刻这方印时,心头洋溢起的自信,看,这就是老夫的手段,自信之情,溢于言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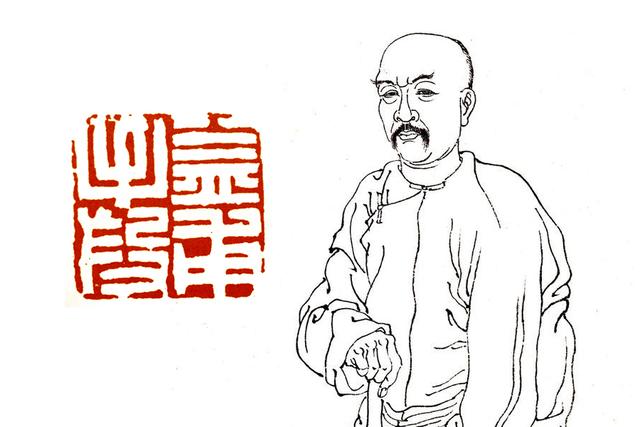
(赵之谦:益甫手段)
咸丰八年(1858),赵之谦给端木百禄(字叔总,不是日本人,是浙江青田人。道光拔贡。)刻的一方白文印:“黎阳公七十三世孙”,印的边款里他写道:“戊午六月,小窗坐雨,为叔总刻此两印,皆貌汉铸,似尚不入俗趣也。冷君记。”在他的心底里,他是反对自己入俗的,他有自己的高品质追求和自信:

(赵之谦:黎阳公七十三世孙及边款)
同治元年(1862),他给好友魏锡曾(字稼孙)刻的一方私印“稼孙”,边款里这样说:“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壬戌润月,撝(huī)叔。”魏锡曾是大收藏家,大鉴赏家,他说赵之谦这方印的水平在丁、黄之下,丁敬、黄易都是浙派宗师级人物,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毕竟赵之谦是学浙派出来的,但赵之谦却不服,他说,我这方印或许在丁敬之下,却在黄易之上,自信的紧!

(赵之谦:稼孙及边款)
还有,还有没有准确纪年的篆刻作品,比如这一方小印:赵氏撝叔

(赵之谦:赵氏撝叔)
在边款里,他自信地说:“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是如此之工。自记。”这一次他说的是皖派的宗师邓石如,邓大师啊,你刻小印,也没有刻到这样的工整吧!要知道,赵之谦在浙派之后,主攻的学习方向,就是邓石如的“印从书出”啊。
又比如这一方自用印:赵之谦印

(赵之谦:赵之谦印及边款)
这一回,他干脆不仅说了浙派的丁敬宗师,也说了皖派的邓石如宗师,“龙泓(丁敬)无此安详,完白(邓石如)无此精悍。”丁大师,你的印没有我这一方安详(浙派本不以安详取胜),邓大师,你的印没有我的精悍(精悍也不是皖派的主要审美取向),一方印,把浙皖两派的特征融于一炉,确实超凡绝尘,当然,这一回,他也自信到了极致。浙皖两派的宗师,都被他放在了批判台上。
我们说过,赵之谦自认是天才,对篆刻尤其自信,他评价自己的篆刻是“生平艺事皆天分高于人力,惟治印则天五人五”,五分的天资,虽然有努力,但也只是五分的后天努力,可见相比其他书法、绘画,赵之谦在篆刻上是下过大功夫的,也足见他的自信。
当然,他喜欢用天几人几的方式来评价天资与后天努力,他曾骄傲地认为自己的艺术天分比别人要高,比如他曾评价篆书书法:邓石如是天分四,人力六;而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天分三人力七(已经够努力了);到了吴让之天分一人力九(可见吴让之的勤奋);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天分七人力三,他自己篆书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天分高,他自己并不努力(但已经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成就)。
不过,要我说,他的极端自信,在篆刻上的表现,主要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方印,就是这方: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

(赵之谦: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
简单看,这就是一方九字的汉印格式的白文印,但实际上,这方印很重要,下文详说。
二、一方意义重大的印
这方印真的意义重大。赵之谦大师在边款里这样说:“取法在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来撫(摹)印家立一门户。”俯瞰千古的赵之谦大师,这次口气更大,他要为篆刻立一门户,这类似一句口号,一个宣言,而篆刻这门艺术,也正如他所说,到他这个时间段为止,有六百年了。
这里说的六百年,当然不包括古代的实用印章历史时期,而是指自元代赵孟頫、吾丘衍他们开辟文人篆刻(或许在他那个时候,宋代文人治印还远不可考)开始,到这一年为止,这一年依据边款,是同治癸亥十月二日,也就是1863年,距赵孟頫的生年1254年、吾衍的生年1268年,差不多就是六百年刚刚好。

(赵孟頫像)
其实,赵之谦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1863年前后完成的,这一年,他35岁,前一年,刚刚因为太平天国战事死掉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家破人亡,仕途蹭蹬,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创作,这才有了这一方印作,而实质上,正是这方有标志意义的“印外求印”的作品,使篆刻这门艺术,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它不再是雕虫小技,而是成了独立的艺术门类,所谓的“立一门户”,要我说,现在的吃篆刻这一碗饭的艺术家们,都应当感谢赵之谦,真的是他,为摹印家开了一条更加宽广的路来。
因为在他之前,或者就是“印中求印”,文人们刻印,文字素材来自于古代印章(不管是汉印还是古玺);或者就是“印从书出”即以自己的篆书书法入印(这是邓石如的创新),文人们的创作文字素材一下子拓宽了,创作方法更自由了;而到了赵之谦这里,他把篆刻的文字取资,样式取资都扩大到印章、书法以外,一时之间,战国泉币、秦汉碑版、权诏、镜铭,文字样式皆可入印,文人篆刻家们的眼界自此大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等都得益于此,才有了石鼓文印风的吴和金文印风的黄),可以这么说,篆刻在赵之谦手里,才真正具有了包罗万象的艺术视野!或者说,这样的事情,是真的需要赵之谦这样的天才来开头的。
好了,来读这方印。
三、文字的取资之处
边款里说,这方印的取法,在“秦诏汉镫之间”,“秦诏”指的是秦诏版,秦诏版我们已经介绍了无数遍,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统一度量衡等的产物,秦诏版的小篆为自由体,当时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用,因此写法草率,笔划方正,行款错落,笔画是刀刻而成,又有金属刻画之痕。文字仍属篆书范畴,却极富天真烂漫之趣。如图

(秦诏版上的文字)
你看,它的文字,不但体型不规整,甚至章法上也无行无列,这是秦诏版的风格。
再看汉镫(同“灯”)上的文字,它也是金属器物上的刻画文字,看两例汉镫拓本,一个是万岁宫镫:

(万岁宫铜镫拓本)
再看长安共厨灯拓本:

(长安共厨灯拓本)
你看,吴昌硕做注说:“……汉篆之最整饬者。”显然,汉镫的文字是最规整的,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甚至在章法上也规规整整,条理清楚到了极致。
赵之谦说他的这方印,取法在秦诏版和汉镫之间,则说明在这方印里,我们既可以看到秦诏版的天真烂漫自由洒脱的一面,又可以看到汉镫文字极度的法度谨严和一丝不苟。
四、印面章法的细节
(1)接近均分印面的汉白文印式格局:

(标准的汉白文均分印面布局)
我们看,赵之谦不愧是浸淫汉印深有心得的大师,无论文字取资如何变化,他仍然将汉印的平整、朴实、端正做为最基础的审美追求,因为这是中国人最朴素,最底层的审美取向。但仔细看,这方印面并没有完全均分,而是有细微的移动了字与字的分隔线,这种移动完全依据于天然字型的大小和章法需要。
当然,赵之谦大师,还在章法上略略做出了调整,比如,上部三字“松、树、藏”互相之间的联结,这实际上是抱紧了三列文字,使印面不再松散,并且,这不是唯一的列与列之间的联系,因为,最后一个字“记”的尾脚悄悄伸到了考字下部留出的空地。这是对上部联结的回应。
(2)调整篆法得来的疏密
大疏大密是赵之谦最突出的风格,也是他章法上的追求,当天然字形无法实现疏密对比时,他一定会调整篆法,生生营造出来疏密关系。比如他的一方私印“赵之谦”,如图:

(赵之谦:赵之谦)
“之”字的上部两笔专门做了上提,这方印由此变得醒目,由此,疏密对比出来了。对于今天这方印来说:“松”字的木部,“江”字的工部,“考”字、“印”字、“记”字的篆法都做了明显的调整,也由此创造出各种方方正正的各种红地,如图:

(红地造成的疏密对比)
注意,这些红地,基本全部是经营出来的,不是天然字形,这是真正的艺术素养。
(3)求异
那么“江”字的“工”部为什么不居中放一个小“工”,在上下各形成横向的红地,而是拉长了中竖,变成纵向的两块红地?这当然是为了既呼应“记”字的红地,又与“印”下部生造出来的横向红地在对称位置有所区别,富于变化,不生硬、雷同。
再比如“江”与“沈”两字的三点水,两字相连,赵之谦巧妙做了处理,使它们不相雷同。当然,“松”字的“木”部与“树”字的“木”部求异处理,也是经过经营的。
(4)呼应
最显眼的呼应说一下,就是印面右上角“松”字右下部篆成了方块,这正与左下角“记”字言部的方块形成对角呼应。当然,这种呼应也不生硬,中部有树字中部的小“口”做了联络过度。如图:

(三个“口”字的关系)
我们暂时只读到这种程度,因为前面的读印系列文章分析得过细,有朋友回复提出,篆刻大师们在刻印时也没有想这么多,言下之意,似乎是我们过度解读了,所以我们把读印细微层次放宽了,有些极细微的地方,就不再说了,比如“镛”字的并笔,“藏”字的右下部方化处理。
(【布丁读印】之30,部分图片引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