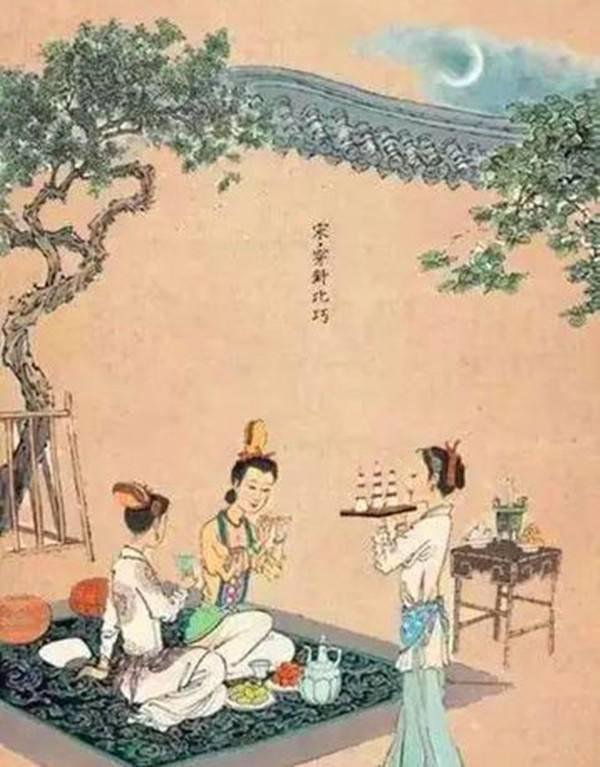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所 郭逸豪

《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美]帕特里克·格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2年2月出版,吕昭、杨光译,262页,64.00元
一
现代史学诞生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它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被构想和发明出来,之后在民族史学中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在获得成功的同时,它散发的民族主义毒气却从学界和政界蔓延开来,最终渗透进大众的意识。祛除这种意识成为令当下历史学家望而却步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族的神话》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自觉的努力,作为中世纪早期史的历史学家,他似乎在专业上更有义务去面对这个难题。
这当然与罗马帝国晚期和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历史格局休戚相关。按照“野蛮人入侵”(the Barbarian Invasions)的古老叙事,晚期罗马帝国这本身算不上铜墙铁壁的政治统一体被北方的日耳曼人穿凿而过,分裂成大小不一的政治体,或者说野蛮人的王国。这种叙事并非是现代的,它源于公元八世纪,比如写作《伦巴底人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的伦巴底历史学家保罗执事(Paulus Diaconus)就这样认为。另一份更明确的证据是一位匿名作家写作的圣徒传《国王圣西吉斯蒙的痛苦》(Passio sancti Sigismundi regis),这份文献认为,在提比略皇帝时期,就有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到莱茵河沿岸。而到了瓦伦提比安皇帝时期,这些人的后代以野蛮的方式入侵了臣服于帝国的人民和土地。这种“野蛮人入侵”的叙事一直持续到现代,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便认为罗马的衰亡是因为被征服,日耳曼民族因军事上更强的战力占领了帝国西部。
然而到了上世纪末,以奥地利中世纪史学家赫维希·沃尔夫鲁姆(Herwig Wolfram)为代表的中世纪史学界用“种族迁徙”(the Ethnic Migrations)的话语取代了“野蛮人入侵”的叙事,或者说,从“全球化和人口迁徙”这样中性的视角去看待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交往史。那么,历史学家的切入点自然从军事、战争和政治统治转向更社会化的主题,如族群、共同体、认同、身份、融合和割裂等。毫无疑问,帕特里克·格里便是沿着赫维希·沃尔夫鲁姆开辟的道路来写作这本书的。
格里认为,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尝试借助语言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在地图上描绘出族群的特点,但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些计划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族群观念是人们思想的产物。格里在书中并未特别强调和解释他本人以什么标准来区分族群,但他援引了欧洲人继承于古典时期和《圣经》中关于社会群体的类别划分,把人类分成“法律性”和“血缘性”群体,前者以法律和忠诚为基础,由历史变化的过程为转移,后者以血统、习俗和地理为基础,不以历史变化的过程为转移。
作为一名法律史学者,本人对“法律性”群体、对“法律能否以及如何塑造族群”的关注和思考,可能要超过其他非法学专业的读者。我们以希腊时期想象的族群为例,希罗多德认为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东方族群爱吃狗肉,是野蛮人。埃塞尔比亚和印度人有黑色的精液,而北方族群高大白皙。相较于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东方人生性容易更接受专制的统治和奴役,野蛮人是非理性的人,他们需要被统治。希腊人同时以“血缘性”和“法律性”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创造出一种实体论与认识论,因此在希腊人中,“法律如何塑造族群”体现得并不明显,这或许也与古希腊的法律体系不发达、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有关。而这个问题在古罗马时期,尤其在罗马帝国晚期与野蛮人的交往中则体现得十分明显。
二
“罗马人”是一个法律性的而非血缘性的族群概念。在古罗马时期,一个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生来自由人(ingenuus)还是解放自由人(libertinus),是自权人(sui iuris)还是他权人(alieni iuris),是家父还是家子,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拥有拉丁权(ius latinum)的人,还是享有罗马公民权却不拥有投票权的人,都在罗马法上有详细的区分,还有相应固定的法律程式。对罗马人而言,拥有罗马公民权即拥有“自由”(libertas),因为当遭遇鞭笞或处以极刑时,他们可以向百人团大会申诉(provocatio ad populum),《使徒行传》中的圣保罗就是最佳例子。法律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道德评价的不同,罗马人遭受刑罚的程度也不同,塞维鲁王朝时期的罗马法学家卡利斯特拉图斯(Callistratus)认为,对奴隶的惩罚要重于自由人,对声誉不佳之人的惩罚要重于声誉好的人。公元17年,元老院决议流放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占星家,而外国的占星家则被直接处死。
毫无疑问,罗马公民权是一种法律拟制,一种政治手段,是罗马从扩张之初就随身携带、以便扩大统治的法律武器。就外部而言,罗马公民权区分了罗马人与罗马联盟、拉丁人、拥有部分公民权的自治市、殖民地和其他王国。就内部而言,罗马公民权制造出不同的法律与社会地位,区分正式的罗马军团与辅助军,也因此有了人格减等(minutio capitis)这样的罗马法概念。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授予帝国境内所有居民(除丧失所有政治权利的dediticii之外)以罗马公民权,从此刻起,罗马公民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罗马世界里人与人最重要的区分——奴隶与自由人的区分,也被其他形式的区分所取代,如上等人(honestiores)和下等人(humiliores)的区分。塞维鲁王朝时期的罗马法学家马尔西安(Aelius Marcianus)在评论《关于谋杀和毒害的科尼利亚法》时说,触犯该法的刑罚是流放到一个岛屿,同时没收所有财产;如今则是处以极刑,但尊贵之人除外,低等公民喂给野兽,或者选择流放岛屿。这是社会等级和身份序列在司法适用上的明显体现。在教育上,前者推崇拜德雅(Paideia),通过教育将他们的身份发展成了更广阔的世界——罗马文化(romanitas)的一部分。又比如因宗教信仰而聚集在一起的早期基督教信众团体(ecclesiae),它们大部分出现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如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等城市,也出现在罗马城内,出现在纺织工、织补工和修鞋匠的家中。
三
《民族的神话》第四章“新蛮族与新罗马人”和第五章“最后的蛮族?”在某种程度上讲述的,是日耳曼人如何利用法律传统为王国境内的人民构建新身份的故事,而这段故事反映在法律史学上,便是古典罗马法与“粗俗罗马法”(Vulgar Roman Law)的关系。“粗俗罗马法”的概念最早由德国法律史学家海因里希·布伦纳(Heinrich Brunner)提出,从制度上看,它是指日耳曼人模仿罗马法(尤其是《狄奥多西法典》)而创设和颁布的法典,反映了古典罗马法在日耳曼化过程中的堕落和变质,包括法律语言的扭曲和法学家论述的缺失(尽管西部帝国流传着罗马法学家保罗的法律意见的摘要)。尽管如此,这些法律对塑造日耳曼人的族群,以及对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融合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包括东哥特王国的《狄奥多里克敕告》(Edictum Theodorici)、西哥特王国的《亚拉里克摘要》(Breviarium Alaricianum)、伦巴第王国的《罗塔里敕告》(Edictum Rothari)、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Lex Salica)。同样的时空和法律史素材,在另一批法律史学家看来则是关涉另一个主题,即古典晚期到中世纪早期法律秩序的历史延续性(historische Kontinuität)问题,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米泰斯 (Heinrich Mitteis)、奥地利学者阿图尔·斯泰文特(Artur Steinwenter)和意大利学者埃米利奥·贝蒂(Emilio Betti)都以此主题发表过相关论文。当然,如果把法律视为文明的一个部门,那么这种历史延续性问题可以适用于彼时文明的任何一个部门,以至文明本身。而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法律史巨擘萨维尼(Savigny)在他七卷本的皇皇巨著《中世纪罗马法史》中把公元五六世纪的法律秩序视作中世纪罗马法的形态(Gestalt)之一。
格里在许多地方都提到了公元三世纪一名潘诺尼亚士兵的墓志铭,上面写道:“我是一名法兰克公民,和一个手持武器的罗马士兵。”(Francus ego cives, miles romanus in armis)格里认为,一个野蛮人会使用“civis”(公民)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法律属性的拉丁文词语来描述他的身份、表达个人认同,意味着罗马政治和罗马法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日耳曼人。
这种法律建构不仅发生在法兰克王国,东哥特国王“伟大的”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Great)更是将“公民性”(civilitas)视为他的社会统治原则。从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的《信札》(Variae)和《狄奥多里克敕告》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窥探到,狄奥多里克国王试图说服东哥特人接受罗马的“法治”原则、兼容并包的传统和公民社会里的共识原则,并用哥特人军队的勇武对其加以保护。《狄奥多里克敕告》的序言告诉我们,东哥特国王期望用法律的权威来对抗不正义的行为、创造和平,他命令王国境内的东哥特人和罗马人都要遵守公共法律。在一封写给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的信中,狄奥多里克极其谦卑地告诉皇帝,他希望王国和平,保护人民的利益,因此要效仿帝国的统治,制定法律。
狄奥多里克执行的是一种被称为“族群论”的意识形态(ethnographic ideology),它将作为士兵的哥特人和作为平民的罗马人——或者说,把士兵和供养他们的纳税人——区分开来:罗马人纳税,哥特人收税;罗马人产粮,哥特人战斗。体现这种意识形态的著名例子是卡西奥多罗斯《信札》第七卷的法律程式三,名为“一个特定城市的哥特总督诉讼程式”(Formula comitivae Gothorum per singulas civitates),它规定,如果争讼发生在两个哥特人之间,就让指派的总督(comes)参照“我们的敕告”,即《狄奥多里克敕告》来裁判;如果争讼发生在一个哥特人和一个出生罗马人之间,那么总督可以接纳一名专业审慎的罗马人(prudente Romano),基于公平的理由(aequabili ratione)来平息争讼;如果争讼发生在两个罗马人之间,那么就让派去行省做公诉人(cognitores)的罗马人来听讼案件。罗马人和哥特人适用不同的司法系统,依据各自的法律审判,只有如此才能造就普遍的和平,让哥特人和罗马人都能享受仁慈的神性和甜蜜的悠闲。狄奥多里克告诉哥特人,罗马人是他们的邻居,与此同时他也告诉罗马人要爱哥特人,因为是哥特人在战时保卫“普遍的共和国”(universam rem publicam)。至此,狄奥多里克用法律塑造身份的策略已经昭然若揭,就血统而言,东哥特王国内生活着两个民族(nationes),就法律而言,王国内只有一种人民(populus),他们尽管在适用法律上有所差别,但都生活在同一个共和国内,他们一起保卫共和国,一起享受和平与悠闲。
除此之外,狄奥多里克还重启了罗马人所熟悉的“自由”话语。无论对哪个时代和哪个民族而言,自由的意涵都是多重的,然而,法律意义下的自由是罗马人最重视且实践最久的,它意味着不受政务官随意处罚的“向人民申诉”制度和保民官的援助权(ius auxilii),这两者被历史学家李维(Livius)视为罗马自由的两个堡垒。在一份拉丁文碑铭中(CIL, X, 6850),狄奥多里克被塑造成“自由的守卫和罗马之名的保护者”;在以他名义所写的书信中(Variae, 3. 11. 1; 3. 43. 2),卡西奥多罗斯将他描述为“自由的主人”和“自由的保卫者”。狄奥多里克的“自由”话语不仅是政治宣传口号,它还具体体现在上述非均质统一的法律程式和司法设置中,我们似乎可以把他的统治策略简单地概括为一体两面,两面中的一面是法律制度,一面是民族政策,一体是自由、和平和统一的,具有公民性的哥特王国。
同样,法律也是塑造伦巴第人的重要工具。从七世纪中叶开始,在伦巴第人王国中服务的、来源多样的蛮族战士都被要求服从伦巴第人的法律,除非国王同意他们可以实行另一种法律传统。在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继任后,他颁布的法律反过来塑造了“罗马人”的身份,这些法律既不将罗马人等同于意大利本土居民的后裔,也不将罗马人等同于遵循罗马法的人,而是将罗马人等同于那些生活在意大利土地上,通过拉文纳被拜占庭帝国直接控制或被教宗控制的居民。由此,“罗马人”在伦巴第王国兴盛的时代,变成了一个政治性和地区性的称呼,基本等同于支持拜占庭的政治力量。
四
在中世纪的西欧,最终取得族群认同胜利的不是法律,而是宗教。西哥特人试图开创一种有别于东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政体:建立并维持两个社会群体,一个是正统教会的、罗马人的、公民的社会群体,另一个是阿里乌斯派的、蛮族的、军事的社会群体,并将这两个社会群体统一在一个获得罗马帝国授权的蛮族王国的领导之下,但这种政治体制以失败告终。我们可以说,阿里乌斯派信仰构成了西哥特人身份的重要元素,正是由于这个信仰,才造成他们与信仰正统基督教的罗马人的决裂,也导致上述西哥特人尝试开创的政体的破产。
宗教塑造族群的最终胜利在时代上超出了《民族的神话》这本书的范围,大致要到加洛林王朝时期,此时,罗马帝国等同于由拉丁基督徒组成的基督教王国(res publica Christiana),欧洲王国(regnum Europae)的概念也被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加以利用。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也承认政治与法律意义上的罗马帝国位于东方,以达成宗教意义上的西部基督教王国与政治意义上的东部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局势(faceres imperium bipartitum)。因此,宗教构建出了普遍基督教王国的国民,与其相对的是异教徒,是犹太人和萨拉森人。不同基督教王国之间的战争被视为是“内战”,而针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是“正义战争”,是国际法意义上的。
法律塑造族群的故事到近代早期的十六世纪才被重新接续上,从法律史角度来看,那主要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家的贡献,而它的大背景是普遍基督教王国的覆灭,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近代主权国家抛弃了几百年以来对法律(包括宗教)“普遍性”的追求,摈弃了对罗马法的适用,期冀挖掘出本国的习惯与习惯法,致力于编纂习惯法的法典,用本国的法律塑造国族的认同,而这种以法律塑造族群认同的努力,最终在各国民法典编纂和“国民”与“公民”的概念中达到了巅峰。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