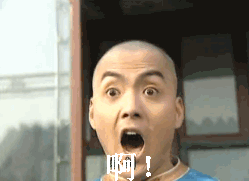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新发现了钱锺书英伦藏书四种,其中有签名、钤印,以及大量未刊批注。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晓明告诉澎湃新闻,这批钱氏藏书是知名翻译家郑大民于2019年所赠西文旧书中的一批,推测可能是由钱先生赠与徐燕谋,再由徐转赠其父。徐燕谋为复旦大学已故外文系教授,也是郑大民父亲的老师,钱锺书与之过从甚密,以兄事之。
湖南师大外文学院教授曹波提供的线索,似乎与这种推测相印证。钱锺书之父钱基博是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大前身)中文系奠基人,1939年邀钱锺书到涟源任英文系首任主任,但不到两年即回上海,这四本书当时可能就留在了湖南。而随后继钱锺书主持国立师院英文系的正是徐燕谋。
当然,也不能排除是郑大民父亲直接从外文书店所购,但无论哪种情况,在相关诸人均已故去的情况下,都已很难考证。
如何判断是钱氏藏书
据发现并整理的馆员赵晨鸣介绍,在整理这批旧书时,通过首页右上角的钱杨花体英文签名,“海天鹣鲽”“中書君”的钤印,内页的笔记标注方式、字迹和内容等,推测其中四种为钱锺书藏书,分别为:

“海天鹣鲽”钤印及二人手书花体签名
第一种:Essays about Men, Women, & Books,Augustine Birrell著,伦敦Elliot Stock,1894年出版,有签名,有“海天鹣鲽”藏印,有标注;
第二种Victorian Literature: Sixty Years of Books and Bookmen,Clement Shorter著,伦敦James Bowden,1898年出版,有签名,有标注,内附卡片7张13面;

英伦藏书书影之一:Victorian Literature Sixty Years of Books and Bookmen Clement Shorter
第三种:Res Judicatae, Papers and Essays,Augustine Birrell著,伦敦Elliot Stock,1892年出版,有签名,五页带有钱氏笔记;
第四种:Eight Victorian Poets,F. L. Lucas著,剑桥大学出版社,1930年出版,有“中書君”藏印,数十页带有钱氏笔记。

“中书君”的题签;钱杨二人的手书花体签名及购书时间地点:Ex libris Chung-shu Ch’ien, Chi-Kong-Y Ch’ien”(钱锺书、钱杨季康藏书,1936年5月15日,牛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金雯告诉澎湃新闻,F. L. Lucas是英国古典学学者,1923年猛烈抨击艾略特《荒原》,散文笔法也很著名。Clement Shorter是英国记者和文学评论人,应该不算很知名。
另外两本的作者Augustine Birrell是19和20世纪之交英国一位不算很成功的政客,曾经在爱尔兰独立前夕担任爱尔兰秘书长,因为没能阻止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而辞职。“不过他的文学类随笔和纪实写作享有盛誉,知识渊博,笔触灵动诙谐,这可能也是钱先生仔细阅读这本书的原因。”

钱锺书杨绛二人欧洲时共有的“海天鹣鲽”藏书章
已具备良好法文德文阅读能力,指向某种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
金雯认为,四本藏书中,“只有两本书——Eight Victorian poets和Res Judicatae中有批注,也只有后者,可以认定是钱先生的批注。我个人觉得,Res Judicatae里批注的字迹与《外文笔记》中的完全一致,风格明显,应该是出自钱先生亲笔。”

Res Judicatae:Papers and Essays一书中,附有此书前主人藏书票一张:沙漠中一头骆驼望向前方,带有 “Per ardua ; patiencs et longueur de temps font plus que forcs ni que race”( 耐心与日久胜过强力与狂暴)
Res Judicatae中有近三十页有批注,金雯按内容大致将其分成三类:一是对作者文学性评论的回应或补充,往往采用第二人称的口吻,似乎在直接与未曾谋面的作者进行对话;二是钱先生自己的发挥,将所读到的某个文学典故或文学史事件与其他类似现象联系起来,有时候还会对联想到的文学作品做摘录;三是钱先生对自己未来思考方向写下的提示。这类批示很少,因为新颖而颇引人入胜。
在金雯看来,Res Judicatae中的批注与《外文笔记》第一辑应该是同时期的,两者可以参照起来读。笔记中在摘录所读书籍的时候,也会插入一些批注,包括表达读者立场、提出质疑和发挥引申这些内容,这些批注与Res Judicatae中的批注风格是一致的。
批注除了英文,还有法文和德文。但在这里,钱锺书对于法文和德文的使用相对简单,法文方面是提到了几个生僻的法语词汇,德文方面是有一句摘抄,一句自己写的德语句子。
比如,书中提到柯尔律治对于吉本的贬低,柯尔律治认为吉本空有世界历史知识,却无任何哲学洞见,钱先生犀利地发起辩驳:“必须承认柯尔律治有时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与席勒、黑格尔那帮人相反。(认为)世界历史无足轻重。来自世界的:不重要。”这个批注的最后两个短句用德语表述(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Coleridge is sometimes a pretentious fool. Pace Schiller,Hegel and co. Die weltge schichte ist gar nichts. Vom welt: garnicht)。钱先生写德语字母的时候基本上按照德语手写体的规范,与英文手写体不同。
“可以说,钱先生在这两种语言上肯定是具备了相当好的阅读能力,也有简单使用的能力,尤其是对复杂词汇的记忆让人赞叹。”金雯认为,可以认为钱先生在批注中已经指向某种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比如发现了法语诗歌与英语诗歌在某一些意象上(如“泪水”)的共通之处。
“不过笔记和批注仍然是笔记和批注,我们不是很清楚假如要做比较研究的话,研究方法、框架和旨趣会是什么样的。当然,根据《谈艺录》中所说的‘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这个原则,可以想象钱先生这时期与后来的许多批注和笔记能够汇聚成成型的研究。”


批注中展露钱锺书难得一见的学生姿态
批注中仅有一例有关自己未来思考方向的提示性批注。在比莱尔论库柏这一章中,钱先生难得用中文英文夹杂的句式留下了一个批注,批注已经墨色隐约难以辨认。金雯猜测内容如下:“把Cowper的nature poems 放在他的遭遇和背景下来考察,找出它们与The Seasons以及Wordsworth的nature poems的不同”。
“这里钱先生是在给自己鼓气,做出一个规划,希望能在日后深入了解自然诗从18到19世纪的变迁。可能因为这个批注凸显自己的不足,其语言风格都发生了变化,批注人犹如突然从意气高昂的年轻学者变成了低眉顺眼的学生。”这种学生立场的瞬间,金雯认为,在钱锺书已出著作中并不多见,“只有在批注中才可能发现吧。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外文笔记》中摘抄的形式本身就是学生立场的一种体现。”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赴牛津。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名Bodleian Library,钱锺书译为“饱蠹楼”,虽藏书巨丰,但不能外借,二人遂手抄笔记。赵晨鸣介绍,除了图书馆,他们还常到“牛津一条街”和各类书店淘二手书,杨绛先生曾赞叹钱锺书有双识书买书的慧眼。相比图书馆的严格规定,自己买的书就可以随性标注,“钱锺书会在书页空白处随手记录心得与评论,兼有多种语言(所见有英、中、法文)。”
在牛津的两年,在金雯看来,是钱先生能潜心攻读西学著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他开始详细记录自己阅读历史的开端。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