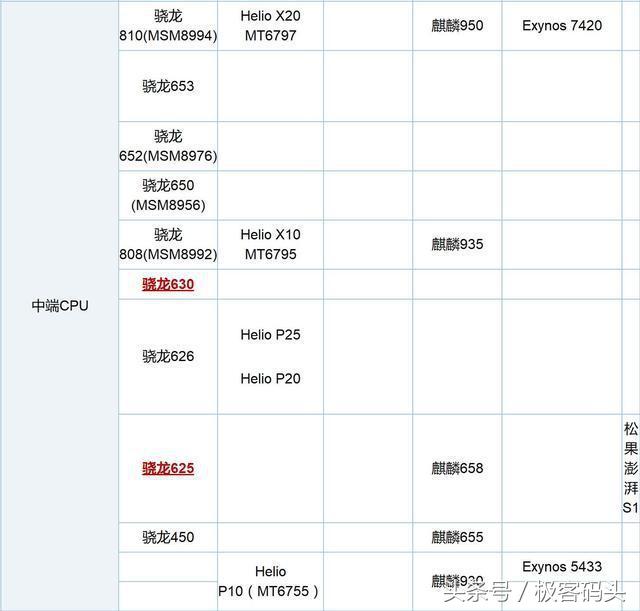专题 · 舞出青春中国梦
作者 | 《中华儿女》记者 王海珍
编辑 | 王碧清

华宵一
华宵一年少成名,2009年第九届“桃李杯”舞蹈比赛中,以作品《罗敷行》获得中国古典舞A级少年甲组(女子)一等奖。那一年,她十七岁。2012年“桃李杯”大赛,她以一支《点绛唇》,再次惊艳全场,蝉联“桃李杯”大赛一等奖。其后,她在第七届全国电视舞蹈大赛中获古典舞最佳演员奖。她的《罗敷行》和《点绛唇》是国内古典舞领域经典中的经典,被后续无数舞蹈爱好者学习,甚至成为范本,是古典舞学生必修课。
2017年,她担当主演和制作人的《一刻》舞剧,开启全球巡演,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至今已经走过多个城市。随着她参加湖南卫视《舞蹈风暴》第二季,与歌手、演员、音乐制作人张艺兴一起录制《冬梦之约》、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与音乐人胡彦斌合作《对月》,参加B站、河南卫视《舞千年》舞蹈节目录制等,她的名字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在人生这条漫长又曲折的路上,舞蹈能和我不离不弃、形影不离。小时候,它是我的爱好;长大后,它是我的看家本领;现在,它是我的职业,融入我的生活,是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就职于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华宵一如是说,“起舞时,所有人看着你、倾听你、举起手电筒照耀你时,你会觉得,作为一个舞者,幸福而又值得”。
舞蹈是与外界交流的方式
现在的华宵一想象不出,如果不跳舞,她还会去做什么。对于她来说,舞蹈如此重要,没有它,怎么可以?舞蹈已经融入她生命每一刻。
华宵一的舞蹈之路,始于父亲。父亲对舞蹈有着炽烈的爱,爱到要让自己的孩子也承继他对舞蹈的爱。大凡父辈未竟的梦想交接到下一代,常常会有相对叛逆的结局,有人逃遁,另谋他路;有人走到中途,不堪重负,怨怼丛生。但华宵一和父亲却携手在舞台上,一直走下去——六岁时,华宵一在父亲引领下,开启学舞生涯;十一岁,她考上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父亲陪伴着她;现在,她在《一刻》起舞,父亲与她同台。华宵一是幸运的,有父亲一直的支持和陪伴;父亲也是幸运的,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和他一起将梦想照进生命,在舞台上挥洒极致的美与热爱。
华宵一不太爱讲自己勤学苦练的事,以及练功受伤。她更喜欢分享触觉、感受,那些感性的瞬间、触碰心底柔软的时刻。“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去老师家学舞,都是爸爸带我去。到老师家,要走一个斜坡,这个斜坡挺长,父亲就背着我,我趴在他后背,能听到他的呼吸。”华宵一脑海里常常回荡这样的画面。这仿佛是父亲与她在舞蹈这条路上的隐喻,路并不那么容易走,要坚持,虽然会很累,但终会抵达。
华宵一十七岁获得全国大奖,奠定在古典舞界的地位,其后持续多年巅峰状态,很多人都说她是天生的舞者。她对这样的说法只是笑笑,“我小时候学舞蹈,身体条件不能说是最好的。也遇到过挫折,考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才考上”。坚持的背后,是深深的喜爱;成功的背后,是更多耐力、更加坚持。
她喜欢舞蹈,舞蹈不言,却直抵人心。舞蹈是这样一种存在,集合极致的力量与美。那些瞬间的爆发力,那些转瞬即逝的美,每一刻都无法重来,无法复制,它是如此极致地将时间与生命复刻在一起。舞者在每一个舞动的瞬间,都是在用自己的肢体乃至生命与外界去沟通,去交流。华宵一喜欢这种感觉,她敏感的触觉和对生命极度敏锐的感知力,在舞蹈时,全部打开、释放。舞蹈接住她流动的思绪和情感,她也赋予舞蹈丰富的情感和表达。
在《罗敷行》里,她是性情机敏、容颜娇俏的翩跹少女;在《点绛唇》里,她又化身情感细腻、满怀期盼的少妇。在诗词歌赋里住了几千年的古代女性们,出现在现代舞台上。华宵一形神兼备地演绎着她们,赋予她们以情,以境,以韵,让她们可感,可知。华宵一身心并用、内外一统的古典演绎方式,仿若将这些美好的古典女性复活。
舞蹈这门艺术,与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一样,技法技艺全然掌控之后,并不代表能达到至高境界,更重要的是,敏锐的感受力和认知。这一层只可意会,不可言说,或许就是匠人和艺术之境的差别。艺术就是这样残酷。华宵一仿佛很早就知道这一点,每一寸身体细胞自由打开,也同时打开那些细微的感受力。她会思考,怎样能走入自己表演的舞蹈,不仅仅动作技法到位,更重要的是,情感纤维的贴合。

舞蹈中的华宵一
她知道古典和现代生活有一定距离,古典舞不仅仅是动作的复古、表情的一颦一笑,更重要的是情感共鸣。时空流转,表达方式虽不同,但人类有些共同情感并没有改变,那个年代的人,甚至更含蓄、内敛。如何表达欲说还羞的情感?华宵一一直在琢磨。“大音希声,大美不言。”从小一直在跳舞,和美在一起的华宵一明白这一点,如何表达?一定是需要想象力。“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想象可能是在月下、在河边,产生一种和观众之间的共鸣。”情感的共鸣,是她走近罗敷们、走近观众的方式。
她知道,不同阶段演绎同一个舞蹈,会有不同况味,就像人们看一本名著,不同年龄段,品读出来的感受都不同。她把自己的经历、对人物的理解,融入进去,每一次《罗敷行》《点绛唇》,都与之前表演有所不同。她拒绝单一,更不愿意重复。
《一刻》里做自己
2020年10月10日,《舞蹈风暴》第二季开播。华宵一出场,引起舞蹈界关注。第一季《舞蹈风暴》亚军李响说:“之前一直有人说,我是《舞蹈风暴》舞台上古典舞的标杆。我想说,那是因为华宵一那会儿没有来。”
由此可见,华宵一在古典舞界的地位。华宵一感谢这样的认可,更清醒地看到赞誉背后自己还需更多努力:“越是别人觉得你是标杆,都在学习你、欣赏你的时候,越重要的是你自己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不然就可能会忘了自己。”华宵一说,前路还有更高处,需要跨越和“牢牢抓住”。她不把自己拘泥于古典舞,她想探索更高、更远的可能。
她已经在尝试不断突破、延展、拓宽自己。她一直都善于思考:那些流动、漫溢的思绪,感性、脆弱的细微,需要有力的理性去厘清、分辨,哪些可以随风而去,哪些可以留在心里养护滋润,哪些可以屏蔽。她敏而好学,她的感性和理性一直很好地分工合作。
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大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她作为交换生,前往纽约。在纽约,她如饥似渴地去各个剧场看演出,吸收不同舞种的养分。一次演出,她看到世界编舞大师阿库让·汉(Akram Khan)的现代舞作品。她记得,舞剧《源》(DESH)中,他独自一人在舞台上跳了一个半小时,那种“丰富有意趣的身体语言,自由而独立的表达”让她震撼。或许就是这场演出,埋下她与阿库让·汉合作《一刻》的缘分。
2017年,华宵一25岁,决定去做和以往不同的事。她不甘于只在舞台上演绎古代美好的女子,作为一名舞者,她想要演绎对生命的理解,演绎自己。这位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的北方姑娘,找到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许锐,国内顶尖编舞家高成明,曾在荷兰舞蹈剧院(NDT)担任编导、资深舞者、自由编舞家娄梦涵,跑到英国,请来阿库让·汉。那些曾经让她为之心旌摇荡的感动瞬间,她一一留存在心底,当机缘到来之时,她将那些储存很久的想法、心动的时刻打捞出来,让它们在舞台上继续生长。
“我想实现一次自我突破,尝试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丰富。”华宵一直言不讳,现代舞的表达方式,对于跳了十几年古典舞的她来说是陌生的,“韵律和起承转合都会不一样”。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肢体,想表达的思想、所处时空都会不同。她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以前像在古代说文言文,现在是到了现代,要说白话文”。
对于一名在古典舞中取得骄人成就的舞者而言,转换并不容易,人皆有惯性,身体也有固有记忆。“一开始,怎么做都觉得很别扭,感到自己是刻意去做动作。因为当一个动作发力对了,或恰到好处,自己会很舒服。”华宵一的倔强与不服输模式开启,越是不容易,越要去挑战,当初选择跳现代舞不就是想要某种挑战吗?她并不畏惧。古典舞与现代舞的转变,需要很长时间适应,这个过程,也是逐渐找到自己的过程。从最初的别扭感,到后来如鱼得水,华宵一仿佛也藉由此,重新认识了自己。
2017年,舞剧《一刻》由四部独立舞蹈作品构成——《眺》《独自起舞》《未完》和《滑》。
作品《眺》,极有东方美学中留白意味。华宵一身着白衣随风而舞,颇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意象。华宵一表示:“在强烈灯光下,我觉得整个世界只有我。身体在宇宙里,被风一片片吹掉,像毁灭与重生。”这一强风与灯光的设计,是高成明别具匠心的结果:集中的一束光打下,全场焦点只有舞者。
娄梦涵担任《独自起舞》编导。编者与舞者相遇,灵感可遇不可求。在娄梦涵眼中,“宵一是一个善于思考的舞者,她的身体没有一刻的放松,大脑也从未停止运转”。
阿库让·汉被誉为“21世纪舞坛第一传奇”,此前与东方舞者合作,仅限于参与中国台湾云门舞集的编舞,与华宵一合作是他与东方舞者的再度惊喜相遇。在《未完》的编排中,他融入自己对于“记忆”的思考:他想表达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在舞蹈中,华宵一引入一个黄衣小女孩,以摇铃警示。这是华宵一的记忆触点,那个黄衣小女孩就是过去的自己。一如阿库让·汉所言:“我们慢慢老去,离人生终点越来越近。但与此同时,我们距离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记忆也越来越近。”华宵一对于《未完》的解释也颇有深意:“《未完》,是我与这个世界的交流,是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最后一幕作品是《滑》。编舞还是担当《眺》编舞的高成明。高成明说:“作品的结构是一头一尾交相辉映,冥冥之中还有一种勾连。”《滑》这一幕的表现方式,让现场观众为之震撼。舞者怕滑,这一幕就是让舞者滑,几米见方舞台,铺上白胶布,上面涂满油,制造一个容易滑倒的环境,华宵一就在油布上跳。“这很考验的,”华宵一说,“舞者最怕滑,一滑就站不稳,也没办法借力发力,你怎么去克服、适应、融合,很关键,要花时间不断在上面磨”。华宵一在铺满油的白胶布上起舞,不断跌倒,不断奋起,身躯有时看似筋疲力尽,有时又昂然傲立,仿若人生旅程。没有人能顺利抵达终点,摔倒就再站起来。最后一幕剧,华宵一身体力量与情感张力表达,已到极致。每每到这一幕,她的眼泪随着音乐收尾和灯光转换,缓缓流下。
她曾在微博上写下:“滑才是人生常态。每一次小心翼翼到平衡的喜悦背后,总会有新的失衡等待我们。滑从来都不可怕,只要身体里蕴藏积聚足够爆发的力量和信心。每一次的滑,是为了不滑。每一次不滑的历程,又是笑对再次滑的勇气。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现世安好,所有的平静,不过是每次树欲静而风不止中,不断挣扎平衡的再一次出发。”这是她对人生旅程的某种注释,某种解答。
整部作品取名为《一刻》,她觉得,“一刻”里蕴含太多内容:紧张、慌乱、不安、叹息、收获、拥有,种种情绪,都可以通过肢体去表现。“没有什么比舞动的身体更能表达生命的脉动。”《一刻》是华宵一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作品。她自己也担任制作人。跳舞之外,作为制作人,她承担项目所有环节。这部囊括多方主创的作品,她是最合适的协调人,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表达自我。她将《一刻》看作自己的标签,她很在意的标签。
制作《一刻》,华宵一遇到太多没有料到的问题,包括各种突发状况和阻碍。她发现,拼到最后,拼的已经不是技术,而是意志力,“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住”。“跳舞也是,有些动作一开始觉得永远不可能完成,看起来根本不成立,但是编导会坚持,最后真的练出来了。”与世界顶级编舞者合作,成为她生命中重要收获。“合作过程很愉快,彼此容易沟通,很多时间觉得心意相通。在他们身上,学习到最重要一点就是‘忘记自己’。”
《一刻》诞生四年来,经过迭代成长,华宵一称之为《一刻》PLUS版。2020年,她又在《一刻》中,加入一幕剧《山丘》,由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中国舞编导专业黄佳园担当编舞。作品《山丘》围绕“何处是高处”哲学命题,将人对“何谓高处”的困惑,转化为一次“不能停下”的奔走游戏。作品以粗线条语言形式,在人和椅子的关系构建中,营造出“停顿”那一刻的漫长思考与回味。
回味剧幕中的道具椅子,华宵一有很多感触:“有的人拿来椅子,又拿走那些椅子,他们在舞台上来了又去,也是一种襄助,一种托举。”她敏捷而细腻的感触力,总是随时随地迸发,但她更知道,如何妥善安置这些情感。一个舞者,需要有强大爆发力,情感丰富但不能泛滥。那些途经心田或湍急或缓慢的水流,她会去感受、觉察,待到表演时,便汇聚成滔滔江河,用身体语言表达出去。作为一名舞者,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她找到生命内在与外界的沟通方式,并乐此不疲。

舞台上的华宵一
一如她所说:“这里有最真实的我,有我对生活的理解、对过往的凝练,有我的人生态度。每个作品里都蕴含不同的哲学思考,到最后百川归海,以一种最接近生命底色的纯粹质朴呈现出来。因此,观众能够感受到一股生命的张力,他们在那一刻与我一同呼吸,在我的身上看到自己,看到人生中每一个刻骨的瞬息。”
舞蹈中见自己
湖南卫视《舞蹈风暴》第一季时,华宵一收到邀请,当时她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拒绝了。
《舞蹈风暴》第二季节目开录前,编导又找到华宵一。她明白,人生中面对的事情和机遇,大多不是在做好准备后才来的。之前排练《一刻》不也是这样吗?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准备好,才接住的吗?并没有。这次她决定参加。
她将舞者参赛时的紧绷状态喻为拍皮球,“你压得多低,你才知道可以反弹得多高”。不管是参加节目,还是平时比赛演出,华宵一对输赢没有那么看重。对她来说,所谓PK,更像是在吸引她不断向前,她更愿意跟自己比、跟时间比。“比的过程不是把自己越比越窄,而是要把自己越比越宽,如果这样想舞蹈,可能我们会更加开阔。”
站在《舞蹈风暴》舞台上,她感受到一份熟悉的孤独。“可能是那些灯照在台上,像星空一样,而你四周都是黑的,就我一个人。特别像我一个人在练功房的时候,也特别像我这两年的心态。舞蹈,就是孤独的艺术。你内心那份笃定,其实是靠你不断地孤独地获得成绩,或者说是自我坚守才得来的。”恍惚中,她又看到《一刻》中的自己,“站在时间的轴线上游走,沉沉浮浮,有一种感觉——这世界本是你自己”。
在华宵一看来,综艺舞台与剧场演出感觉不太一样。剧场演出,她可以用一个半小时酣畅淋漓的演出,让观众沉浸其中,层层递进,与舞者共鸣。但在综艺舞台上,她只有几分钟来进行故事的表达和情感的承载,“在这个时间里,你所要表达的、承载的都很多”。但就是那种浓缩的表达,与国内顶尖舞者一起演绎,让她在每一次表演后都有惊叹,原来自己还可以这样做,原来自己有这样的一面。一如她在舞台上演绎的宫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舞蹈的时刻探照自己,更为全息角度地认识自己,输赢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舞动的过程,那些瞬间,那些“一刻”,以为它滑过,却又参与塑造自己的过程。

舞蹈中的华宵一
“车到站了,但路依然要勇往直前地去闯,每一步小心的试探和大胆的尝试都会值得。感谢舞蹈,让我有幸用身体描述我爱的世界,于无声中传达内心的感悟。”华宵一对舞蹈常常心怀感恩,“舞蹈带给我的快乐远大于付出时的辛苦,哪怕是一点点快乐,我都很满足。回头看时,每一个曾经都有着无法细数的刻度。每一个星光闪耀的时刻,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正是那一段时光,不抱怨、不诉苦、不浮躁,最后度过这段感动自己的日子。我要感谢舞蹈这个奇妙世界,让我以舞蹈去语言、去倾诉,让我用舞蹈,去磨练自己的内心和身体,学会耐得住寂寞与孤独。我要感谢它带给我的所有”。
还有她的父母、家人、老师们,她是幸运的,身边围绕着爱与奋进的力。她不用与逆境做战,消耗自己;她只需要与自己交战,丰富自己。对这个美好的世界,她葆有深深的爱。她期待用敏锐的感受力与想要不断认识自我的探索力,去发掘自己更多潜能,让自己更深刻地去表达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她起舞的每一刻,都是对生命的极致描绘,是每一秒对热爱的不辜负。她期待未来的自己,不仅仅让更多人看见,也要让更多人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