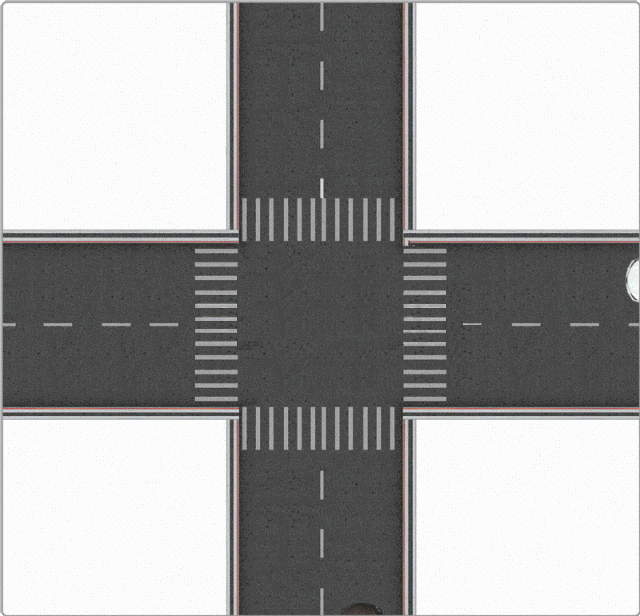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我是1949年参加屠甸区粮库工作的,当时就去殳山乡和区政府的同志一起,搞借粮和征粮准备工作,主要是动员农民缴爱国粮。
因为刚解放,老百姓对政策还不太了解,所以征粮动员工作相当艰苦,得一家一家上门去说服。但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50年5月初,我被调到桐乡县人民政府粮食局工作,当时局长是李紫林,我被分配到储运股工作,股长是史禄清。不久,我们粮食局接到任务,就是要我们运粮食去支援上海,局里把支援上海粮食的押运任务交给了我。
事情是这样的。上海解放后,一些不法份子捣乱市场,大量抢购囤积粮食,造成粮价一天比一天上涨(记录者注:上海解放后,曾发生过“三战”,即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粮油之战)。
就说米粮吧,大米每个人天天要吃,上海的一些不法粮商,以抬高价格大量收进大米。他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囤积居奇,待市场没有大米了,他们就高价出售,剥削老百姓,刮民脂民膏;二是造成粮食紧张,人心恐慌,给刚建立的人民政府压力,企图动摇人民政权。
他们说:你共产党打仗可以,搞经济不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接到了上级命令,要我们粮食局给上海调运粮食,支援上海解决粮荒(记录者认为,这应该是华东局或华东军政委员会给江浙两省的命令,调粮食支援上海市人民政府解决粮荒)。
我们粮食局接到命令后,在桐乡当时的大顺公米厂(在现在的城河路)、乌镇米厂加紧加工大米(当时只有这两个厂指定为国家粮库加工大米),加工好后立即装船。当年都是私人的风篷船(帆船),以风作动力,一般一只货运船装二三十吨。
运输途中需有人押运,局里让我当押运员。我们多数是下午装船,夜里开船,第二天上午前到嘉兴。我的任务是随粮船从桐乡确保粮食送到嘉兴专员公署直属库办理交接手续,由他们负责装火车运到上海。给上海支援粮食,我负责了多次专运押运任务,直到支援任务结束。
由于江浙两省大批粮食支援上海,解决了上海居民有粮食(大米)可购买,粮价平定了,粮荒解决了,人心稳定了,上海人民热烈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而那些搞投机倒把的不法粮商,原想搞囤积居奇发狂财,结果人民政府平价供应粮食,那些不法粮商也只有平价出售粮食,有的不法粮商就此破产了。
第二次押粮任务是这样的。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50年朝鮮战争爆发,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志愿军入朝参战,首先当然需要武器,但是志愿军不能没有饭吃,所以后勤工作同样成为急需。我们江浙沪一带主产大米,支援抗美援朝,供应前线粮食就成了义不容辞的支前任务。
当时嘉兴专员公署专门成立一个抗美援朝粮食转运站,地点设在嘉兴火车站仓库。转运站任务就是接收各县送来的粮食,再由我们押送转运东北。每个县抽调2个干部到转运站工作,我们桐乡县粮食局又抽调我和凌树源2人(说明:凌树源同志只押送了一次任务,后来就回桐乡了),就成了我一个人。我在嘉兴转运站住了10个月,实际押运粮食去了7次东北。
下面我来说说押运粮食任务的具体情况。
当时支援抗美援朝的大米,都是用双层的龙头细布做米袋,每袋装50斤大米(25千克),主要,一是龙头细布袋结实;二是便于搬运,所以不用麻袋。当时装粮食的火车都是敞篷车,就是上面没有篷(棚)的货车,每一节车箱可装40吨或60吨大米的。一列火车有24节或30节的车箱。大米装完后,每节车箱就盖上绿色帆布帐篷,固定绳索。只有两节车箱留出押送人员居住的空间。
每一列车由4个人押运,前2人后2人。装好粮食后,由嘉兴出发经上海(沪杭线)再在上海西站转到京沪线,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到南京。到南京后还得摆渡过长江。有时要等待很长时间,这渡轮很大,轮船上有三条铁轨,如24节车箱,每条铁轨装8节(30节每条装10节),装好后,可以一次渡过长江。
渡轮开到浦口,再把车箱拉到浦口火车站,又要重新进行编组,从南京到浦口有时要一天时间。铁路上的火车头是分段的,到了另一段就要换车头,一路上还要加水和碰到直快客车、特快车,还要停车交换。虽然我们货运车属于军列,比其他货车要快,但还是比较慢的。不过火车出了山海关后,东北铁路都是双轨道,减少了交换,速度就快了。
我押运了7次列车,其中1次到铁岭市,6次到沈阳市。每次运输其实我们押车员根本不晓得送到哪里,由车开到那里算那里。每次列车到目的地车站货场后,这次的长途运输就算结束了。
接下来由货场的火车头,由铁路员工指挥调度送到铁路专线停靠在仓库站台,才能正式办理交接手续。我们押送员跟着调度车走。
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志还站在火车头前面的踏板上,火车开了,看着脚下的铁路帎木往后飞速退去,心里好紧张,这真是一次难得的一生经历。
交完货后,我们在沈阳市就可以到市里去白相(玩的意思),看看沈阳的市容市貌。特别是冬天,在街头能看到有的老人,胡须上都结了冰珠。他们习惯了也无所谓冷不冷。我们住在粮库招待所,管吃管住。等到正式办完手续拿到证件后,再去买沈阳到上海的直达客车,回上海再转车到嘉兴。
我们每押运一次,大约要八至九天时间。你问到我们押运员当时的生活状况?那我就来说说我们押车员的车上生活。
我是1951年5月去嘉兴转运站到1952年2月回桐乡的,经历了夏秋冬三个季节。当年我们押运员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夏天住在蓬布下面,闷热难当,秋天好一点,到了冬天,北方特别寒冷。
比如11月,在我们嘉兴气温还是暖和的,但一到东北就相当冷,真是冰天雪地,所以组织上就发给我们长皮大衣,里面是羊毛的,还有棉鞋。在东北,风吹到脸上,就像刀子在刮,因为那时我们都是青年人,忍受力强,总算没有冻坏。但是,因为我们送粮的列车都是敞篷车,车上面只盖一块蓬布,每到大站,火车停靠时间长时,我们就得下车去检查捆蓬布的绳子有否松动,松了就得拉紧,以免蓬布让风刮飞了,这是我们押车员的责任。
那么这一路,我们的睡觉怎么办?就睡在留岀可以住人的那节车箱空间米袋上,人就在蓬布下,不睡时就坐在米袋上。
由于蓬布盖上后不通风,为了通风呼吸,不致闷死,就用一根竹杆把蓬布顶高一点能通风,高度很低,所以不能站立。身子不能朝向前进的方向,因为当时的火车都是烧煤的蒸汽车,煤烟很大,居住的车箱只能朝后面,如果朝前,开车时风大吃不消。煤灰更严重,这样一天下来,也是一脸煤尘。这里要说明的,当年没有给我们发被子,我们睡觉,夏秋季节穿随身衣服,冬天就是抱着皮大衣睡,几天几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
哪么我们吃饭怎么办呢?当时车站站台上,都有推着车卖食品的,每到一个大的停车站,就到车站买吃的,多数是面包。如果车刚巧在符离集停车,大家就下去买烧鸡吃,改善一下生活,增加点营养。到了沈阳后,我们就吃不惯了,早晨吃小米粥还可以,中饭夜饭吃高粱米饭,大家真的吃不下,但也只有吃。
最有趣的就是大小便。讲个小故事,我们押车的4人都是男同志,小便拉出就是,但在篷车上大便怎办呢?能坚持就坚持,实在坚持不了,火车在开动,只有拉住棚车的栏杆,管他下面是铁路,往下大便就是,只要千万留心不让自己掉下去就是,掉下去肯定死了。
还有一个笑话,列车到锦州车站,按常规,锦州是个大站,停车时间比较长,嘉善县的一个同志去车站大便,可当他大便好了,列车却开走了。那个嘉善的同志急得没有办法,他只有到车站找到军代表,给他看了证明,当年我们押车员,上级都发有身份证明书,这时正好有一列军车开往前线,也停在锦州站,就让他上了这列军车(享受了一次有篷车)。军车开到大虎山才追上我们运粮车,他才回到自己车上。
还有一次挺让女同志们尴尬,那是一列军车,当时送志愿军到前线军车很多,他们乘坐的不是客车车箱,而是运货的有篷车,车上有男兵女兵,有次在车站,我们见军车一停下,女兵们跳下车就在车子下面小便了,男兵们也就站着小便。大便就困难了。
还有一次让我们挺心痛的,不知是那个县的一个南下干部(押运员),白天在我们车箱上聊天,到泰安车站已是黄昏,天已很黑,车站灯光又很暗,他准备回到自己的车箱去休息,下车时不小心,跌倒在站台下面,伤得很重,我们马上报告车站,但车不能停长久,只好让崇德县的一个同志留下陪同。
这次列车就我和平湖的一个同志从泰安押运到沈阳。我们完成交货手续后,特地从沈阳买票到泰安,到车站一问,车站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同志连夜送济南铁路医院,因跌伤很重,救治无效已经死亡,我们听了感到非常痛心。
原来我俩想,如果那同志没事,那么我们到泰安后,就一同到泰山上去玩玩,现在一听那同志死了,根本没有心思玩了,就直接买了车票回嘉兴。而崇德县陪同的那同志早已回嘉兴了。
现在让我回忆起来,虽然抗美援朝我没有去过前线,但我在后方也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
本文来自【嘉兴日报-嘉兴在线】,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