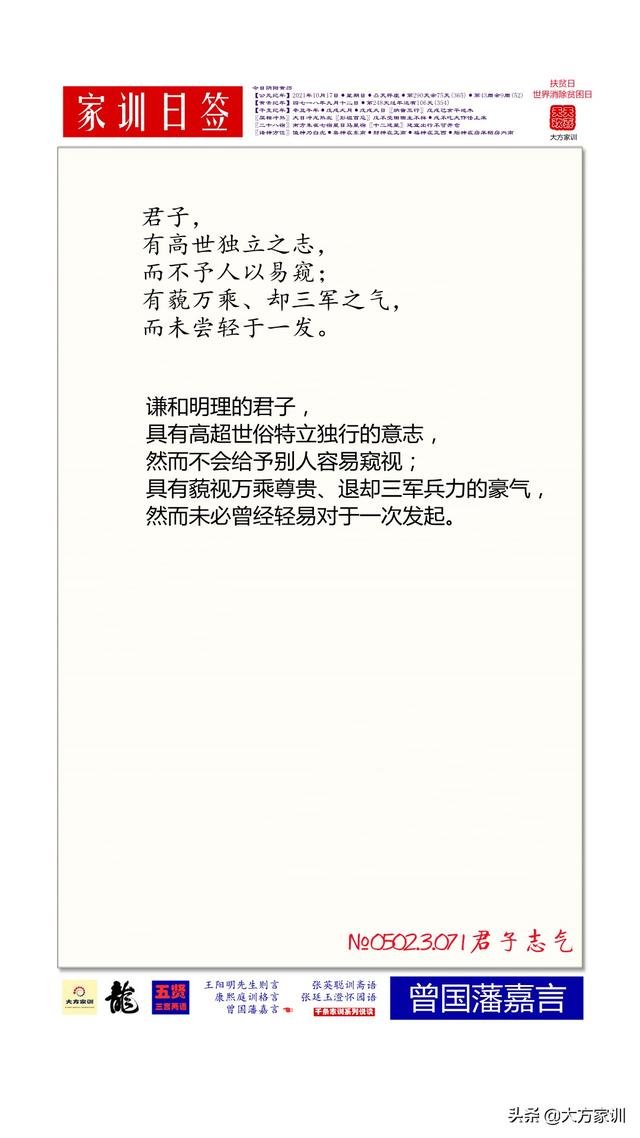杨立华:现代生活的哲学基础及其困境
某种程度上,在物质积累的高度上,我们是空前的。我们今天一个人所享受的物质丰盈度,是此前无数个时代的人都享受不到的。但是今天最糟糕的是,不管什么样阶层的人、他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他每一天的生活内容在本质上竟然并无区别。

EMBA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立华
人物简介
杨立华,浙江大学工学学士(1992年),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8年)。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
由于人类生存基本问题的高度一致,因此“现代生活”在本质上并不具有特殊意义。
在标榜现代性的过程中,我们开始面临诸多问题:生活无意义、感受力钝化、道德契约化、高度自我中心化。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在于现代数字理性所导致的虚无主义。
儒家倡导的礼乐文明,在理性中恢复神圣感,在敬畏中培养愉悦感,在主动性中积极关怀他者,重建对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及他人存在的感受力。
儒家通过“仁”培养人的自立精神与责任意识,成就“中庸”之德,进而有助于摆脱自我中心与虚无主义的困境,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
“虚构”出的“现代生活”
我们从“现代”这个词讲起。大家在用现代这个词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词是很奇怪的一个词。所谓的现代、当代、古代其实只是一个标划时间的词。我们说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本质上并无区别,但是这个词为什么现在有这么重要的地位?“现代生活”这个词,“现代”这个词,我们对这样一个词的标榜和凸显,标榜了怎样的一种自我理解、自我把握,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大家想想,人类有文明到现在,起码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的文明,我们知道传说中的就有五千年,可确定、有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的历史也至少有了三千年。大家想想,历史上的人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当代。但是曾经有过哪个时代的人,像二十世纪以来的人这样标榜自己生活在现代?
因此当我们用现代这个词来标榜我们当下生活,作为一个自我理解的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大家想过没有,这样的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家想想是连续的关系,还是断裂的关系?答案很清楚:当我们凸显和标榜我们现代生活的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在标榜我们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之间的断裂。
换言之,在“现代”这词中包含的对现代生活的自我理解是这样的:我们相信我们处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中,我们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生活样式、文明样式中的。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这样:在物质积累的高度上,我们是空前的。我们今天一个人所享受的物质丰盈度,是此前无数个时代的人都享受不到的。这个时间是正午的时间,古代这个时间有人会点灯吗?即便是帝王也都不会点灯。我们现在享受到的光亮,是我们古代人享受不到的;我们今天一天享受到的美食,可能是古代世界里的人很多年都享受不到的;我们今天生活所达到的方便的程度,是古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同时,这也是他们不愿意想象的——我们要注意,这个“不愿意想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换言之,在一个儒家思想的时代——比如在孔子的时代——他对所谓“便利”就有一个清晰的限度,过分方便的生活在孔子看来就是一个不正确或者是不健康的生活。我们今天,信息交流的方便程度、人与人关系之间的方便程度实在是空前的。在今天想被别人找不到是何其困难。在某种意义上,你想被别人找不到是一件非法的事情——你抄起一部电话就可以找到这个人。朋友之间交流越来越容易,但是越来越没有意思。
在我们生活中,不用比远,就比二十年前,我们也已经少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不再有突然有位老朋友来造访的喜悦,因为老朋友造访前一定会事先通知你。“有朋自远方来”,而且是“不速之客”的这种,肯定不会有了。还有一种寻访不遇沮丧我们也体会不到了。这里面包含的生活和心灵的味道,我们也不再有了。
这些都是事实,我们确实生活在古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说孔子有什么了不起,庄子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上过网吗?他们坐过汽车吗?既然他们连这样生活的皮毛都无法想象,那他们的思想和智慧对我们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之间的断裂是一种真实的理解的话,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当年鲁迅等先生要求我们做的事情那样,把中国古代扔到一边,所有的典籍用火烧掉算了。那些东西不仅不是我们的遗产,反而是我们的包袱。
但是现在问题到了这里,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断裂,究竟是一种真实的洞见,还是一种虚妄的幻想?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虚妄的幻境。我们以为我们是全新的人类,错了:生活的实质根本没有变;生活的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变,古往今来人们面对的问题仍然是今天在困扰着我们的问题。
大家想想,生老病死的问题变了吗?人的尊严的问题变了吗?道德生活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取消了吗?善良与邪恶之间的区分取消了吗?在所有这些问题仍延续着古代世界的基本问题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生活中?
既然生活的实质、本质、生活最基本的问题没有改变,那么古往今来那些圣贤大哲,他们在面临人生中的基本问题的时候,他们所运用的智慧和他们的洞见就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资源;而我们放弃它,就意味这让我们的生活离开了原本丰厚的土壤,活在一种无比单薄的生活中。
现代生活的基本问题:虚无主义
我们接着讲第二个问题:这种虚构是何时开始的,又是如何产生的?在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上,哲学信念上,这种虚构出现了呢?而且这种虚构怎么开始成为统治我们的,对自我生活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观念呢?答案很清楚:现代性的生活不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而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地点是欧洲。我们今天生活的基本逻辑,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建立起来的。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什么呢?尼采发过这样的感慨,晨祷已经被晨报所取代。这种深刻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看看晨祷和晨报的共同点,二者都是每天早上要发生的事情。不同点呢?晨祷是什么生活呢?是宗教生活的内容,而晨报是世俗生活,这是晨祷和晨报变化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晨祷的内容每天都是重复的东西。晨报呢,如果每天都是同样的东西,不出几天就要倒闭。换言之,朴素的、每天都在重复的生活,已经被充满了新奇的生活取代。
晨祷是宗教的生活。晨报是世俗的生活,内容是丰富的。而晨祷是一种单一的生活。什么样的精神能让我们专注于每天都重复的东西,这里面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敬畏。我们在每天进行晨报生活的时候,敬畏感消失了。这样一种变化,为我们现代生活的基本的面向提供了两个表述。第一个描述是,朴素的生活态度已经被对新奇的追求所取代,第二个是生活的均质化和彻底的世俗化。
彻底的世俗化大家都理解了,刚才我说的是生活的均质化。什么是生活的均质化?我觉得今天最糟糕的是,不管什么样阶层的人、他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他每一天的生活内容在本质上竟然并无区别。这实在太糟糕了。
我当然不能自诩我是知识精英,但是我毕竟是每天念书的一个人。当我认真反省自己生活时,我发现我和街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区别。我们见到朋友的时候也是请朋友吃饭,也是喝酒。喝酒之后也是在酒桌上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我们现在在酒桌上什么都说就是不说学问,喝酒之后竟然也都是到卡拉OK唱歌。
作为一个读书人你生活的优雅何在?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生活内容。生活的实质内容一样还不可怕,关键是人对生活想象力的趋同实在可怕。这是我说的现代性的重要的一个面向。刚才我提到的新奇和朴素之间的关系。每天不断重复的生活,在古代世界,人们愿意相信每天重复的生活就是生活的本质,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接受这一点。因为每天重复的生活就意味着乏味的生活,这样乏味的生活是不可忍受的。
前面说了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就是我说的均质化和世俗化。德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小布什政府中的基本政策、基本方向都是他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奠定的。他对现在的生活有一个感想,这是我见到的现代的西方哲学家对现代生活最为深刻的反省。
他说:“现代生活意味着人类在最低水准上的统一,生命的完全空虚、无聊的自我不朽学说。在这样的生活里,没有从容、没有专注、没有崇高,没有单薄,除了工作和休闲一无所有,没有个体也没有民族,只有孤独的一群。”这是他对现代性的一个描述。

图为美籍德裔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
现代性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一方面是物质的享受无比的丰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物质最大化的状态,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无比的空虚。为什么,一到国庆放大假,大家就纷纷花钱到祖国各地去看人?为什么呢?大家都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是没劲的,我就只好去旅游。
我劝我很多想去旅游的朋友,我说你别去了;就你这样的心态,你走到天边也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来吃喝拉撒而已——你没有感受精致愉悦生活的能力。你没有这样的感受力,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里都是乏味的,都是没有优雅感,都是不能感受到精致生活的这样一个人。
于是,我们把现代生活的问题揭示出来,揭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聊和空虚——除了工作与休闲一无所有。为什么说除了工作休闲一无所有?大家想,有工作和休闲生活还不够多吗?还不够。仅仅有工作和休闲,这样的工作和休闲都是无聊和空洞的,什么丢掉了?生活的意义丢掉了,工作的意义丢掉了。因此这是现代生活的第一个问题,意义的缺失。
第二,感受力的淡化。我们不再有那种精致敏锐的感受,同时也不再有朴素的感受。这是感受力的方面。
与这两者相关,第三个方面,是道德根基的缺失。我们不再相信有绝对不变的道德基础,有恒常不变的道德底线,也不再相信有确定无疑的道德标准。
第四个方面,自我中心主义。这些方面都全部关联到一起。所谓的自我中心主义就是说,我们首先相信所谓的意义都和自我有关,对自我有意义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第二,对自我有用、有利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第三,自我是衡量其他东西是非好坏的真正标准。这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观点。
所有这些编织在一块,得出的结论就是虚无主义。现代的生活当它展开到一定深度,展开到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深度的时候,我们发现它骨子里是一种虚无主义。这样一个虚无主义从哪来的?它的哲学根基是什么?它的最基本的哲学气质是什么?这时候我们还要回到十九世纪来思考。
虚无主义问题的哲学根基:数字理性
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样哲学气质的改变导致了这种对自我生活理解的变化?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十九世纪以来,人类陷入了理性乐观主义的情绪中。
十九世纪大家认为,随着愚昧迷信被驱除,这个世界就进入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理性对无知、对愚昧,以及由无知和愚昧引出的邪恶的关系,就如阳光之于黑暗,当太阳升起,阳光照耀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黑暗就被清除,人类就回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堂上,人类真正回到了一个上帝之国,这个上帝之国在地平线上实现。
十九世纪的想象是很有意思的,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把上帝之国挪到了人间,认为上帝之国在不久的人间就会在地平线上出现。
但是十九世纪理性乐观主义,到了二十世纪立刻受到了当头棒喝。十九世纪的人们都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人类将进入科学、发展、民主、进步的世纪。但实际呢?即使二十世纪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悲惨的世纪,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悲惨的之一。在这个世纪,战争的借口是前所未有的,战争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战争背后的理念也前所未有的。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战我们说是对法西斯主义的一次大战,但是那背后是有种族的问题。德国人最大的罪恶体现在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处理上。

图为二战纳粹德国在波兰组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变化。战争围绕着什么呢?从1950年前后,或者说在二战一结束(1945-1980年前后),是以什么为核心打仗?意识形态冲突——冷战。到了冷战结束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个短暂的人类的黄金期。那个时候我们都相信,人类将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就发现这如果不是骗人,就是在自欺或者既是骗人又是自欺。战争没有改变,战争在以更为现实的借口在发生。大家想想,现在的战争围绕什么?资源,经济,当然背后还有种族、文明、宗教。
先不要说二次大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卢旺达发生的种族仇杀,一个礼拜的时间用冷兵器杀掉了一百万人,这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在二十世纪出现。同时我们注意这样一个精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精神是人类不够理性的结果。错,这个结果恰恰是某种理性精神被强化的结果。
这种理性精神在什么地方体现最为明显呢?就是在二战德国人对犹太人的问题的处理上体现的最为明确。德国人对纳粹人的屠杀不是简单的屠杀,而是充满了一种理性精神的屠杀。德国法西斯和日本的法西斯是完全不一样的,德国的法西斯是一种严格的理性精神的体现。
二战后犹太人为什么会有幸存者?什么样的理念使得犹太人在德国人的那样的政策下还会存在?答案是理性。因为犹太人是劳动力、是成本,在这个劳动力被消耗掉前,杀掉他们是理性的吗?当然不理性。第二,在杀掉犹太人之后,消耗过多的物资和财富,是理性的吗?不理性。所以不应该用枪来杀,而应该用毒气。犹太人死了以后,牙齿上的金假牙都要被剥下来,甚至有的犹太人的皮肤被用来做灯罩,有的人的头发被用来做地毯。这是二十世纪最可怕的东西,是一种极端的理性统治世界的结果,也就是说理性之光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光耀。
在这样一个“理性之光”之下,我们进一步地探讨,难道理性错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理性吗?不对,我们没有说不应该理性。我在这里丝毫没有任何一点反理性的意思,我不是一个反理性者。
我只是讲,作为现代性的思考基础的这个“理性精神”错了。这是一种理性的独特的样式,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理性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数字理性。这种数字理性就意味这是一种数字的中心主义或者是数学中心主义的理性。这个衡量一切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什么的标准呢?是量还是质的标准呢?
是量的标准。当量成为最重要的标准,质重要吗?质不重要,甚至质已经完全不是标准了。大家一定说,你说得不对,我们这些搞企业的哪个不关注质,每个人都在关注质。但是我们关注是什么样的质?我们所关注的质的标准都是可量化的质。你所关注的质,是一定可以量化的,在这个意义上,量还是唯一的标准。
现在典型的艺术品的评价是放在拍卖的价格中去,大家在评价梵高和毕加索的画的时候,说梵高最高的画卖到了7千万,毕加索《拿烟斗的男孩》卖到了1亿3千万美金,但是你把毕加索的画和梵高的画拿到一起看看,梵高色彩的运用是直接穿透灵魂的。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看到连艺术品这样的东西都已经被还原成量了。
我们在评价艺术品的时候都说这无价之宝。它真的是无价的吗?不是。你真正的给出价格,人家还是卖的。真正的艺术品是不能被还原成数字标准的,这才叫无价之宝。连艺术品都变成了以量为单位的东西,还有什么呢?

图为梵·高画作《夜》
质和量的哲学范畴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这样一个数字理性会带来刚才我们说的问题:意义的缺失、道德根基的缺失。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缺失呢?我们顺着这个概念来分析。如果我们不做特别严格的对应的话,我们同时会把质和量的范畴,“质”对应为内容,而“量”对应为形式。
既然一切质的标准都已经被还原为量的内容,同时也就意味这生活的一切内容被已经抽象为纯的形式。换言之,生活的内容丢掉了,只有形式了。意义是生活的内容还是生活的形式呢?生活的内容。因此意义的缺失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想想,对生活的感受是生活的内容还是形式?也是生活的内容,那么这样一种数字理性的统治就必然会导致内容被简单的抽归为形式。这样一种数字理性的统治,和与这样数字理性统治相伴的意义的缺失、感受力的败坏,以及道德的契约化,以及自我中心主义都是一个必然的机会。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地方。
如果大家不理解这个,把质还原成量,就在日历上体现的特别的明显。我们今天的日历只是表明了一个时间的节奏。我们说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天,这是表明我们工作和休闲的生活的节奏,星期又被称之为礼拜。
礼拜,原本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是世俗生活还是宗教生活?是宗教。礼拜告诉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是工作的时间,到了礼拜六应该是去教堂做礼拜。但是今天还有宗教意义吗?今天这样一个时间,仅仅用来标划我刚才说的,工作与休闲。所以列奥·施特劳斯说的,除了工作和休闲一无所有。当然星期和礼拜是西方的日历。
我们中国古代的日历是皇历。我们皇历除了讲时间,还有什么内容?有非常多的内容。举一个例子。皇历可能会写今天“冲龙煞北”,大家想想这天有利于什么呢?有利于北方。煞的意思是有利。下面有一句话是说“大利北方”,就说你今天到北方办事是非常有利的。或者是皇历说今天不宜动土就没有人会翻自己家的墙根,或者是一翻开日历说今天诸事不宜,就回家睡觉。
而且在中国的古代,方位的内容也是各异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我举一个例子,金庸小说中给东邪、西毒起名,就用得特别好。西在五行中属金,东在五行中属木,木在季节上是春,因此它是春天。所以说东邪很好,春天意味着不确定的生命状态。所以东邪是什么样的人格形象呢?其实归根到底他是是慈悲的人,内心很柔软的一个人,没有刚毅的原则。但是西是属秋,秋对应着杀。所以说人家金庸的国学功夫高。
大家有没有算命呢?我们知道算命中有四柱。年、月、日、时叫四柱。每一时刻都有它独特的品质,你出生的那一刻的独特的品质就赋予了你一生的品质。年月日时都有四更,每一天都有自己的内容。
像甲子,按照五行应该甲是属木,子是属水,甲子这天是水生木,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假如这天上面这个是金,下面是木,这就不好了,因为金克木。如果这个是水,下面是火,今天做事能成功吗?不见得不能成功,但是今天是比较闹的,因为水火不容。就是这样一个方面,但是这些方面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讲到这些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意义的缺失、感受力的缺失,以及所谓道德的契约化、自我中心主义,几乎都是数字理性对生活的全面征服和统治的必然结果。我们做一个总结:所谓现代性生活,它的哲学基础无非是数字理性对生活的全面征服和统治。
在这样一个生活下,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把这样一个生活视为世界的黑夜。但是他的问题是,他不知道我们正处在这个黑夜的哪个阶段:是黑夜刚刚开始,还是黎明即将到来,这是海德格尔唯一疑惑的东西。但是,在黑夜这个判断上是勿庸置疑的。

图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这是我们对现代生活哲学基础以及哲学困境的揭示。现在的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是我们生活的实质呢?我们已经把它归结为刚才那几点,现在我们说是三点:
第一个是生活意义的缺失。这样一种意义缺失的生活,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就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正因为这种轻,生活变得无比的空洞和乏味。
第二点是感受力的倒错,使得我们不再感受到生活中平静的愉悦和幸福,我们不再有对生活平静细腻的感受。
第三是自我中心主义。
来源:通识联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