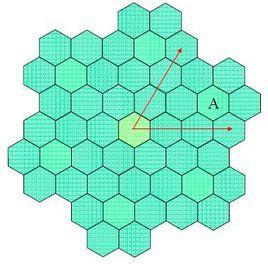央金今天在家里办公。
和平常一样的时间醒过来,庆幸免去挤车之苦,又痛恨不能再睡回去。刷够了微信微博,起床,打算踏踏实实吃个早饭。
阳台上晒满了衣服,还是先摘下来叠好。然后把床、沙发铺得平平整整。散落在各处的书一本一本收回书架,按高矮厚薄排好。
加水,放咖啡豆,按下开关,豆子咔嗒咔嗒转动,把门外的牛奶拿进来,打了细细的奶泡,旋转倒下,咖啡杯里浮起一片油脂,搅拌好,然后清理咖啡机水槽,咖啡渣盒。
哦,还要清理一下地板,吸尘器的声音确实有点大,关掉它以后,耳朵仍然嗡嗡了好一会儿。
抬头看一下时钟,快九点了,平常这个时候,央金已经下了地铁,正疾步如飞奔向公司。
吐司炉咔嗒一声,金黄的面包片跳出来。央金拿出白色平底盘,把面包放上去,端到餐桌上,放在咖啡旁边,说:
今天来不及了,只有面包啦!
九点钟,央金把电脑放到餐桌上,像在公司一样,一边吃饭一边开始工作。
咖啡有点苦,而央金有些发呆。独自在家的日子,总是难免想起什么。
每天早上起来,央金都是这样一通忙。手里拿着衣服,书,水杯,包,脚下匆匆地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像电影快放一样,零乱一晚的房间瞬间整洁了。待到再不出发就一定会迟到的那一刻,才去洗脸换衣服。
罗布从一睁开眼,到出门,只发出一次声音:打火机咔嗒一声,点上一只烟,然后吐烟圈儿玩。吐啊吐啊,吐到央金把早餐放到桌上,就会起床。
央金说:
今天是面包,煎蛋,牛奶呀。
今天是小米粥,花生,馒头干呀。
今天是油条,豆腐脑呀。
吃完了早饭,央金和罗布一起洗漱换衣,用一样长的时间。央金抹一层面霜,扎个马尾就出门。
罗布一边走,一边揪央金的马尾,发梢在手指里缠来缠去。有时候他把脸凑到央金的头发上,蹭来蹭去。通常这时候罗布才开口说一天里第一句话:香。
两站地铁以后,央金和罗布分开,去各自的公司。傍晚,又各自回到家。罗布总是回来得晚一些。然后一起吃饭。
央金发现自己走神了很久,心思重新回到电脑前,用很快的速度处理了十二封邮件,整理了四篇文章。
没有什么特别急的工作了。央金很久没想起罗布了,今天,她急着要好好回忆一下。
接近正午,没有阳光。央金端着已经凉掉的咖啡,坐到靠窗的一侧。早晨叠好的衣服放在沙发上,还没收进衣柜。最上面是一条牛仔裤。
央金系着围裙,削土豆,排骨八分熟的时候,就可以把土豆放进去了。
这时候,罗布推门而入,像猴子一样扑过来,从后面抱住央金。发现碍了做饭,便把两只手揣在央金仔裤的后兜里。央金走到冰箱旁,跟到冰箱旁。央金走到水池旁,跟到水池旁。央金抬手打开上面的橱柜,够不着调料罐,罗布不情愿地伸手拿下罐子,然后迅速将手放回央金的裤兜。罗布把下巴搁在央金的肩上,把空气呼在央金的脖子上。
央金把叠好的牛仔裤打开, 把手揣进后面的裤兜。
揣不进去。试了几次,还是揣不进去。央金把裤子正正反反看了几遍,有点心慌。它的口袋很小,小到连央金的手都放不进去。央金忽地想起,前些天收拾了一些旧衣服,其中有好多条牛仔裤,和同事们一起捐了。那天,她笃定地把这条拿了出来,还抱在怀里揉了揉。
央金颓然地放下裤子,觉得嘴里泛酸,脑子嗡嗡作响。十年来独自走过的上班路,辗转不眠的漆黑夜晚,孤寂自语的清晨,都叠加在这一刻,排山倒海汹涌而来。
2006年4月16号周日,央金加班。
下午05:30离开公司回家,07:10进了小区。罗布从花坛那边跳了过来,冲到央金面前。他张开双臂把央金抱进怀里,气呼呼地说:这么晚啊!罗布出门没有带钥匙,坐在花坛边等了两个小时。
春末的那一天特别热,有很多人穿短袖,下班路上央金也脱掉了外套,焦躁地往家跑。罗布扑过来的时候,手里还拎着一个冰激淋。两个小时里他吃掉了六个快要融化的冰激淋,第四次,他只买了一个。
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分针指向的那个时刻,罗布气呼呼的样子,央金都记得一清二楚。
但是央金竟然记错了那条裤子,带着罗布温度的那条裤子,被捐掉了。
手机咔嗒咔嗒两声,有微信进来。
央金所有的微信联系人全部是免打扰,除了罗布。有信息来的时候,央金会用深呼吸按捺住马上打开的冲动。
然而通常的结果是,不知道谁又拉她进了新的群。
然而央金从不抑制新的期待。
这次,是罗布。
罗布说:我想出去晒个太阳,结果呀,布达拉宫广场全是人,怎么那么多人呀。
罗布说:幸好天还是那么蓝。
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意大利对法国。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那一刻,央金开心得跳起来。罗布喜欢齐达内,央金讨厌齐达内。
央金一心盼着意大利赢。终场哨响的时候,罗布发来短信大骂格罗索,央金输入了七十个“哈”字,又一个一个清除掉了。
期待已久的这场比赛开始的时候,两人已各自天涯。
五月的一晚,央金和罗布缩在沙发里一起看电影。很老的港片。
“星星在哪里都是很亮的,就看你有没有抬头去看它们”。
这句台词令央金窃笑,她侧头看着罗布,罗布不语。
刚才回家的路上,央金抬头:看,那颗星很亮。央金摇晃着罗布的手臂,希望他一起看。罗布用手指刮着央金的鼻子,嘲笑她,罗布说:西藏的星,才是星。
央金抬头望窗外的天,雾霭沉沉。当年她心底的暗自思忖如今看来多么可笑:哪里的星空不重要,重要的是身边是罗布。
央金又忽然想起,这些年来独自一人走的夜路上,她很少抬头寻找那颗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它不见了。
央金和罗布提前一个半小时到了车站。
罗布有七八个同行的伙伴,每个人,都有十几个人送行。每个来送行的人,都在胡乱地递着烟,罗布抽了好多支烟。
央金坐在罗布的大箱子上。
送行的人渐渐散去。罗布的双手环绕央金的肩头,下巴搁在央金的头上,膝盖顶着箱子,溜到站台这头,溜到站台那头。央金握住罗布的手指,放在鼻子旁闻啊闻啊。罗布抽烟很凶,手指和衣服却总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车轮转动,咔嚓咔嚓。
是想念西藏的星空了吗?
罗布六月离京回藏,九月结婚,第二年生子。
罗布一反在北京的混沌和沉寂,仿佛被追赶着,奔跑着做着这一件接一件的事情。
罗布厌恶拥挤,躲避热闹,如非上学,他可能从不会走出西藏。
他眷恋那里的山,湖,天,云,空气,家人。罗布说,小时候他会蜷在阳光里发一个下午的呆。罗布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会和妈妈一起掉眼泪呢。
罗布的朋友是一起出藏上学,一起踢球,一起同车回去的这些人,几年来不增不减。
罗布常常用一根手指从上到下刮央金的鼻子,一边刮一边说:去了西藏,脸就不会这么白了。
罗布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央金从不说话。央金想,我的妈妈也很爱掉眼泪呢。
央金摸摸心脏,做过手术的它,不能靠近高原。
咔嗒咔嗒。罗布又发来:央金?
罗布总是这样欲言又止,央金从前总是回答:哎,罗布!
于是罗布不再回复。
过去的这些年来,罗布发来了很多照片。新娘拉姆、球队、车队、白云、雪山、星空、蓝天、湖水、儿子嘎玛、湖水、湖水、湖水…
央金去过的最接近西藏的地方是雍和宫,央金分不清那些湖是纳木错,玛旁雍错,羊卓雍错,还是巴松错,拉昂错。
那些照片满满是罗布的新生活:湛蓝的湖边投射的身影,以前是两个,现在是两个大的,一个小的;高原红的脸辉映着雪白的牙齿;蜿蜒不见头尾的车队穿行在雪山脚下;球场上飞奔的朋友们,和踩着足球的大脚,……大脚仿佛踏在了央金的胸口,结结实实按捺住那里的痛。
央金忽地想起了什么,起身走到书架前,在角落里找到牛皮纸本子。
和罗布在一起的日子里,她如此热衷往这个本子上抄写很多首歌词,抄写很多段电影台词。
纸很厚,翻页的咔嗒声略显笨拙,那些依偎在一起看电影的夜晚,热气腾腾的早晨,买七张游戏卡的月初,吃泡面的月末,在指尖滑过。
时光停留在这一刻:
人们说当你遇上你的挚爱时,时间会暂停,真的是这样。但人们没有告诉你,当时针再度恢复转动,它会无比飞快,让人无法赶上。
——蒂姆波顿《大鱼》
天色已暗。央金拉上窗帘。
央金把完成的工作逐项记录进表格,关上电脑。
而回忆不能制表。一天下来,央金想起了一两个确定的日子,两三幕依稀的影像,剩下些细小的尘埃,随处飘荡着,拢不到一起,很沉很重的忧伤,无声无息跟着那条裤子走了,虽然它刚才回来,重重敲了一下门。
央金轻抚厚重的本子,拭去上面的灰尘,放回原位。
央金拿起手机。
把微信名字“央金”的“央”字,改回“小”,小金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
闪闪发光的小金认真地回复罗布:哎!
小金想出去走走了,打包了几件衣服,几本书。小金看看空空的化妆包,决定过几天去买一只口红,或者,两只。
小金下楼,走出小区,时近黄昏,雾悄悄弥散,路逐渐清晰。
去哪里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