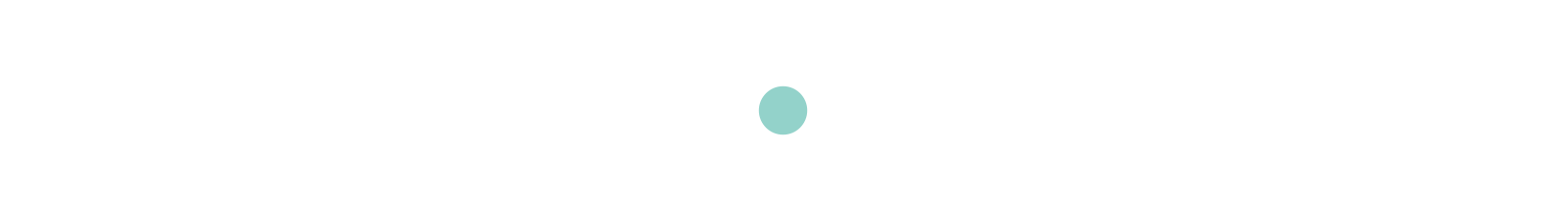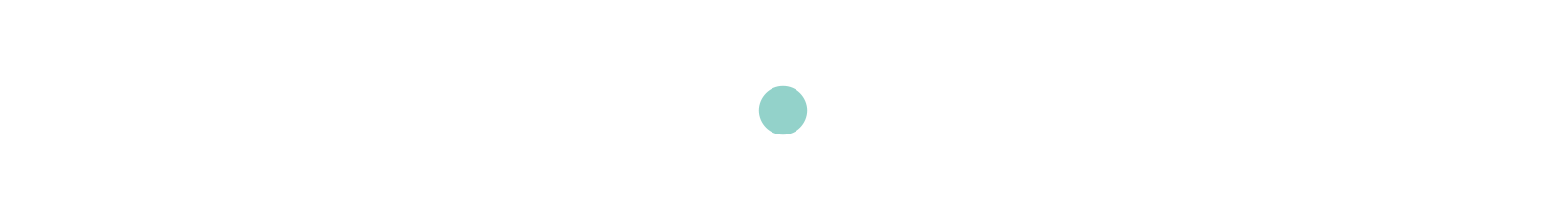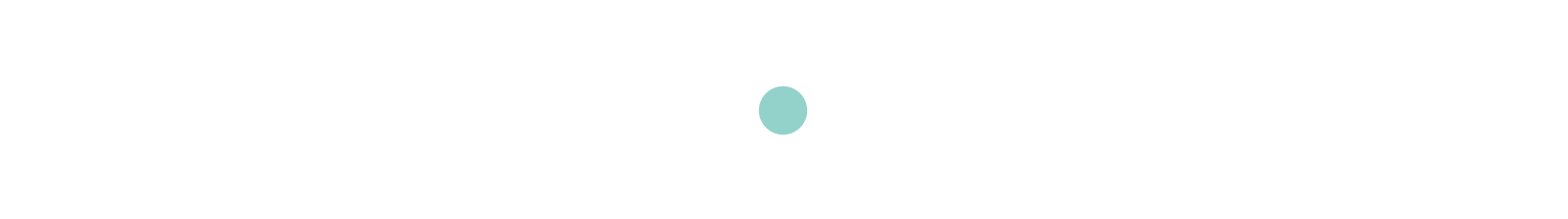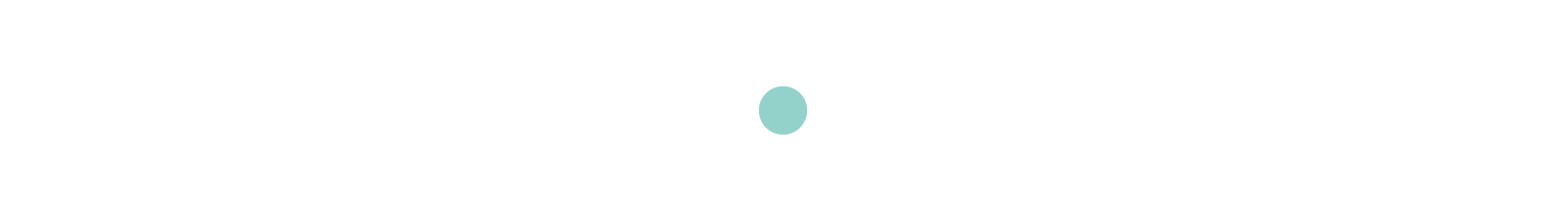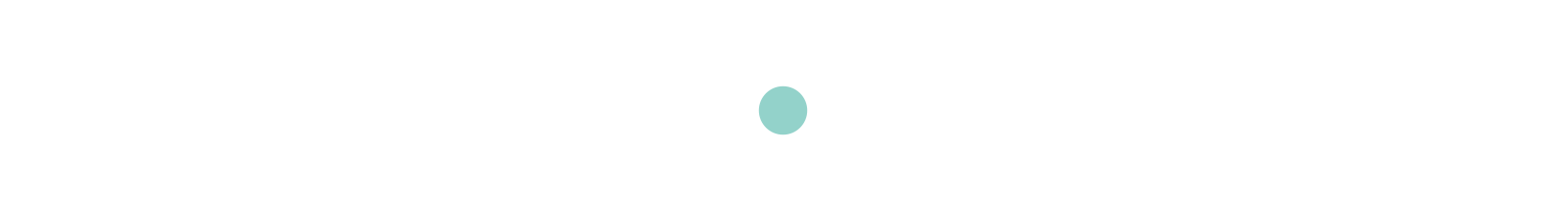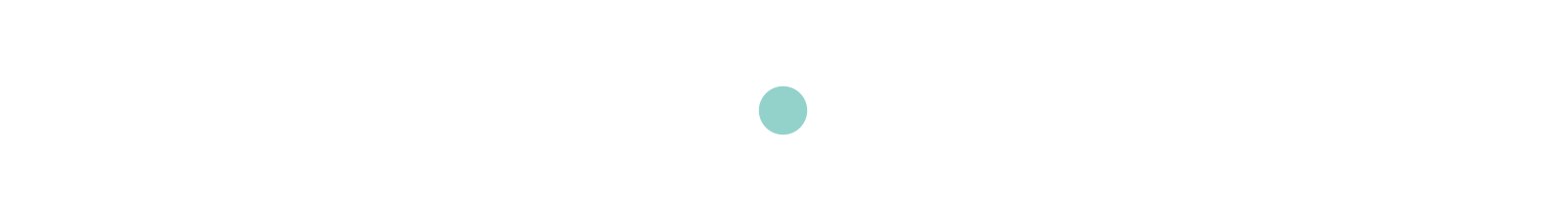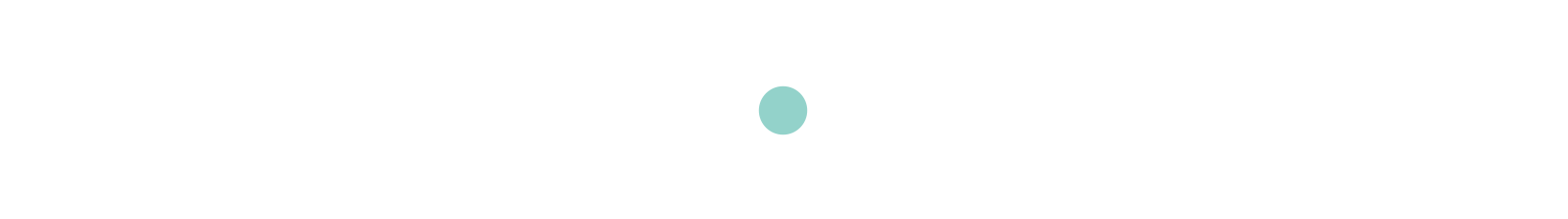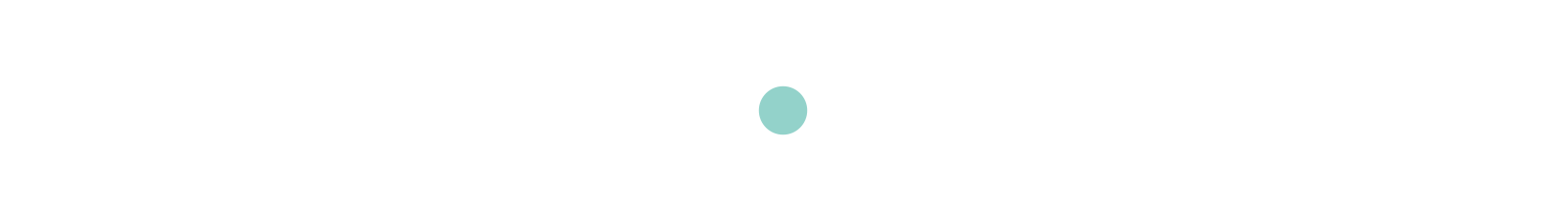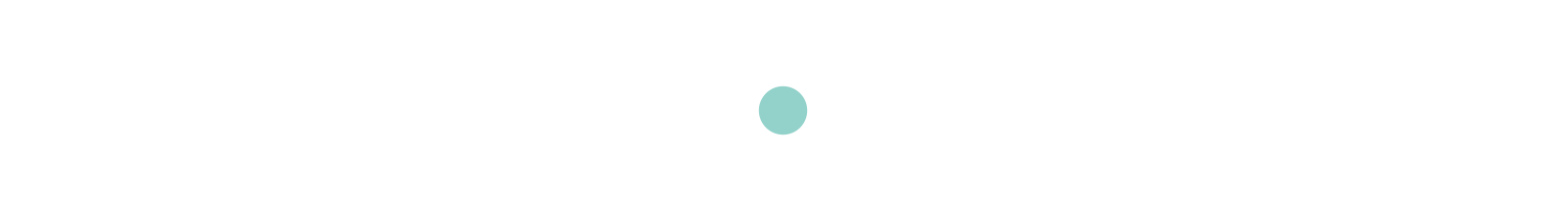
我一直以为,自己和马维的相识是基于偶然,直到我成为他的女人才知道,一切是他刻意安排的结果。
那年夏天,市电视台举办某化妆品形象大赛,系主任让我报名。他说:
你代表学校,取得名次将给学校带来荣誉。
于是,我去了。
初选结束后,四十人淘汰至二十人;复选的结果,二十人淘汰至十二人,我排第九。
对于决赛,我是抱着应付态度的。很明显,排在我前面的几个女孩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得多。
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大多集中在前四名身上,包括一个复选名次第六的女孩,她被认为是本届最有希望的黑马。
决赛的结果出乎所有人预料。当司仪宣布,本次大赛第二名获得者是米艾玲的时候,场内陡然安静。所有人大跌眼镜,包括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我戴上花冠,忐忑不安地站在台上,几乎不知该往哪里看。忽然,我的视线与台下评审席上的某个年轻男子相遇。
他随随便便地向后靠在椅子上,似笑非笑地瞧着我,目光不无得意,也不无欣赏。
那一刻我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他搞的鬼。
一周后,我已经躺在马维怀里。
他承认是他的暗中运作,影响了比赛的结果。
他还承认早就见过我,知道我在哪所大学。系里推荐我参加大赛,也是他的安排。
我说:
既然费了这么多心思,何不干脆好人做到家,让我当个冠军荣耀荣耀。
他淡然一笑说:
这你就不懂了,出出风头可以,真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上,容易把狼招来,我可没那么傻。
我逗他说:
你不就是狼么?
他说:
你抬举我了,充其量我是狼腿子,一个虚弱的前台人物。我的命不掌握在我手里,就像此刻你虽然在我怀里,但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数,是一个道理。
马维父母都是省直机关干部,家庭背景可谓优越。但这并没给马维的人生带来正面影响。
他大学没读完就辍学回家,拒绝了父亲托人安排的电视台工作,每天行踪神秘。
一年后,整个西区最大的洗浴会所开张营业,法人代表是马维,那年,他二十四岁。
此后五年,马维陆续开办了两家高档台球厅,一家高档舞厅,投资了一所孤儿学校,成为本市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我所在的师范学院就位于西区,地点与马维的台球厅相隔不远,是全市唯一的一所大学。
我以为像马维这样年轻有为的男人,身边定然不乏女人围绕,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我之前,他没认真交往过女友。问他原因,他说没时间。这显然是搪塞。
他第一次看见我是在台球厅,我和几个男生打斯诺克,他们输了,我是唯一的赢家。
他听见几个服务生议论我们打球,忽然对我产生了几分好奇,想知道一个擅长斯诺克的女孩长什么样子,于是悄悄来到我们那张桌附近。
马维说,见我的第一眼他就有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女孩注定要和他发生点什么。
他没有坐等那个“注定”的到来,恰逢那个化妆品形象大赛举办在即,他稍稍运作了一下,就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大赛结束,我回学校继续读书,生活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是多了一个校外男友——马维。
我们学校的位置偏近郊区,公交线路经过市老干部大学。马维在老干部大学后面胡同里有个四合院,他经常住在那里。
马维有个贴身跟班叫小义,几乎与他形影不离。
去的次数多了,我常在四合院见到一些神秘人物。他们身上散发出不同寻常的气息,带来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压迫感。
那种感觉就像黑暗中等待猎物上钩,或者说,他们本身就像一群极具危险性的猎物。
每次那些人来,马维都吩咐我待在卧室不要出去。
对面厢房屋门紧闭。他们抽烟喝茶,连着几个小时不出来,晚饭都是小义端进去。
一天深夜,他们聊着聊着,忽然吵了起来,气氛陡然紧张。
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仅捕捉到只言片语,似乎是因为某个项目主导权起了纷争。
其中有个人称五叔,每次来都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这会儿他嗓门最大。
他拍着桌子叫嚣,大不了把反贪局招来,管黑的白的,大家一起出局。
谁都没说话。过了会儿,谈话声继续,那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期间,我始终没听见马维的声音。
后半夜,那几个人走了。
马维回到卧室,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蹙着眉头。
我凑过去问他怎么了。
他看了我一眼,无言地搂住我。
记住,
他认真地说:
任何时候,无论听到外面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走出这道门。懂么?
我点点头。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他继续说:
这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过于聪明往往会让一个人死得更快。
一时间,马维眼里闪过一道寒光。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所以,
他继续说,搂着我的胳膊紧了紧:
必要时要学会装傻,而且装得不露痕迹,这是必学技。
我笑道我不聪明,本来就傻。
马维亲了我一下。
傻我也喜欢。
马维睡熟后,我去卫生间,发现拖鞋不知什么时候踢到床底去了。
我弯腰伸手去够。黑暗中,我赫然看见床底横梁用胶带固定着一把手枪。
它像个怪物,在黑暗中冷眼觑着我。我瘫坐在地上,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那夜之后,我开始回想这段时间经历和看到的事。
马维的手机铃声常在夜半忽然响起,他看上一眼,立即走出卧室,去对面厢房接听。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察看他的手机,发现通讯录里很多人没有存名字,均以某个字母或者数字代替,比如“1”,“m”等等。
四合院有两间正房,四间厢房。正房是书房和大会客室,四间厢房中,一间是我和马维的卧室,对面是小会客室,剩下两间靠着院门,住着马维的几个手下。
渐渐地,我感觉马维不像他说的只是个“前台人物”那么简单,这个猜测很快得到了验证。
一周后,那几个人又来了,却不见五叔。
我假装去卫生间,经过厢房门口刻意放慢脚步,听了听。
他们在讨论两家大型游乐场的收益分配方案,据我所知,那两家游乐场之前都是五叔的势力范围。
马维一个人在说话。他声音清晰,音量不大,却透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
一个小时后,马维领着那几个人走了。临走前,他吩咐小义三十分钟后去喜来登门口接他。
马维走后,我问小义,五叔怎么有日子不见。
小义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目光有些躲闪。
来不了了。
为什么?
死了。
我想起一周前马维目光中的逼人寒意,一颗心渐渐收紧。
我的男友是黑社会。我觉得这简直像演电影。
我想到离开。可是,马维会放我走么?就算他肯,我又真的走得出去,能割舍掉他么?
而且我不相信这个的结论。我想他或许只是涉黑,并不是真正的黑道人物,这是有区别的。
他每个月去孤儿学校一次,送些生活物资,和孩子们玩一会儿。那一刻的他特别开心,特别放松,完全是个大孩子,而不是一个二十九岁的男人。
他对我说,这世上有两种孤儿,一种失去了父母,另一种父母依然健在,但形同不在。相比之下,前者的伤痕容易治愈,后者却可能跟随一辈子。
那一刻,他眼里流露出痛楚。我望着他,隐隐感觉到,他说的是自己。
和马维在一起那么久,我从没见过他父母亲,也没听到他们之间的通话。
他倒是常和我说起过世的奶奶,提到她,他脸上浮现出孩子般天真的笑意。他脖子上有块玉,是奶奶的遗物。他戴了十年,从未离身。
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无论如何都难以让我和黑社会联想到一起。
可很多时候,想到床底那把枪,想到无端消失的五叔,小义躲闪的眼神,进进出出的神秘人物,我意识到,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那几个人又来了。他们沉着脸,直奔小会客室。
争吵很快爆发,马维的声音夹在其中,却没起到震慑作用。
他们吵了整个晚上,最激烈时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
夜里十一点多,他们走了,马维却没离开小客厅。他吩咐不许人打扰,直到天亮才回到卧室,搂着我睡了会儿。
那个周末,我刚进院子,就觉得不对劲儿。
门口厢房多了四五张陌生面孔,院落四周多了好几处摄像头。
马维问我来的路上有没发现行踪可疑的人,我摇摇头。
马维说:
一会儿吃完晚饭,我就派人送你回去,两个月之内,除非我派人去接你,你不要过来。
我说行。
吃过晚饭,马维定定地望着我,忽然改了主意。
明天早上走。
他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是那个手握球杆冷静沉着的斯诺克女孩。我的性格变得柔软而忧伤。这一切只因为马维。
我爱他。
第二天吃过早饭,马维吩咐小义备车,送我回学校。
小义伏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他脸色微微一变,说了声“知道了。”
那天我没回学校。接下来整整两周,我没能走出那个四合院的大门。
马维说:
这几天外面不安全,出去容易被跟踪,在学校没人保护,等局面稳定了你再走。
我担心地问:
你不会有事吧?
他笑笑说:
不会,得罪了几个人而已,我能摆平。
我说:
等一切都过去了,带我离开这里吧。
他注视着我:
你想去哪儿?
哪儿都行,
我说,
有你就行。再也不回来。
他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艾玲,你记住,人这辈子,遇到什么事都不能逃避。时至今日,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只是,
他叹了口气,
我后悔把你牵进来。
他沉思片刻,忽然转身喊了声:
小义!
小义闻声而至。
马维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小义听着,眼睛定定地望着我。
我这就去办。
说罢,他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两周十分平静。
马维很少出去,常常坐在天井的椅子里,望着天空发呆。看到我就招招手,让我坐到他旁边。
我从小就在这个天井里玩儿,没有谁比我更熟悉这片天空了。
他安详地说。
我这才知道,这个院子是马维童年时住过的地方。
那时觉得这里很宽,很大,从这边走到那边要走很久。慢慢长大才发现,它很小,从这边到那边不过几步路。被欺骗的感觉是,你会蔑视它,发誓让自己强大。终于有一天,你认为自己足够强大了,可回头一看,你想要的不过是头顶那片小小的天空,它一直在原地等你,你却再也回不去了。
马维摘下那块玉挂在我脖子上。
戴着它,奶奶会保佑你,
马维柔声说,
因为你是我喜欢的女人。
那夜我刚睡着,就听到一声细微的脆响,像小时候过年时玩的那种摔炮。
马维腾地起身下床,弯腰摸了什么东西别在后腰,迅速朝门口走去。
记住,别出来。
他回过头。
他穿着青色细格睡衣,站在门口,望着我大约两秒钟,然后果断推开门,消失了。
我听到院子里的脚步声,压低的说话声,枪栓滑上膛的咔哒声。
我看了眼床底,那支枪不见了。
我无从判断外面的形势,只感觉到处都是人,屋顶上也有,但始终无人讲话。
陆续有枪声响起,稀稀落落的,来自不同方向。终于有人说话时,已经是二十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
来的不都是警察,还有那几个人。他们带了不少人,计划包围四合院,逼迫马维出局,却与早就埋伏在附近的警察相遇,双方开火。马维随后加入,导致一场混战。
我被警察押送上车时,看见小义仰面倒在厢房门口,胸前一个枪眼,早没了气息。其他人有的死,有的和我一样被当场缉捕。
上车前,我的眼睛搜寻着马维,却始终没看见。这让我感到心安,觉得马维一定是跑了。
警车缓缓驶离之际,透过车窗,我忽然瞥见一个警察正蹲在院子外墙下,查看一具尸体。
他趴在地上。血从青色细格睡衣后背一点点渗出。手里的枪已被拿走,手掌却还保持握着的姿势。
在他的头上方,大约一米高的位置有一扇窗,里面是我的厢房。
他一定是想叮嘱我不要出去,或者只是想死得离我近一点儿。
我们之间只一墙之隔。他在死去,而我一无所知。
审讯时,我说自己是在校学生,什么都不知道。
警察问我马维那些人每天都干什么,我依旧说不知道。
总之什么都不知道。
我被关押了一周才被放出。
我无处可去,只得回学校。
我准备休学,我想,这是唯一的选择。
递交申请时,系主任对我说,过去的事和谁都不要讲,以后记住一件事:好好读书。
这让我感到意外,但很快明白了。
那天马维吩咐小义去办的大概就是这件事。
我望着系主任的一脸精明,想到三个月前他受马维委托,说服我参加形象大赛的情形,忽然感觉人这辈子真的十分滑稽可笑。
就这样,我又回到从前的日子。
那阵子,关于我的流言在校园内到处飞。
和一个黑社会混了大半年。
流过产,别看长得还凑合,残花败柳。
……
我恍若不闻,每天照常上课,独来独往。
随着时间的流逝,马维在我心中渐渐模糊,始终清晰的是他趴在墙根下,血从青色细格睡衣后背不断涌出,手掌微微张开,保持着握枪的姿势。
这一幕定格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夜里,我常常忽然醒来,怀疑一切其实并未发生过,只是一个梦。
直到我触碰到胸前那尊小小玉佛。
它柔润,温热,在黑暗中闪着莹莹的光,像蒙上了一层永远拭不净的泪。
---END---
作者:奴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