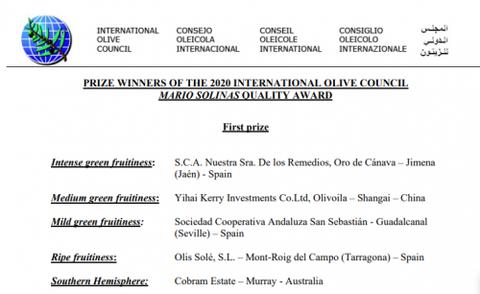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
主笔/陈赛
罗伯特·帕特南
帕特南说,比起美国版的封面,他更喜欢《我们的孩子》中文版的封面。美国的星条旗被设计成了一个跑道,终点是“成功”二字,但在起点处,不同的赛道被分成不同的起点——富人家的孩子站在靠前的位置,穷人家的孩子则远远落后。
对美国人来说,好的教育,好的职业,快乐的生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人生价值,这些都是关于“成功”最朴素的定义。
“美国人大体上并不相信完美的平等。我们可以接受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成功,因为每个人的天赋和后天付出的努力不同。所谓‘美国梦’,就是我们相信,无论终点如何,至少每个人都公平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获得成功。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选择正确的父母,站在正确的跑道上,成了一个人一生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选择。”
200多年前,美国建国,《独立宣言》上第一句话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如今的美国显然背道而驰。但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曾任克林顿、小布什、奥马巴三任总统的资深顾问,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独自打保龄》,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关系网的不断坍塌,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际疏离,个人沦为一个个原子式的存在,整个社会则渐渐如一盘散沙。此后,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不平等问题上。在美国,关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集中在成年人,而他希望把焦点放在孩子身上。因为他认为过去40年来,随着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最为凸显的就是教育公平问题。富裕和高知家庭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人际网络和社会视野,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在各个维度上都缺乏对等的机会。
“最近数十年来,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这是帕特南的研究团队以好几年的时间,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不同地区的107位年轻人,并结合大量社会统计数据和报告得出的结论。
他们的田野调查是从帕特南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开始的。在帕特南的青少年时代,作为一个美国中西部小镇,克林顿港虽然规模不大,种族构成也谈不上多元,但除此之外,无论从人口、经济到教育、社会、政治来看,都是一个可以代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微观缩影。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独自打保龄”之前的美国,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具体表现为:经济与教育高速发展,收入平等水平较高,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种族间通婚与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被打破;公民参与度高,社会凝聚力强,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
以他自己在克林顿港高中的同学为例,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几乎每个人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生活在自家拥有的房产里,邻里之间友爱团结。他们的人生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才华和进取心,而非他们的阶层。
《我们的孩子》
比如他的高中同学唐,出生于工人家庭,家境贫寒,但父母关系和睦。唐学业优秀,有运动天赋,父辈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时刻督促他上大学。为他提供人生指引的还有社区的教会,唐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牧师。
他的另一个同学弗兰克,出生于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被教育不可炫富。他学习资质平平,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海军,退役后在一家报纸做了25年的编辑,最后还因为人事变动被炒了鱿鱼。之后,他重回克林顿港,半退休地在家族企业里做事。家族财富虽然保护他不至于因为生活的碰壁而伤痕累累,但也绝非可以助他一飞冲天。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帕特南说,“无论出身如何,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体面的人生机遇。”
所以,一直以来,这位中西部小镇平民出身的哈佛教授都是“美国梦”的坚定信奉者。但是,半个世纪之后,当他的研究团队重返他的家乡时,却发现“曾经的克林顿港早已不知去处,随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经济繁荣、社区中无所不在的凝聚力,以及惠及所有家庭的平等机会”。
由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境况恶化,他们的家庭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都快速衰退,很多孩子早早辍学,打架吸毒,前途一片黯淡。与之相对,中上阶层的孩子则得到来自家庭、学校与社区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他们从一入学父母就存好了教育基金,他们被送去学习乐器、绘画等各种才艺,参加各种夏令营和旅游项目,参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及各种出国留学的计划。他们还得到来自学校、社区的长辈们的指导和支持。
“我的一生很顺利,事业成功,养育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也都很成功,学业有成,事业成功,经济上丰裕,都结婚了,都有孩子。我有7个孙辈。7个孙子孙女,要么已经,要么即将,在美国最好的大学读书,比如哈佛、普林斯顿。他们的假期经常在国外度过。去年夏天,他们各自分散在5个不同的大陆,一个在伦敦,一个在南非,一个在印度,一个在拉丁美洲,一个留在美国。他们非常的国际化,他们是好孩子,但他们是有特权的孩子。没有了特权,他们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我说的‘机会鸿沟’。在今天,出身优越的孩子,就像我的孙辈,他们的人生前景非常美好,他们会当工程师,会成为物理学家,会去探索宇宙,或者成为诗人,写出美好的诗句。但那些出身贫困的孩子,哪怕他们同样聪明,同等勤奋,也几乎不可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帕特南告诉我。
“这不公平,”他说,“这与美国的核心价值直接相悖,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经济上也极度低效。更糟糕的是,这个现象并非只发生在克林顿港,而是遍及整个美国。”
除了数据、图表之外,这本书用了大量的篇幅讲故事,关于富孩子、穷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的人生故事。“我希望借助这些故事的情感力量,让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更年轻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关于美国的理解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美国。”
比如一个叫斯特芬妮的黑人单亲母亲,靠着微薄的工资将4个子女养大,不但要时刻想着如何为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家,还要保护他们免受危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她形成了作风强硬的子女教育理念,她会毫不留情地抽打管教孩子,但至少将他们培养成了“为人正派、生活体面的人”。
俄勒冈本德镇的凯拉,生在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家庭,全家依靠父亲打零工勉强度日,凯拉有5个兄弟姐妹,要么同父异母,要么同母异父,属于典型的“拼盘家庭”。父母离异后,各自再婚,凯拉跟着父亲艰难度日。然而祸不单行,父亲中途又患重病,凯拉不得不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当初父母离异给青春期的凯拉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她的性格变得孤僻自闭,抑郁症状表现日趋明显……
最令帕特南震惊的是一个21岁的黑人男孩,名叫伊利亚,3岁时被父母抛弃,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祖父是个酒鬼,喝醉了就对祖母拳脚相加。他们住在新奥尔良的贫民区,家徒四壁,周围环境极度危险,各种绑架、强奸、谋杀都是家常便饭。他4岁时目睹一个小女孩骑着滑板车被一颗流弹击中,“下一刻我就看到她血流满面,子弹穿过她的前额、鼻子,这里还有这里(做手势),血从她嘴里涌出来,我吓蒙了……”
伊利亚长到13岁时,从新奥尔良搬到了亚特兰大,为的是照顾母亲和她的新男友生下的孩子。后来一时意气,因为故意纵火入狱,被父亲保释出来后又被一顿毒打,打到不省人事。但他言语之间仍然对自己的父亲抱着温暖的感情。19岁高中毕业,他开始了吸毒和醉酒的生活,被母亲扫地出门。在尝试了各种谋生手段之后,最终在超市做起了打包杂货的生意。
“在经历了21年充满暴力、动荡不安的生活之后,伊利亚还能毫发无损地活到现在,甚至做到勉强的自给自足,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对我们这些中上阶层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无法想象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我之所以挑选这个故事,就是为了震惊我的读者们,‘看,看,请好好看看!’”
作为读者,我们尽可以怀疑作者选择案例是否过于极端,是否偏离典型,但那些关于美国贫富分化、阶级隔离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却不会骗人。帕特南说,他的书中引用了成百上千个定量研究,“从克林顿港到费城,从本德镇到亚特兰大再到橘子郡,家庭之间的经济悬殊是每一段故事的关键情节。每段故事各有不同,但不变的是令闻者伤心,甚至感觉到危机将至的伏线:下层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但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父母却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源”。
在书末题为《我们的孩子的故事》一篇附文中,作者这样写道:“我们在本书中讲述了许多穷孩子的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我们绝没有在样本上动手脚以扩大穷孩子的困境,如果说有的话,反而是我们实际上低估了生活在我们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的悲剧人生,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孤苦伶仃的孩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这本书取名叫《我们的孩子》吗?”他问。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克林顿港的居民们,无论身份和职业如何差别,都把社区里的所有孩子视为‘我们的孩子’。当我的父母说,‘该给我们的孩子建个游泳池了’,他们指的不是我和我姐姐,而是整个镇上的孩子。”
“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非常‘我们’的美国。但今天,这种‘我们’的意识已经全面枯萎,为孩子提供机会成了一家一户的私人责任。”
有没有逆转的可能?
“美国的早期历史,也曾经是一个极度‘我’的时代。从1900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才逐渐从一个极度‘我’的社会转变到一个非常‘我们’的社会。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就是想要研究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需要对别人的孩子负责,不仅仅是出于利他主义。如果我们不帮助这些穷孩子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整个国家会更糟糕。如果不投资别人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会更糟糕。GDP会更低,医疗成本会更高,刑事司法系统的成本会更高。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变成瑞典那种民主国家,而是说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美国价值:关心每个人的孩子。”
如何终结机会鸿沟?
——专访罗伯特·帕特南
三联生活周刊:《纽约时报》上有一篇评论指出,你的书就像为癌症患者开阿司匹林的药方。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帕特南:我们姑且以他的隐喻为框架吧。现在癌症已经能够治疗,但不是通过某个神奇的药方,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由成千上万种药物和治疗方法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代表只能有一个很大的解决方案。不断增长的机会鸿沟是一个大问题,但它有很多的源头,比如我认为源头之一是家庭结构的变化,稳定的家庭结构中长大的孩子与残缺的家庭结构里长大的孩子,人生前景是很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更好地帮助单亲妈妈,以便更好地照顾她的孩子,她们并不是邪恶的母亲,而是处境太过艰难。
第二个源头我认为是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比起半个世纪前,今天的中上阶层父母会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仅因为他们有能力和资源这么做,也因为他们更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以及潜能挖掘上。关于儿童的心智发育,科学界有两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是孩童在其成长初期所获得的能力是基础性的,这些能力越发达,他们今后的学习就越高效。这就是为什么《晚安,月亮》式的亲子阅读时光如此重要,也是为什么早期的恶性压力会给一个孩子的一生造成毁灭式影响的原因。第二个结论是智商和情商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孩子的成功,除了学业成绩之外,勇敢、敏锐、乐观、自控力、责任心等非认知性的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为人父母的规范已经表现出了一项普遍的阶级差异:高知父母致力于培养自主、独立、又具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要让子女自尊自强,有能力做出积极向上的选择;相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往往把目光投向纪律和服从,要求孩子严格遵守家长定下的各种规矩。我们可以批评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甚至谴责父母的错误决定,但我们怎么能让孩子为父母的过错负责任?
第三个源头是学校系统,现在的情况是富孩子上好学校,穷孩子上差学校。但这种学校教育的阶级隔离之所以形成,并非学校本身的师资、预算或者政策有什么不同,而是学生自身的社会经济背景所致,富孩子给学校带去资源,穷孩子则给学校带去无尽的麻烦和挑战。但是,学生、老师和资源的再分配要从何开始?
在第四、第五章里,我谈论的是邻里和社区关系,富人和富人住在一起,穷人和穷人住在一起。种族与宗教隔离不再有,但阶级之间的隔离却越来越严重。不同阶层之间的孩子一起上学,或者结婚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怎么解决最根本的问题——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鸿沟?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这些问题和对策有优先顺序吗?
帕特南:这取决于哪个领域的改革影响力最大,以及可行性如何。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一条法律,要求所有的孩子离开父母,在一个经济完全平等的环境里统一抚养,这种政策虽然会很强大,但副作用太大,不可能施行。在我看来,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普及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我指的是非常早期的,两三岁之前的教育。不是日常托管,而是真正优质的幼儿教育。
第二个大变化是税收政策,提高中上阶层的税收,用这些钱为贫困的孩子提供教育。这个政策会有很大的影响,但现在的特朗普政府恐怕不可能执行。
第三,重新开始职业教育。美国曾经有一支充满活力的职业教育体系,设置在校园内外,包括职业培训、学徒实习和员工训练,但过去数十年间,我们却不再把钱投到这些项目,原因之一就是“人人都要上大学”的准则成为新的信条。在今天的经济状况下,这种信条必须改变。
《我们的孩子》出版之后,我参加了一系列的研讨会,邀请了50个美国最顶级的研究员,他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性别、拥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我们共同探讨了到底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发布了一个报告叫《终结机会鸿沟》,这些就是我们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
当然,要在全国层面推行这些政策会非常困难,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没法合作。但我们可以在地区层面一个个展开,一个个解决问题,比如西雅图、波士顿、加州……这是我们美国人一直以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通过某个宏大的国家政策,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美国是一个更去中心化的政治系统,我们的力量也在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年美国媒体上有很多关于中产阶级育儿焦虑、过度养育的批判,但根据你在书中的描述,他们的焦虑和过度养育似乎都是有理由的?
帕特南:首先,这不是一本育儿书,而是关于如何帮助那些被落下的孩子。中上阶层的美国父母如何抚养他们的孩子,他们的方法也许有益,也许无效,我并不关心。美国社会有很多关于过度养育的问题,但我认为对孩子的漠视才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