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端七情”之辩始于孟子与告子之争,其争论之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作为“道德心理”的“四端”,以及“四端”与人的“一般心理”(所谓七情,如欲求、恐惧等)的关系。由此涉及两个议题:第一,“义”之内外之辩;第二,“不动心”之辩。
四端与义内/义外之争
告子持“义外”说,所谓“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告子之“仁内义外”依据的是传统之说,即“仁”关乎内在心理情感,而“义”为外在行为原则,这不只是牵涉“人性”“善恶”之辩,更关联于道德行为的“确保”基础问题。告子认为人性之趋向无有定向,譬如水之决于东西,这意味着“道德行为”所依持之“义”是外在的价值原则,故而道德行为不具必然性,只是“任意”的。对此,孟子站在“道德自律”的立场,坚持“义内”说。不过,“义内”之说并非儒家本有,实是孟子的一个新提法,因为在《论语》中,仁/义有分。孔子以“仁”导引“好恶”,偏于心理情感;以“义”辨“利”,实在于行为原则。心理情感固在“内”,而行为原则当在“外”,故孔子虽未尝有“仁内义表”(“仁内义外”)之明确表述,而其意不难推出。及至孟子,通过“义”之内在化,作为“德行”的“义”自身开出了“德性”之“义”。由此,孔子那里的仁/义内外有分、为仁/从义的不平衡,即转为孟子那里“义”自身的“潜能”(心理)与“实现”(行为)之关系。如此一来,“德行”的“必然”只在于“德性”之“扩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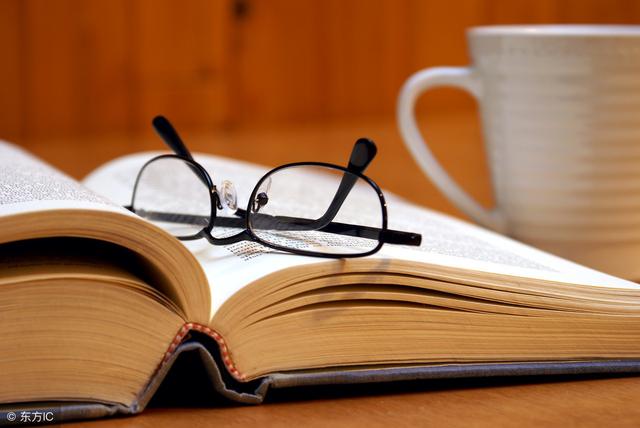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孟子何以区别了四端与四德。事实上,四德为“行为”原则意义上的“德”,是行为主体在现实行为中作出的“善”,故可理解为“德行”;而四端(四心)则是“心理”朝向意义上的“德”,是人心天赋本具之向善“倾向”,就此可称之为“德性”。借助四端/四德之关系形式,实也就将行为层次的“德行”与心理层次的“德性”连通起来。就四德的核心仁义而言,相对于孔子之仁内义外思想,孟子的“义内”说是对孔子思想内在问题的调停处理。
孟子通过“四端”说将“义”落实在“心理”层次而非“行为”层次,意义重大。事实上,四心同列,而仁、义二心至要,二者乃源于“不忍人之心”的次第表现,先有恻隐之心,次有羞恶之心,就此而论,仁、义之心无有轻重之分,但为前后之别。然而,由于孟子对“义内”的特别提倡,我们不难发现二心之中,“义”之端尤有特别价值。恻隐之心作为“仁之端”,只是提供了“道德意识”触动的情感基础——不忍人之心,继之而来的“义之端”才是“道德意识”的真正启动,因为其有“羞恶”之感的产生。“羞恶”之心即自觉的“应当”意识,这是心/耳目之官分工之结果。虽然耳目之好恶随声色而转,然“心”有自觉,有其“应当”规约下的“好恶”,如“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心”。心既悦“义”,如有不合“义”之好恶,则有“羞恶”感之生。显然,较诸“仁之端”之纯发乎自然、不待思虑,“义之端”之发似乎有一反思停顿,即所谓“念转”。如此,其实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并不冲突,因为“良知”“良能”义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均用以说明“仁”“义”之“发起”的迅疾与不待习得。但是,相对目睹“孺子入井”而“自动”即生“怵惕恻隐”之心,作为“义之端”,“羞恶之心”的升起虽然也是“迅疾”的,然其“自动”性程度稍弱,要经过一个十分微妙的“评价”过程,方有“羞恶”感的生起。此点差异正说明,作为“道德意识”的“启动”,“义之端”不同于人的“一般心理”。如果说,人的“一般心理”是基于自我欲求的“好恶之心”,那么,“义之端”(羞恶之心)则是对此“好恶之心”的“评价”之心。
勇与集义/义袭之分
从广义上讲,“义之端”虽然也是“欲”,属于人之“一般心理”,但其是“道德心理”或“反思”性的“欲求”,故不同于基于“耳目”之官的“欲”。由此问题,也就引出了“心志”(义)与“气”(勇)关系的辨析,此即孟子与告子关于“不动心”(不畏惧)的辩论。孟子自云“四十不动心”,意指面对外在权力诱惑与威压无有畏惧,故具有“勇”这一心理状态与品质。但孟子之“不动心”不同于告子的“不动心”,因为二者“不动心”的意涵与机制不同。如孟子所云,告子之“不动心”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在告子看来,“主体”若被他者之言所辱(“不得于言”),并不必反省“义”之是否在我,不扰乱己“心”;若“主体”之心不处于“定”之状态(“不得于心”),则亦不必通过“气发”而强作勇状。无论是何种情形,告子的基本原则是“定心不动”“不扰心”。可见,告子之“不动心”是在“心”与“勇”之间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不于“外在”言行上表现“勇”(作为“气”的“勇”),而直接以“不动心”为“勇”。换言之,告子完全放弃了“勇”作为“气”之行为表现,而只承认“内心”之“勇”。
对于告子的“不动心”之“勇”,孟子的态度似乎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从孟子自身陈述看,其表示认同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而否定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但这只是一种修辞之说,孟子实是根本否定告子的“不动心”之“勇”。因为告子不能坚持“直养其心”,故在心气关系上只是“力制其心”,使之不动。反之,孟子认为“夫志,气之帅”,强调“心志”对“气”(勇)的统摄、引导,故有“不动心”。这样,孟子的“不动心”之“勇”是“无有畏惧”之心理,而非静止的“不动心”,其必然有相应之外在“勇”的行为表现。依此,孟子强调养“浩然之气”,不使其“馁”,“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这里,孟子区别了集义/义袭,以前者为“义内”,后者为“义外”。“义外”故“气”之依“义”偶合而张,然因“义”与“心”不配合,一但有“行有不慊于心”,气“则馁矣”,“勇气”丧失,如此道德行为不能保证。相反,由于“集义”,“羞恶之心”得以涵养、扩充,故有“勇气”之“充沛”,确保道德行为的有效性。
早期儒家从心理学角度区分了人之“道德心理”(以“义”为根本的四端)与人之“一般心理”(七情),且以“以志帅气”为例指出了“四端”对于“七情”之“统帅”“引领”性。这一区分说明,在孟子那里,四端不可理解为后世理学理/气对立意义上的“理”,亦非是理/气对立意义上的“气”,而是心/气对立意义上的“心”。此“四端”之心别于“气”正在于,其为“天”所赋,与超越价值有一内在关联。事实上,尽管孟子将“义”内在化为四端之一,但他还是承认,有作为“心”之所“同然”对象的“理”“义”,所谓“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养之悦我口”。“四端”之“义”与所“欲求”之“义”是平行关系,并无高下或决定被决定关系。因为“四端”之“义”是主体天赋之“良知”“良能”,而所“欲求”之“义”是客观之“普遍原则”,二者均是在“超越价值”(天)层次意义上给出。毋宁说,“四端”之“义”与“理”之“义”是“天”(超越价值)在主、客两方面的落实。如是,孟子之“四端”(心)内在与“天”(超越价值)关联起来,立此天赋之“心”而开展存养功夫即是“大人”,反之则为“小人”。由此可推出,孟子之“四端”本身不可直接视为超越价值的“天”,但由于其是“天赋”,故而“内在”获得了指向超越价值的合法性。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忠伟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