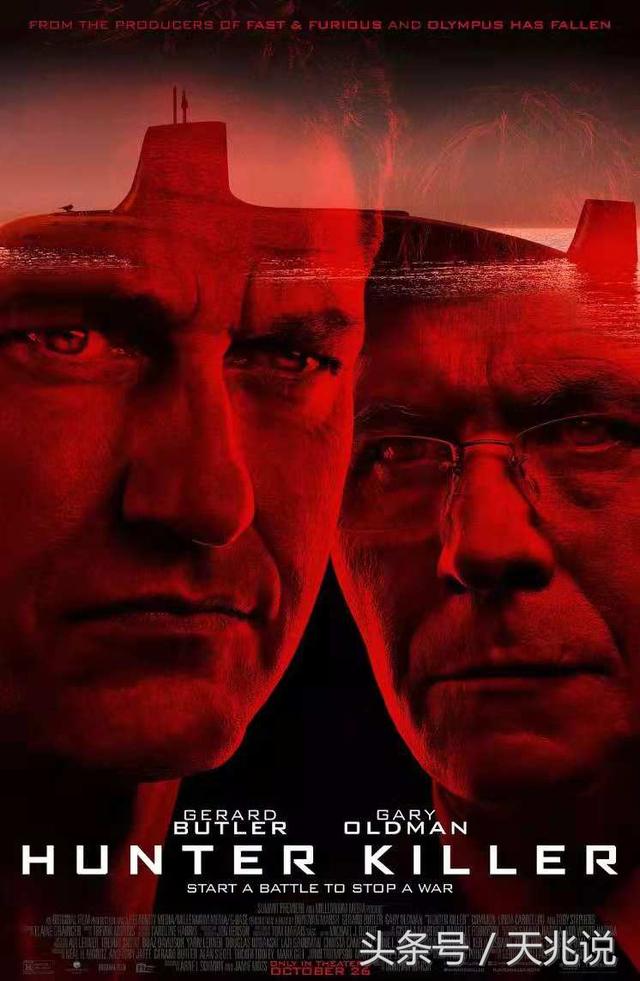算起来,老宅被拆了也快六个年头了。
在我的情感里,老宅,包含着许多意味,亲情。自在。快乐。厚重。传承。老宅即是老家。老宅是根,是家族的魂,是涵养血脉的厚土,是栖息记忆的院落。而今,老宅不在了,老家呢,仅存下记忆里的地理方位,活在岁月的深处了。
那时候,我还在临近的乡镇工作。大哥打电话说,老家的老宅,连同整个大口村,被开发区征用了,仅剩下一片残垣废墟。后来,每次回家,我总是忍不住,跑回去看一看,期待着遗留点什么,哪怕是蛛丝马迹。然而,脚下这片曾经僻静的村落,已生长成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恢宏气派的厂房车间。城市的屋檐下,夹杂着越来越多的外域乡音,车流,人流,物流,汹涌袭来,纷扰着红尘。不远处,新城的天际线错落起伏,现代,洋气,醒目,叫人激动,不安,又蠢蠢欲动。
或许,这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吧。我想,我在期待什么呢?立在废墟上,我像丢了魂似的,失落,无助,虚空,我似乎听到了内心孤单的回响。而今,我仿佛就是一叶浮萍,在光阴的长河里随处游荡。若干年后,谁还记得,这里,曾经是一个村落,这里,曾经盛开着一个人儿时那么多欢畅的光华。
我的老家大口村不大,百十来户人家,错落而聚。老宅在村西头。院子里有一棵泡桐树,很老了。巨大的树冠几乎覆盖了半个西房顶。春天,泡桐花开了,团团簇簇,香气蓊郁,很繁华了。我们吸溜着鼻涕,在院子里掼宝,伏在地上打溜溜弹,渴了,顾不上取水瓢,直接拿嘴贴着满满一水缸清水,咕隆咕隆几大口,然后,撮起衣袖抹一下嘴巴,锐叫着,呼一下又飞奔出去。我的母亲坐在堂屋门口摘菜,见了就笑骂,个小炮铳的,看把你欢的,喝冷水肚疼,长虫子。
在我的记忆里,老宅,总是喧哗的。我有三个姐姐。东院的小姑,还有村东的姑娘们,都喜欢来我们家串门,她们坐在泡桐树下织毛衣,纳鞋底,聊天。那时候,她们也像春天的泡桐花,正值盛期,花样年华,处在一生中最光华的岁月。这一幕,我印象深刻,是三月天,春光正好,明亮,跳荡,风也软和了。院子里,一群姑娘坐在一处,说着悄悄话。一朵泡桐花,落到一个人的辫子上,有人说她要摊上好事了。好事的意味,姑娘们自然都懂。那一张脸立时绯红了,娇嗔着,冷下来,几个人就吃吃地笑了。几只麻雀落下来,叽叽喳喳地,警觉,觅食。
很记得,那时候,我的大姐罹患脑膜炎,落下了病根,智力衰减,口齿不清。在大姐十六岁那年,母亲告诉她,你已经16岁了,别人问起你多大啦,你就要告诉人家,16了。我的大姐很兴奋,念叨着自己的岁数,“叶陆,叶陆”。我和三姐常学她的读音,叶陆,叶陆,然后,嬉皮笑脸,飞奔而去。大姐恼羞成怒,又追不上我们,便折回身缠住母亲,气急大哭。母亲哄着她,抓起笤帚,一把掷过来,也不怎么认真,个讨债鬼,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现在想起来,常常后悔。如今,我的大姐已为人祖母,精神也时好时坏,大不如从前。我们常去看她,偶尔,提及当年的往事,她一脸茫然,大姐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老宅前面,有一眼老井,水清澈,味微甜。很有些年头了。我记事起,老井就在。井有多深呢。我一直好奇,小心翼翼地趴在井檐口,朝里面打探,黑咕隆咚地,不见底,有丝丝凉气袭来。嗨!不知是谁突然从背后搡了我一下,把我的魂都骇跑了。此后,我对老井便多了一丝忌惮,每次经过老井边,都会下意识地朝旁边多绕几步。我一直恐高,我想,大约也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吧。
夏天到了,烈日煌煌地烤下来,树上的蝉鸣正欢,徐一阵,疾一阵,没玩没了的意思。人们下湖锄草前,拿西瓜放在水桶里,盛满井水,系在老井里冰镇。晌午收工回家,将井里的西瓜捞上来,放在面板上切开,红壤黑仔,一口咬下去,清凉,鲜甜,解渴,受用极了。多年以后,我还时常回味那样的味道,拿西瓜放进冰箱里冰镇,凉是凉的,比起那时候,甚至更冰更凉了,却再也体会不到,儿时的那份清甜了。
老井的前面,是菜地,大约七八分田,种了各种菜蔬,韭菜,青菜,辣椒,茄子,苕瓜,洋柿子,还有长豆角。垄垄畦畦,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缠藤绕架,有红有白,很热闹了。那时候,祖父的身体尚健朗,也是种菜的一把好手。通常是下傍晚,祖父便吆喝我的大哥和二哥给菜田浇水。那时候,我的两个哥哥正是青春年少,有使不完的劲,轮流从老井里提水,倒进小渠里。长长的小渠,浅浅的,连接着老井和菜地,清清的井水欢快地流进菜地。
我呢,蹲在小渠旁,看到一群蚂蚁惊慌失措的样子,我拿了一片树叶,挡住它们的去路,小东西们立时慌了阵脚。我猜想,在它们眼里,这小小的树叶,一定无异于一座高高的堤坝了,这浅浅的井水呢,简直就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了吧,我仔细打量着,忍不住咯咯笑出声。祖父正拿粪勺浇菜,讶异地朝这边看,然后,裂开豁牙子嘴巴,也笑了,这臭小鸠。
夕阳从树梢上掉下去了,暮色也浓稠起来,淡紫色的暑气升腾着,汇成薄薄的一层雾霭,把远处的田野,近处的树木都笼罩进去,缥缈而虚无。祖父裸露着上身,弓着腰,摘洋柿子。高高的洋柿架下,扒开茂密的绿叶,挂满了果实,一簇簇,一串串,生的青白,熟的深红,或浅黄。大姐和二姐端着瓷盆,跟在祖父的身后,将刚摘下的洋柿子,端到锅屋,我的祖母拿湿毛巾,将新鲜的洋柿子擦干净,轻轻地放到笆斗里。我蹲在祖母的身旁,看着她忙碌。这些洋柿子,爹爹明天要推到街上卖,换钱给胜子买糖果子吃,做新衣裳穿,好不好啊。我和祖母都高兴地笑了。
那时候,我的父亲在乡村小学教书,微薄的工资,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全凭了祖父侍弄的这片菜园子,贴补家用。一年四季,菜园子生长着春夏秋冬的季节性蔬菜,一季也没闲过。到了冬天,全部种上过寒菜。大口村的人,不叫过寒菜,叫它矮矮老,贴着地皮生长,形象,生动。雪地里,或者,厚厚的一层霜露下面,隐约透出一片盎然的深绿,充满生命的活力。那时候,菜地里还有地窖,我忘不掉。农村长大的人,怎么不熟悉地窖呢。
通常,地窖深约两米,长约六七米,盖上柴席子,拿土掩实了,再覆上稻草。地窖里存放着过冬的菜蔬,大白菜,青萝卜,还有山芋。山芋都是精挑细选,个头大,品相也好,那是留作来年的山芋种子。印象中,地窖也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地方。我藏进地窖里,一股子泥土的气息,蔬菜混杂的味道,扑面而来。不一会,我便听到了外面凌乱的碎步,急促,迟疑,蹑手蹑脚,又窃窃私语,咦,明明在这块的,人呢。是三姐和小梅。我紧张极了,屏了气息,一颗心怦怦乱跳,非要死死捂着,似乎,稍有不慎,直接就要蹦出来。
后来,我不大记得了。母亲找到我的时候,吓得半死,我躺在地窖里,脸色苍白,气息微弱。母亲一把将我拖拽了上来,搂进怀里,抹着泪,连声轻唤,乖啊,莫怕,莫怕。然后,从地上捏点土,撒在我的头上,这个动作,是驱邪赶恶的意思。其实,我原本是想出去的,怕三姐和小梅再找回来。我等啊等啊,一直听不到她们凌乱的碎步,隐约听到母亲在井挨边剁山芋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沉闷而单调。我实在是等得太久了,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母亲每次提起这件事,仍心有余悸,想想都后怕,个小炮铳的,怎么没跟你闷死的呢。
地窖风波后不久,老宅又突生变故。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大哥婚后约大半年时间,就搬进老宅前面的新瓦房,分家单过了。堂屋腾出后,东头房,我的父母住,西头房,三个姐姐住。我,二哥,还有祖父,住在老宅门前的防震舍里。一天深夜,忽听有人高喊,失火了,哪家失火了!尖利的呼喊声,打破夜阑的宁静,人们从睡梦中惊醒,顾不得穿鞋子,惊慌失措地跑出门外。我家的西屋,火光冲天,烟雾缭绕,夹杂着剧烈燃烧的声响,噼里啪啦。我迷迷糊糊地,死死守着窗沿,哇哇大哭,却不敢出来,有一种恍若世界末日的惊骇。多年以后,火灾的那一幕,我依然记得很清晰。
天色渐渐亮了,老宅的西屋,已是一片废墟,强烈的烟熏味,呛人的鼻子。我的祖父蹲在院子里,闷头吸着旱烟,神情呆滞。我的母亲抹着泪,嘴里嗫嚅道,这不——倒运嘛,坑得嘛。然后,拿铁叉翻看灾后的遗存,锅碗瓢盆,生产农具,一切都化为灰烬了。这时候,邻居们纷纷前来帮忙,轻声劝慰,长吁短叹了。我们小孩子围坐在一起,嘤嘤泣泣,一副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神态。这个时候,村东的小反子,小银子,三兆,竟然,他们竟然,笑嘻嘻地,翻找烧焦的蒜瓣吃。我悲愤交织,错了牙,冲着他们吼了一通脏骂,把这几个不识好歹的万恶棍子撵跑了。
后来,老宅的西屋重建了,由土墙茅舍,建成三间瓦房。再后来,堂屋也推倒重建了。那时候,我在北京当兵。父亲写信告诉我,新建的堂屋,是三间带廊阔的大瓦房,留你退伍后,讨房媳妇。我结婚的时候,就在老宅的新瓦房里,三间带廊阔的瓦房,敦实,宽阔,轩敞,也热闹。这一晃,过去多少年了,细细一想,那么清晰,真实,具象,像是不远的前几天。往事如昨,鲜活如初。
多年以后,我从外地回到村子,回到老宅,我的父亲母亲,都已老了,华发苍苍。我的父亲躺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看他喜爱的古书。我的母亲,坐在一旁,膝盖上托着簸箕,正费力地捡米里的小虫子。太阳明晃晃的照下来,一院子的树影。一只老母鸡,红着脸,咕咕叫着,骄傲而负气。
这样的画面,在老宅,我是再熟悉不过了,也熟视无睹了。然而,这一切,却再也回不来了。而今,脚下的这片废墟,是我的曾经的老宅吗?在这里,有我那么多欢畅的童年岁月,我的兄姊们,盛开的青春韶华,我的父亲和母亲,携着手,走过了他们在老宅里的苦乐年华。还有,那棵泡桐树,春日里,香气蓊郁的泡桐花,纷繁而落。而今,这一切,都远去了,再也寻觅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