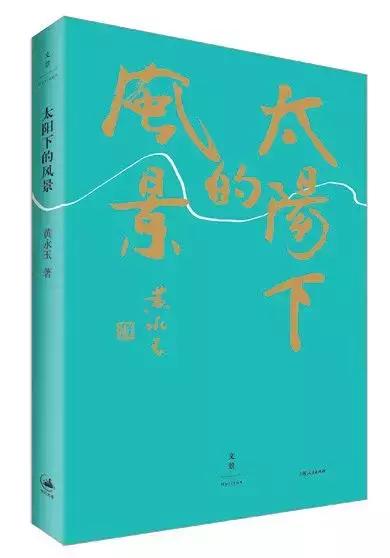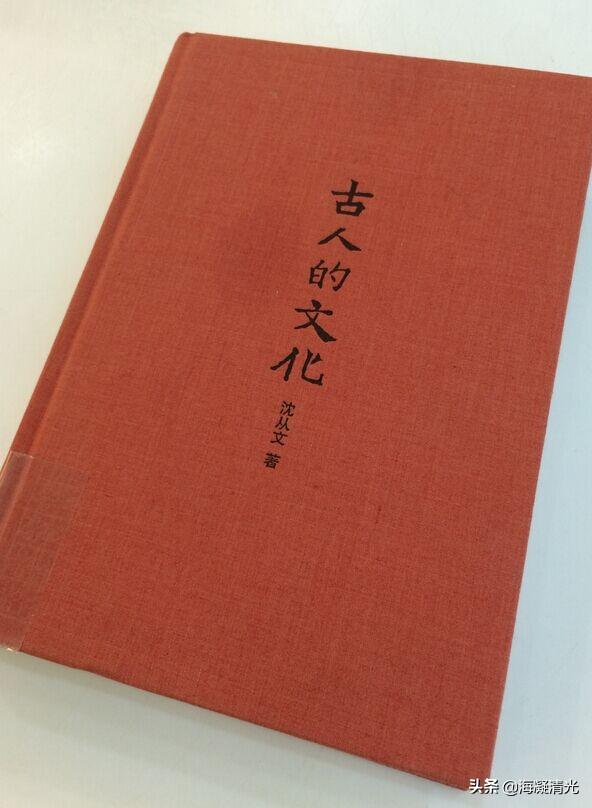
古人的文化
今天介绍沈从文先生一本书。
从文先生出身湘西凤凰,代表作《边城》不用多说了,笔端下翠翠的爱情故事流淌在多少人的心底。还很爱先生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中间记述的回乡沿途见闻不必多说,每篇开头的“三三”还能更甜腻一点吗?

写给夫人的湘行散记
但是,以一九四九年为节点,我们就会发现,从文先生文学上的创作基本停滞了,更严重的说,没有了。
究竟是为什么?很多介绍中会略过不提或者说的很含糊,一般都是用收到“空前政治压力和恐吓”,以至精神失常,并有过自杀举动,在此之后,一九四九年八月之后,彻底改业,转入北平历史博物馆,先后出版《陶瓷史》,《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一系列的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著作,这本《古人的文化》就是其中一些文章的节选。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我还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查了不少资料,大概情况如下:
一九九六年出版社的《从文家书》中有一篇散文,写作时间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名字叫《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
“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
这大抵是在压力中的自我呐喊,其中的深深孤独和无助透过文字我们也能感受的很清楚,这大概就是四九前后从文先生的状态。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
汪曾祺是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写过很多纪念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重要,就是《沈从文转业之谜》,他是从张兆和和沈虎雏(从文先生之子),处得到过第一手的信件的,所以很有些说服力,大概就是: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并且这篇文章在北京大学以大字壁报的方式贴了出来,直接导致了从文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
同时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不太适合再从事文字的相关工作: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这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的,因为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家,也不再想他们之前写东西哪样,没有再创作出可与自己以前文学成就相媲美的作品,名字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原因从文自己也总结过:
“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惟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如果用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有过极为准确的解释: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创作能力的衰竭,而是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当代文化规范不适应并且不能接受他们的精神劳动。”
就像给作家的笔戴上了难以挣脱的镣铐,如何再写《边城》,恐怕连《湘行散记》也写不成了。
就像汪曾祺对老师的遭遇做过的总结:
“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这固然是时代大潮中的必然,但·····
还是很难过,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