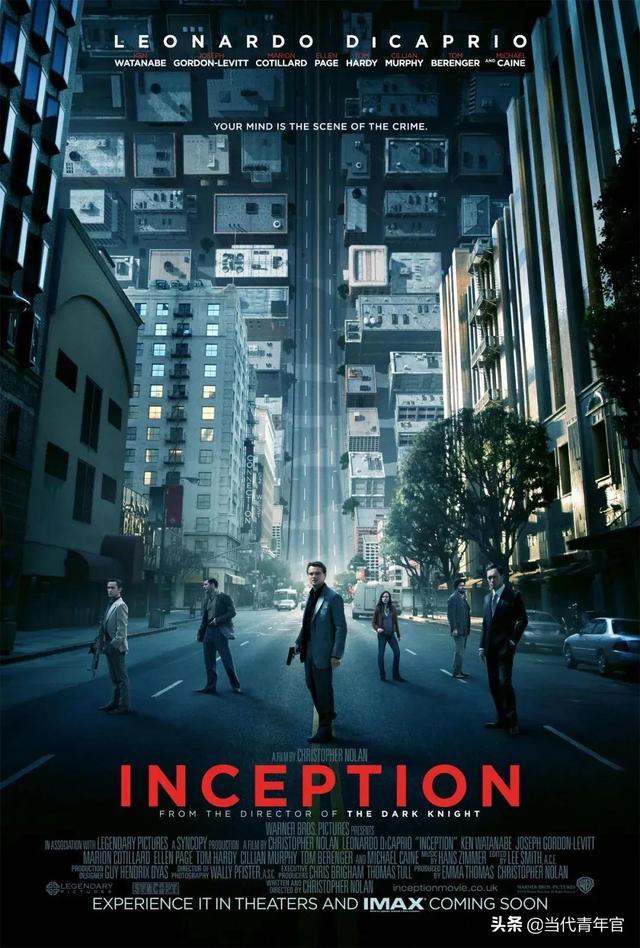第四篇论社会影响,经过导、摄、演几方面高超才艺的施展和离婚事件等引起的关注,一直是张艺谋居首;论专业圈评价,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陈凯歌声誉第一在走向市场的历程中,张艺谋继续保持了他无人能比的热度,度成为中国电影的象征,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张艺谋电影和陈凯歌电影对比?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张艺谋电影和陈凯歌电影对比
第四篇
论社会影响,经过导、摄、演几方面高超才艺的施展和离婚事件等引起的关注,一直是张艺谋居首;论专业圈评价,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陈凯歌声誉第一。在走向市场的历程中,张艺谋继续保持了他无人能比的热度,度成为中国电影的象征。
张艺谋来自最底层,受过重重挫折磨难,早消磨了那种高傲的心气;同时他的技艺远高于学识、思想,更像是一位高明的艺人,而不是一位思想家。考虑市场,迎合观众,在观念上他并不需要经历怎样痛苦的转变,只是在技艺和模式上,因为早年创作的强大惯性,不是略加调整就可驾轻就熟的。
早在1988年,《红高梁》为中国电影赢得空前的欢迎后才一年,张艺谋就开始了纯娱乐片的实践。这一年他导演的《代号“美洲豹”》上映。张艺谋后来不愿承认这部讲述劫机的影片是出自自己之手,该片叙事拙劣,置景虚假,毫不惊险,票房惨败。
张艺谋在商业片上的最早涉水还有1990年主演的港片《古今大战秦俑情》。有人把该片称为他和巩俐的“爱情宣言”,其实保持着“艺术家”惯性的张艺谋对这部香港商业片亳不在心,参演只是为了逃避婚变舆论,连后期配音都没有去。
1990年,张艺谋完成了《菊豆》。这部影片以偷情乱伦为主干剧情,以封闭的环境、扭曲的人物和主演巩俐的上身裸露镜头引起了海内外观众的莫大兴趣。两年后《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这部影片以环境对人的戕害为立意,主人公是迫于命运压力而无力应付的悲剧女性。张艺谋设计了一系列深宅大院内异于寻常的奇怪仪式和生活方式,大大激发了观众的猎奇心理。
这两部影片手法洗练,隐喻重重,在商业外衣之下,还是顽强表现出张艺谋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身子已向大众市场迎去,但他的脚还扎在高雅艺术之中。
在这市场化过程中,张艺谋还是得到了拍艺术片的机会。《秋菊打官司》的剧本放到香港银都机构高层的桌子上后,老板们认为此片票房无保证,获奖有希望;经研究,《活着》海外版海报,都决定为荣誉不惜赔本。该片以其纪实风格。而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巩俐在这部片子里发挥了她最高的表演水平,一个纯朴自尊的农村妇女跃然银幕。
1994年拍摄的《活着》被称为张艺谋最好的一部影片。在这部没有公映、但该看到的人都看到了的片子里,张艺谋向第三、四代导演的风格和手法回归,有浓浓的谢晋的韵味。它不再用造型,不再猎奇,不再炮制伪民俗,而是实实在在地讲述一个中国家庭的心酸往事,同时,影片又对悲剧内容巧妙消解,使感慨中又有了几分幽默
再经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有话好好说》,张艺谋一直在融入大众文化主流。1999年开始,张艺谋一连推出三部纪实风格的小成本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和《幸福时光》。号称“平民三部曲”的这三部影片水准一部不如一部,除了捧红了新星章子怡,影片生命感匮乏,平谈无味,张艺谋曾经辉煌的才华已略显疲态。要说收获,就是借助自身历年积累下的品牌,以最少的投入赢得了最大的就在张艺谋影片的市场号召力日益疲软之时,2002年导演的国产大片《英雄》利润
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武打片《英雄》是一部形式大于内容的作品,因为附和主流意识形态、歌颂封建帝王的“统一大业”而被学界诟病,李银河教授就直称该片立意“反动”。
一般观众能感觉到的是,在《英雄》恢弘的大场面之下,掩盖着一个单薄苍白的故事。第五代导演重视电影本体,习惯于淡化故事,淡化表演,注重视觉造型和表意功能,而在“讲故事”和塑造人物上捉襟见肘。当投入大众文化潮流,叙事上的“课”非补”不可。“过去我们开始没能力把故事。人物弄扎实,永远被镜头后方所迷惑…我们没有能力去完成扎实的人物和故事。玩电影语言仅仅是一条腿走路,我们现在就不能这么拍了,要两条腿走路,既有好故事好人物,又有好镜头,表现性的。张艺谋自己的这番话,十分切实。
就《英雄》来看,他制造“视觉盛宴”得心应手,但“把故事、人物弄扎实”还远未成功。《英雄》创造的票房纪录,只能说首先是营销上的成功:封锁剧情和拍摄消息,使市场产生“饥饿”;抛出“中国电影进军奥斯卡”的噱头,勾起人们的梦想和期待;从投资里僻出相当部分充作宣传经费,首次在央视黄金时间打出气势恢弘的广告……
再经过《十面埋伏》的历练,到2005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终于把握住了商业剧情片的要诀。《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确给了观众一个扎实的故事,他终于完成了由艺术家向大众文化产品生产者的转型。
然而,这个故事改编自曹禺的经典剧目《雷雨》。学习“讲故事”的张艺谋还是离不开文学的“拐棍”,他没有故事上的原创能力。对于摄影出身的他来说,文学创造力始终是他电影创作中的一块短板,他那些赢得高度评价的作品,无一不建立在莫言、刘恒、苏童、陈源斌、余华等优秀作家的小说作品的基础上。
从《红高粱》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跌跌撞撞完成了他从“精英艺术家到受欢迎的大众文化产品生产者的转型。在那“文化热”的时代,他是代表中国电影水准的大导演之一;到市场主导的阶段,他又是票房和利润的保证。艺术智慧和生存智慧兼备,使他 历20年而不倒。
相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的转型可供解读之处更多。他是“精神贵族”,一直高处精英艺术的云端。从小学起,他的作文就作为范文被老师念遍全校;从高材生云集的北京四中毕业后,陈凯歌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不得,遂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校期间,他整天谈论的都是“国家、民族、社会将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
陈凯歌曾经说;“有人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而我只能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还曾经有传言说,他拒绝接受35岁以下记者的采访。
一派大师气质的陈凯歌在精英艺术的象牙塔里修炼。拍《黄土地》时,他给饰演翠巧的演员说戏:“你肩上担的那不是水,你肩上担的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
这样一个人,要他在电影里讲故事来招徕观众,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他的同学田壮壮说,在1980年代,“叙事根本就没进入我们的视野”。在陈凯歌眼里,影像不是用来讲什么故事的,影像直接传达着导演的思想观念,体现着知识精英们对历史和文化的沉痛反思。陈凯歌的电影观,与中国整个1980年代的浓郁人文气息紧密相关。
然而环境变了。不考虑市场,任由导演进行艺术探索和文化沉思的时代一去不返。陈凯歌也要走出殿堂,面向市场了。
1991年拍摄的《边走边唱》开始与观众口味相结合;而标志着陈凯歌转型的作品—1993年出品的《霸王别姬》—获得空前成功,使他一举拿下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这是迄今中国大陆导演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高傲的陈凯歌最初看不上这个故事性极强、很“讨巧”的剧本。该片的制片人徐枫为了说服他接拍,花了200多个小时来游说。而片子剪完后,陈凯歌以一贯的风格告诉徐枫,全片“要2小时45分钟,少1分钟也不行!”徐枫通达地说:“那就2小时45分钟。”
才学在张艺谋之上,社会名声却总被当年为他当摄像师的张艺谋压着一头,难说陈凯歌不为此着急上火。高傲的风度下,他其实已向市场和环境全面妥协,《霸王别姬》一片,汇集了国粹京剧、“国际流行色”同性恋、“文革”、大明星巩俐和张国荣等既保证票房、又顺应西方人口味的四大元素—在暗地里,他把“成功”的条件已琢磨了个透。
接下来的《风月》和《荆轲刺秦王》,一个讲述和江南水乡一样曲折的江南情感故事,一个试图质疑历史巨轮中所谓“必然”带来的可耻鲜血。这两部不很成功的影片及2002年拍摄的《和你在一起》,表明他已离开《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和《边走边唱》时代的探索,而明显地和大众文化市场合流。
2005年年底,陈凯歌的大制作《无极》上映。这部号称中国电影史上最大投资的“巨片”却成为陈凯歌一个难以言说的伤痛。影片透着陈凯歌无法全部剥离的精英色彩,剧情将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的两个经典故事糅合在一起,产生面对历史和命运的空茫和无奈。在推广这部不惜血本的作品的过程中,骄傲的陈凯歌为把观众吸引到 影院而使尽浑身解数,常规手段之外,甚至不惜扯出前尘往事以制造新闻点
然而最惨重的打击还是到来了—票房一般倒在其次,一个叫胡戈的青年人制作了一部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网络短片,短片裁减《无极》画面拼贴组合,以煞有介事的“恶搞”让这部投资3亿多的影片顷刻间成为令人喷饭的笑料。因为《无极》的超高票价和观众看后感觉上的落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大快人心,时风行网络,并让“恶搞”这个词成为2006年最流行的词汇之一。
陈凯歌狂怒之下,怒斥胡戈:“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可胡戈已成网民拥戴的草根英雄,陈凯歌的怒骂激起了人们的更大反感,“做人不能太陈凯歌”反而在网上引起了共鸣。
身处大众文化市场的陈凯歌尽管也赢得过《霸王别姬》这样空前的成功,但他内心深处还是精英艺术家:他可以容忍对《无极》的严肃批评,但绝对受不了这样的“恶搞”:也就是说,他可以容忍别人说他差,但 绝不能容忍别人说他“好玩”。大众文化中,导 演本就是给人提供娱乐而换取利益的艺人;而陈凯歌心里,自己还是高踞云端的艺术家。在享有市场利益的时候,可以作一定妥协;而当市场喧闹解构了殿堂神圣,又流露出强烈的反感
从孤傲的陈凯歌的电影之路可以看出,些艺术家的底气不过如此,有对艺术的追求,又有对世俗利益的艳羡;内心有傲气,其支撑又不是那么强有力,在与世俗和时代的相处中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