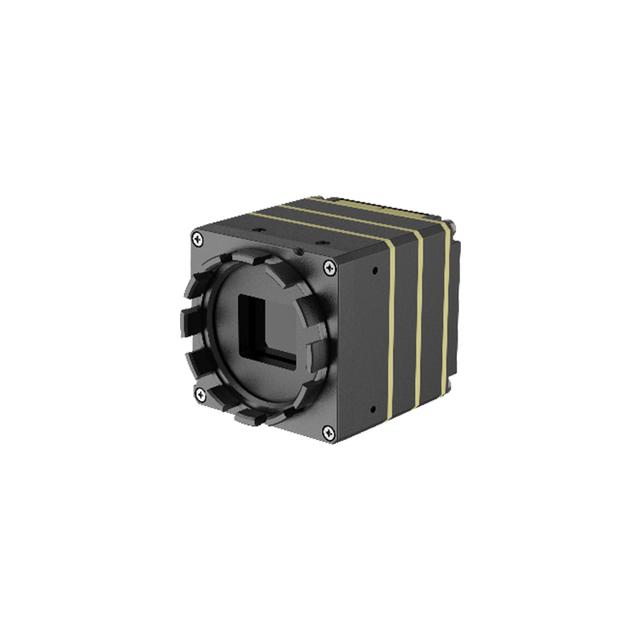苏轼《赤壁赋》中的“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到底是什么意思?
文 | 张聪
海德格尔在评论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考察》时说:虽然作者已经尽可能清楚地揭示出了历史与此在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但我们依旧可以从字里行间推知,“他所领会到的比他所昭示出来的更多”。(《存在与时间》第七十六节)。
“他所领会到的比他所昭示出来的更多。”——每次读苏轼的《赤壁赋》,我都会想起这句话来。尤其是文中的那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哲思?——这似乎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就能够读懂的,而对这句话的理解,恰又是我们深入解读《赤壁赋》全文的关键所在。
本文力图就学界常见的两种解读思路(第一种解读、第二种解读)进行讨论,并根据《东坡易传》中所体现的苏轼的哲学思想提出自己对于“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句话的思考(第三种解读)。

01 第一种解读
《赤壁赋》被选入了高中语文必修(上)。在《教师教学用书》中对这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给出了一个比较粗线条的解释:
“苏子承接前文客所说的‘江水’‘明月’,以二物继续作比,认为流去的水像这样不断地流去而永不复返,却并没有流去,意味永在流淌;月亮像那样时圆时缺,却终究没有增减的变化。如果从变化的一面看,那么天地间万事万物时刻在变动;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万物同我们一样都是永恒的。”
这个解释是否符合作者苏轼的本意?
我们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真正回应了“客”因个体生命的短暂与人生意义的虚幻而发出的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其次,我们还要看,这个解释是否能与苏轼的其他文字相互印证,符合作者一以贯之的人生哲学。
在《赤壁赋》中,“自其变者而观之”是容易理解的;而“自其不变者观之”,到底什么是不变的?按照《用书》的解释:江水虽然在不断流淌,但是“流淌”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变的。这当然并不错。把它类比到人类社会,就是说:虽然个体生命终将消逝,但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是不会变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顺应这种变化,只消“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就可以了。
这固然符合道家对待人生的态度——“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庄子·至乐》)——可是从这里怎么就推论出后面的那半句“物与我皆无尽也”了呢?“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能够称得上是一种“无尽”吗?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在物质层面上所获得的“不灭”与“无尽”又有什么意义呢?苏轼在《问渊明》一诗中说:“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大约可以算作对这种解读的颇具幽默感的回应吧。
至于《用书》把“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一句简单地解释为“月亮像那样时圆时缺,(作为一个整体)却终究没有增减的变化”,恐怕就更与作者的本意相悖了。且不说作为自然天体的月亮是不是“不变”的、“无尽”的,我们只将这个意思类比到人类社会,能够推演出一个什么道理呢?——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变”的、“无尽”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自己生命的消逝而感到悲伤,因为总还会有一些人不断新生,补充到这个社会中来,并维系着整个社会的存在。所谓“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是也。——我们试想,听完这样的解读,那位对个体生命的意义有着深切关怀的“客”是不是能够转悲为喜,并且还要“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每一个体存在的意义莫非只在于保存人类社会整体的持存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岂不是只具有一种生物学上的意义了吗?我看这样的解释未必能起到助“客”佐酒下饭的功效,反倒让人会徒增一种人生的虚无幻灭之感。
由此可见,《用书》中对于“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句话的理解——实际上也就是对《赤壁赋》全文主旨的理解——仅从字面上着眼,是似是而非,不够准确的。
秦观在《与傅彬老书》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而适卑之耳。”(《淮海集》卷十四)如果我们想深入探究《赤壁赋》中所蕴涵的真意,就不能只将目光停留在“至粗”的文字层面,而要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对苏轼“性命自得”之处做精微的思考。

02 第二种解读:
关于《赤壁赋》,在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认识,即认为“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哲学思想源出于东晋时期僧肇提出的“物不迁论”。据说这一观点最早是由南宋大儒朱熹提出来的,依据则是《朱子语类》中的一句“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第一,苏轼之说与僧肇的“物不迁论”其实无涉;第二,对于《朱子语类》中的这句话,我们不能做断章取义的理解,而是要将其放回到原文之中体味其语境意义。

我们先来看朱子“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这句话的完整语境:
或问:“东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代而卒莫消长也’,此只是老子‘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
(朱子)曰:“然。”
又问:“此语莫也无病?”
(朱子)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虚者如代’,如何不消长?既不往来、不消长,却是个甚底物事?这个道理,其来无尽,其往无穷,圣人但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说个不已,何尝说不消长、不往来?它本要说得来高远,却不知说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虚者如代’,便是这道理流行不已也。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祖宗四”)
完整地读过这段答问便不难理解朱子的本意。朱子认为《赤壁赋》中“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代,而卒莫消长也”(实际上也就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实际上与老子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同一意谓的。但也同时指出:苏轼的这两句话因为在语言表达上的欠妥——“本要说得来高远,却不知说得不活了”——故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苏轼这话哪里说的不妥(或者说是“不活”)呢?我以为就在于苏轼在《赤壁赋》中把“自其变者而观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放在同一层面上,相提并论,等量齐观。这实际上就是把“独立不改”的道体降低为了“周行不殆”的现象——仿佛只要“观”的法子一变,在现象世界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种什么“不消长”“不往来”的东西了。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请注意,朱子并没有说苏轼的思想就是僧肇的“物不迁论”,他说的是“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之说”,即苏轼的这种不妥、不活的言辞很容易与僧肇那种“即动即静”“即体即用”的说法相混淆。不得不说,对于苏轼的这一批评是非常准确也很有分寸的。
其实,只要我们对“物不迁论”的思想略有了解就能发现,僧肇“动静一如”的思想与苏轼《赤壁赋》中提出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是貌同而实异的。在“物不迁论”中虽然也提到了“言去不必去”“称住不必住”“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但僧肇论证的理路却决然不同于苏轼的“水月之喻”——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肇论校释·物不迁论》)
过去的事物在时间中变化或者消逝,这一点毫无疑问的。但是僧肇从这一现象中所得出的认识却迥异于常人——他认为这并非因为世界本身是“动而非静”的,恰恰相反,这一现象证明了过去与现在是并不相通的,过去的事物永远地保留在了过去,永远地停留在了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之中,并未来到现在,所以世界是“静而非动”的。
“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复而求今,今亦不往。(同上)
“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时的曹操永远停留在了建安十三年的那个深冬,既不会消逝,也不会来到当下;而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绝难穿越回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赤壁。由此可见,“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就是现在,二者彼此隔绝、不相往来。于是乎“既无往返之微联,有何物而可动乎?”
僧肇的这种认识与古希腊数学家芝诺的“飞矢不动”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既然射出去的箭在每一时刻、每一瞬间都静止在它固有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一个“动”字强加在它的身上。
这种哲学思想是不是《赤壁赋》中“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来源?如果是,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问题了——圆月自在圆时,缺月自在缺时,我们连盈、虚之间的内在联系都否定了,哪里还需要讨论月亮“有没有”消长的问题呢?消长变化这件事情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赤壁赋》中的句子就应该改作“盈虚者如彼,并非消长也”或是“盈虚者如彼,无所谓消长也”。
由此可见,简单认定“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是值得商榷的。而况僧肇“物不迁论”这种肯定过去的事物永存于过去,现在的事物永存于现在的思想本身是与佛教最基本的缘起性空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地道的“有见”。探赜妙门、深通佛理的苏轼是不是能够认同并接受这样的思想,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

03 第三种解读
那么,苏轼笔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中的“不变者”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略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在现象世界中是找不到“不变者”的。“不变”的只能是现象背后的某种知性的、抽象的东西,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它称作“理念”(idea,或译作“相”)——
人们之所以提出了关于理念的意见,是由于他们相信赫拉克利特的道理是真实的。一切可感事物都在不断地流变着,如若某种知识和思想果然存在,那在可感事物之外,就应该存在着某种不变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十三卷第四章)
作为一条具体的河流,长江是奔腾不息、逝者如斯的,但是作为理念的“长江”,或者说作为一种概念的“长江”是“未尝往也”的;作为一个具体天体,月亮是有阴晴圆缺、东升西落的,但作为理念的“月亮”却是“卒莫消长”的。
当然,苏轼所讲的“不变者”绝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理念”,长江和明月也可能仅仅是对“不变者”的一种比拟(《东坡易传》卷一:“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拟者也。”)。苏轼所真正关注的也不是具体事物背后的“不变者”,而是整个世界背后的具有本源性的“不变者”——“道”,并试图从这里出发去解答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该如何追寻生命意义的问题。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样一个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是怎样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转变成了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这是我们理解《赤壁赋》一文的关键所在。

在这里,我想引述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中针对宋明道学思想的一段高屋建瓴的阐述。读懂了这段文字,或许有助于我们站在宋代道学家们共通的思想脉络上来理解《赤壁赋》中所蕴涵的哲思——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通论道学”这一章中,冯友兰中指出:道学所要讨论的大多是关于“人”的问题,它的目的是要在人生的各个对立面中得到统一。在这当中,有两种基本的矛盾——“它们存在于宇宙的任何个体之中,包括人在内,不管是多么小或多么大”——一个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另一个则是殊相与共相之间的矛盾——
个体是一个殊相,它的性质就是寓于其中共相。所以,在每一个体中都有殊相与共相的矛盾。”(《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十九章第二节)
对待这两种矛盾,在中西哲学史上有三条路子:
第一条路是以柏拉图“理念论”为代表的“本体论的路子”,这条路子固然把“共相与殊相的矛盾说得很清楚”,但也“只是证明了这个矛盾比一般人所知道、所了解的更尖锐”。
第二条路是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的路子”,这条路子把“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讲清楚了,可是照他的讲法,这个矛盾比一般人了解的更尖锐”。按照康德的说法,在现相与本相之间,已经有了一道“闪光的光亮”,那就是人的道德行为。在道德行为中人可以体会到上帝存在、灵魂不灭和意志自由等属于本相的东西。“照逻辑的推论,应该说,在道德行为的积累中,人可能对于本相有完全的认识或经验。可是康德没有做这样的推论。他还是认为本相是彼岸世界,人性是此岸世界,彼岸世界是此岸世界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同上)
宋明的道学家与上面所谈到的西方哲学家们不同,既不是按照“本体论的路子”走下去的,也不是按照“认识论的路子”走下去的,而是另辟蹊径,走了一条“伦理学的路子”——
……他们(道学家)并不停止在本体论的路子上,并不停留在对于共相与殊相的分析上。他们所要做的是要得到一个这些对立面的统一,并且找着一个得到这个统一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道德行为的积累。就这个意义说,康德和道学家走的是一条路。但康德还没有说出道学家已经说出的话。
照道学家所说的,共相与殊相之间,一般与特殊之间,殊相并不是共相的摹本,而是共相的实现。实现也许是不完全的,但是如果没有殊相,共相就简直不存在。在这一点上,道学的各派并不一致。朱熹自己的思想也不一致。不过我认为这应该是道学的正确的结论。
照道学家的说法,人性是善的。他们所谓人性,指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等于人的本能。人性是一个逻辑的概念,不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人性包括有人的本能,但并不就是人的本能。照这个意义说,只能说人性是善的,不能有别的说法。
……道学家们认为,(感性的欲望)本身并不是恶的;其实恶者是随着这个欲望而来的自私。对于行为判断的标准,是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为己还是为他,如果是为己,他就是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如果是为他,就是道德的。道德的行为,意味着自私的克服;道德行为的积累,意味着克服的增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量变成为质变,自私完全被克服了。在质变中,共相和殊相的统一就实现了。随着殊相与共相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统一也跟着来了,这种统一道学家称之为“同天人”、“合内外”。
人一生都在殊相的有限范围之内生活,一旦从这个范围解放出来,他就感到解放和自由的乐(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由”)。这种解放自由,不是政治的,而是从“有限”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上帝存在”),从时间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永恒(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不死”)。这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道学所说的“至乐”。(同上)
理解了宋明道学家们这个共通的伦理学的大思路,再回到《赤壁赋》,很多问题就会感到豁然意解。在《赤壁赋》中,苏轼所要回答的同样是一个带有本体论意义的伦理学问题:在一个“哀吾生之须臾”的“人”的背后,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无尽的?作为个体,我们该如何从这有限的、殊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抵达那无限的、共相的、永恒的人生至乐之中?

苏轼对于“客”的回答,也正是这样一条打通殊相与共相,力求在共相中安放殊相的路子:在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背后,真正不变的、无尽的东西是恒常的天道与人性(苏轼认为“性”与“道”是一致的,《东坡易传》卷七:“敢问性与道之辨?曰:难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则声也;性之似,则闻也。有声而后有闻邪?有闻而后有声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性者,其所以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这才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中的“不变者”,它就像理念世界中的长江与明月一样,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一个人,只有在对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人性与天道的不断回归中才能寻找到那爿对抗虚无幻灭、安放人生意义的基石。
当然,这样的解读是否合乎苏轼本意,不能仅以冯友兰先生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论述作为依据,还需要从苏子本人的论著中去寻找印证。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黄州上文潞公书》)。《东坡易传》完稿于元丰三、四年间(略早于《赤壁赋》的创作),是苏轼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我们或可寻找到《赤壁赋》的思想根底。
在《易传》中,苏轼提出,世界具有一个统一的、不变的本源(“一”)。万物的形成以及种种生灭变化都是这个统一的、不变的本源的展开——
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人见其上下,直以为两矣,岂知其未尝不一邪!由是观之,世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于一而两于所在也,自两以往,有不可胜计者矣。(卷七)
是以圣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刚柔变化本出于一,而相摩相荡至于无穷之理。(卷七)
在《东坡书传》中,苏轼也同样提出变化的、不安的现象世界需要一个不变的、安稳的根基作为依托,而这个安稳的根基就是世界的源头“一”。“一”确保了事物能够如其所是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变而不失其常”,就像是长江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月亮的“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夫动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托焉。惟一者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万物资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资明焉。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昼夜之代谢,寒暑之往来,风雨之作止,未尝一日不变也。变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杀而不害其生,岂非所谓一者常存而不变故耶?(《尚书解》“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人也同样如是,在纷繁变化的生活中展现出变化的、各异的“情状”,但只要我们反推上去就会发现,在变化万千的“情状”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是——“性”。
贞,正也。方其变化,各之于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此所以为贞也。……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君子之至于是,用是为道,则去圣不远矣。(卷一)
天命之谓性,苏轼认为“性”是一种“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的东西,它本身并不为善,而是善的根基(“夫善,性之效也。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性”本身是一种不刻意的“无心”——
易简者,一之谓也。凡有心者,虽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则无信矣。夫无信者岂不难知、难从哉!乾坤唯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从之也不难。(卷七)
夫无心而一,一而信,则物莫不得尽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死者不怨,无怨无德,则圣人岂不备位于其中哉!
当一个人能够进入到这种“无心”的状态中,就能够把握住这个具有确定性(“信”)的、不变的“一”。也就是《赤壁赋》接下来所写的“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段话的的哲学根基。于是——“夫苟无蔽,则人固与天地相似也。”(卷七)人在回归本性的过程中,消融于无尽的宇宙,便可以在刹那间领会到了生命的永恒。自然,这种永恒并非肉体上的永恒,而是意义与价值上的永恒。
哈
余论
在撰写本文之余,我阅读了赵汀阳先生撰写的《历史·山水·渔樵》一书。书中对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山水意象”、“渔樵史观”的论述能够为我们深入理解《赤壁赋》一文——尤其是文中的“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一句的意蕴提供重要启示。作为教师,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论述,并以恰当的方式将它们传递给学生,必然有助于引导学生从对《赤壁赋》一篇文章的阅读延申到对一系列山水诗、游记文的阅读,甚至延伸到对一种文化现象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引述赵汀阳先生《历史·山水·渔樵》一书中的部分观点,权作余论。

在《历史·山水·渔樵》中,赵汀阳先生提出:中国的精神世界——不同于希腊的以哲学为本,古罗马的以政治-法律为本,犹太、印度、中古欧洲、伊斯兰地区的以宗教为本——是以历史为本的。或者说,历史是中国精神世界的根基。以历史为本,经史一体,就逐步形成了一种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历史观,“历史之道”与“历史之事”相互构成,使得我们的先民具有一种“形而上学化的历史哲学”或者说“历史化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与历史哲学的合体摆脱了封闭的语言游戏,转而向外寻求一种经验性的、历史性的证据。
在此就定义了一种以经验为有效范围的形而上学,或者说,一种无须先验原理的形而上学。其形而上问题不在于解释万物的本源,而在于解释万事的意义。进一步说,万物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万事有意义而有意义。存在本无意义,只是因为历史而具有意义。于是,历史成为形而上学问题的田野,而存在退居无可提问的暗处。(《历史·山水·渔樵》)
但这也同时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形而上学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关于无限性的问题。而历史的经验性却意味着时间和空间上的有限性。那么形而下的经验性应该如何回应形而上的超越性呢?也就是如何用有限性去回应无限性呢?赵汀阳先生指出:
要在历史中去理解无限性只有一个办法:以历史为本也因此以历史为限的精神世界必须在自身中发展出一种“有限内含无限”的方法论,即能够实现“以小见大”效果的方法论,以达到在有限性之中理解无限性。要达到“有限内含无限”的效果,历史就必须形成对内无限开放的空间,使得任何历史问题都可以通向无穷解释,并在无穷解释中产生无穷意义。……于是,历史空间虽然有限,但内部空间所能够容纳的意义却是无限的,因此能够以有限性内含无限性。……意义的无穷延伸性就能够给有限的历史撑开一个“对内无限开放”的意义空间,历史就具有无穷的意义潜力,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也就成为一个“内无穷”的世界而具有形而上的能量。(《历史·山水·渔樵》)
于是,“山水”这样一组意象就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之中。

“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赤壁之战,作为历史事件;曹操,作为历史人物,都已经永远地消逝在了时间之流里。但是赤壁之山仍在,长江之水仍在。它们成为了一种历史之道的象征,一种永恒的象征;成为了我们俯察历史事件时的超越性的坐标——
……以山水的形而上历史观去看待历史,是一种静观其变的态度和沧桑为道的维度。山水被看作道的化身。于是,以山水的尺度去观察历史就相当于以道的尺度去看待历史,即以万变而不变之法去观察世事之变化万端,在其中,超验的无限性似乎化为一种经验,虽无法定义却隐隐可感。
山水以其自然身份而拥有无穷的时间,因此能够以其不朽的尺度去旁观即生即灭的人事。王朝兴衰,世家成败,人才更替,财富聚散,红颜白发,功名得失,以青山度之,皆瞬间之事,所谓青山依旧在,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为变在,山水为永在,两者于对照之中尽显道的无限性与丰富性。
当历史感引进了道的尺度,即山水的尺度,历史感就转化为历史观,意气难平的历史感消失在心平气和的历史观之中,怀古的心情也就转化为论古的理性。(《历史·山水·渔樵》)
这种道的尺度,这种山水的尺度,这种超越性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意涵所在。我想,赵汀阳先生在这里的思考,或许恰是苏轼想说却没有说出的话——“他所领会到的比他所昭示出来的更多”

写到这里,本文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在结尾处我还想再饶舌几句:
正如黑格尔所言:“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行,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论,而是结论连同其形成过程。”(《精神现象学》序言)——我们要的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寻觅求索这个答案的整个过程。
而今,有多少文学经典仅仅像有待解剖的尸体那样横陈在我们的课堂上,等待我们将它们条分缕析为知识、要素、结构、方法,我们“不是在掌握事情,而永远处于事情之外;不是逗留在事情里并忘身于事情里,而是永远在追求别的什么东西,不是伴随着事情,现身于事情,而勿宁说是仅仅停留在渺小的自身中。” (同上)——这,也许才是我们通达《赤壁赋》这篇文章的真正障碍所在。

作者简介

张聪,小学老师。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董京尘 谢琰
责任编辑:刘桐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