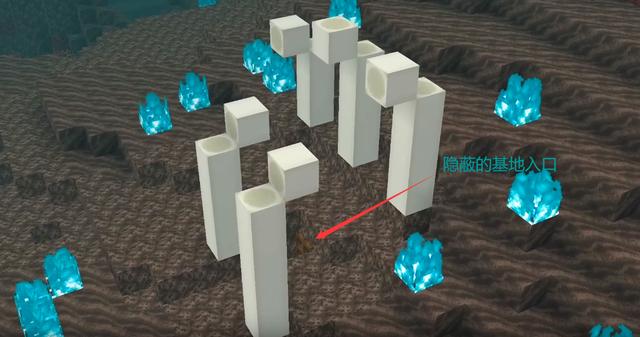1
我不断往自己身上喷洒古龙水,其实我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除了我自己,别人根本闻不到那股臭味。
那是死亡的气味。
还记得第一次闻到这种味道,是在张大爷身上。
张大爷就住在我家的隔壁,那一年我五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粒糖招呼我,我却捂着鼻子飞快地逃走了,因为他实在太臭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买了一束花,然后离开去了旅游,等你回来时,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换水,你闻见花瓶里……是的,就是那种植物从里到外被水泡到腐烂的恶臭。

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个晚上,张大爷的心脏病忽然发作,当时他的儿子和女友正在看电影,等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小学时,我在几个同学身上闻到了同样的气味。
臭味是忽然出现的,就在他们提议要去学校后面的小湖游泳的时候,那个湖看起来不大,但是很深,我听说有小孩曾经溺死在里面,于是我说不,并且很耐心地说出这个理由,他们对此的回应是一把将我推倒在地上,然后大声嘲笑我是胆小鬼,这个时候他们身上的臭气已经浓烈到让我不得不转过头了。
他们朝着湖的方向去了。
我飞奔回学校,办公室里只有数学老师还在批改作业,我把这件事告诉他,并求他去把他们叫回来,他对我的要求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在他的概念里,去湖里游泳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倒是我的大惊小怪让他十分烦躁,他敷衍了几句,然后埋下头继续他的工作。
那天一共有七个人去湖里游泳,只有三个人回来。
四个人被淹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明明都会游泳,而且他们也并没有被水草缠住,幸存者说,他们沉下去之前没有任何迹象。
死亡学生的家长跑到学校大闹,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数学老师被开除了,因为当时正好有人听见我向他报告,学校也正好需要找个人出来平息公愤,于是数学老师成了这个人。
后来我在街上遇见数学老师,他用仇恨的目光瞪着我,我知道他为什么恨我——如果我那天没有去向他报告,他就可以不用知道这件事——不知者无罪。
我很内疚,因为数学老师是个好人,他之前一直对我不错。
初一的时候,表弟林康到我家里来过暑假,我再一次从他的身上闻到了同样的臭味,因此当他说要去爬山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劝了他很久,他不听,于是我只好把他捆了起来,塞进了衣柜里,我很喜欢林康,我不想看见他成为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但是林康在衣柜里一直哭一直骂,这让我很心烦,于是我关上门,一个人到街上逛荡,直到傍晚才回家。
但是那个时候我家已经变成了一片熊熊火海,母亲在外面哭天号地,因为她以为我也在里面,我试图冲进去,但是被大人们死死抱住了,大火被扑灭后,人们在灰烬里找到了林康,他已经被烧成了一具蜷缩的焦尸,他身上的绳子也被烧掉了,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无法逃出来的真正原因。
看见林康尸体的时候,我晕倒了,之后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说胡话,等到一个月以后出院,我便发现自己除了那种臭味之外,其它什么气味都闻不到了。
我闻不到鲜花的香气,闻不到草地和树叶,闻不到食堂里的饭菜味,闻不到作业本上散发出来的钢笔墨水的味道,我不会因为隔壁厨房飘来的煎辣椒油的气味而眼泪汪汪,也不会因为一碗苦药而皱起眉头,路过公厕的时候不再捂鼻子,但是也不会再为了一块五彩缤纷的蛋糕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世界里的唯一剩下的气味就是死亡的气味。
我常常看见一些人,这一刻还在笑着,吵着,发着呆或是把肚皮吃得滚滚圆圆,下一刻就倒在了车轮之下,也许前一天才在你面前说将来要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第二天早上就已经躺在了停尸房……
没有气味的世界只不过是枯燥,而只有那种气味的世界简直就是噩梦。
唯一知道我秘密的人是我母亲,她告诫我,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
大家看不见我的能力,可是他们总能看到我的不能,很快就有人就发现我失去了常规的嗅觉,他们在我的课桌里放了一包狗屎,然后告诉我那是一份礼物。
我闻不到臭味,于是兴高采烈地拆开……
教室里充满了嘲笑声。
女同学捂着鼻子躲开。
“真臭!真臭!”所有人一起说。
我于是愤怒了,指着其中一个人大叫:“你们家才臭!你爸爸才臭!臭死了!”
后来他爸爸真的死了。
之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好几次。
每一次当我被激怒时,每一次当我忍不住说出某某某的谁身上很臭时,那个人很快就会死去。
大家终于发现了我的能力——但是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种诅咒的能力。
当我说一个人很臭时,就是我诅咒了他。
没有人再敢在我的课桌或是书包里塞进任何东西,他们怕我口中说出的下一个名字就是他们本人。
一开始我颇有胜利的快感,可是这种快感很快就变成了沮丧——没有人在被所有人隔离和回避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心情愉快。
我身边的座位被空了出来——没有人敢挨着我坐。
后来有传言说我的诅咒能力其实是一种遗传,因为我的母亲便是靠给人算命为生,很多人都说她算得很准。
逻辑上讲,她也是预言者。可以预言的算命者与让预言成真的恶魔确实是可以被联系在一起的。
学校找到我的母亲,传闻说校长跟我的母亲下跪了,跟校长一起下跪的还有很多学生家长。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在母亲那里得到过证实,她也没有提起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确实离开了那个城市。
从那一天开始,不管我在什么人身上闻到那股味道,我都会保持沉默,就这样,我和母亲过了很多年平凡并且平静的生活。
直到七年前,我在母亲身上闻到了死亡的气味。
我抱着她嚎啕大哭,我辞掉了工作,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不让她做任何可能发生危险的事,不让她靠近任何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我睡在她房间门口的地上,我花光所有的钱买下昂贵的补品和保健品……我小心翼翼,我想尽一切办法……可是她还是死了。
她死于心脏病发——可是在此之前从来都没有检查出她有心脏病。
“……人从一生下来,就是在往死路上走,”临死前她喘息着对我说:“没有人可以超出生死之外,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能主宰的,死亡不像你想得那么可怕,其实它只是另一个开始,我知道这很难,可是你要学会放手,不管那个人是谁,活着不一定是最好的结局。知道吗?如果你不放手,死去的人也就不能重新开始了,那样的死亡才可怕。所以,答应我,孩子,不管是我,还是将来那个对你很重要的人,你一定要放手……”
我答应了她,放开了手,她死去了。
现在,我又闻到这股味道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做到放手。
因为它来自于我自己的身上。
2
我不想死。
再过几天,我就满二十七岁了,这是一个很年轻的数字。
我开着一家花店,前店后屋,虽然我闻不到鲜花的气味,可是我喜欢坐在它们中间,让记忆中的香气包围着我,这个方法是母亲教会我的,她说所有的东西都会衰亡,无论是香气还是别的什么,而一个人死的时候,他唯一能带走的就是回忆,记忆是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唯一真正获得的东西。
我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就死去了,我是一个遗腹子,我母亲守寡的时候还很年轻,可是她没有再嫁。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有回忆就足够了,她和父亲之间的回忆已经足够她过完一辈子,她从来没感到过孤独,更何况还有我陪着她。
母亲还对我说,你不要把这件事当作是不幸,而要把它看做是一种幸运。因为生活是不断变化的,很多最初的美好到后来都会变得乏味,甚至丑恶,而我记住的那些美好气味已经被永远留住了,不会被扭曲,也不会被抹杀,她常常说,现在的花没有以前香了,现在的泥土也没有以前那种生气勃勃的味道了……她压低声音对我说:现在的好多女孩子,都用劣质香水,你要是闻得到,会把你熏晕过去的。
于是我们一起大笑。
母亲教会了我如何让自己幸福地活着,在失去她的七年里,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幸福,可是我还不够幸福,或者说,我的幸福才刚刚开始。
因为我刚刚才遇到小雅。
我想她绝对不是那种会使用劣质香水的女孩,她有着顺畅丝滑的长发,像一匹黑缎子一般披在肩上,她喜欢穿素色的连衣裙,脸上不施粉黛,可是依旧白里透红,微微的几颗小雀斑,俏皮地洒在挺直的鼻梁上。
她常常到我的花店里来买花,她喜欢香水百合。
我总是用最便宜的价格卖给她,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常常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喜欢看见她站在那里选花的样子,我把那个场景用笔画了下来,她来的时候,我便把画送给她。
她惊喜地叫起来:“天哪!你画得竟这样好!你是个隐居的艺术家吗?!”
后来小雅邀请我去她的生日PARTY,我送了她一千朵红玫瑰,那一晚所有的人都在羡慕她。
“小雅,你朋友是开花店的吗?”
小雅便捂住嘴笑:“是啊是啊,我朋友就是开花店的。”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母亲把一束明黄色的野菊花插进瓶子里,我站在旁边深深地吸气:
“妈妈!真香呀!”
母亲便回过头对着我微笑:“是啊,真香。”
就是那样的香味在我的身体里弥散开去——幸福的香味——我对自己说,一个故事要开始了,一个幸福的故事。
我怎么能死呢?
——故事还没有结束,我想看见它的结尾。
我决定去找老孙头。
过去,当一个人的身上出现臭味,那个人很快就会死去,但是老孙头却是一个例外。
七年前我就在他的身上闻到过那种味道,那股臭味至今都还存在,可是他还活着,老孙头开着一家纸钱铺,长着一张仿佛全世界都欠他钱的马脸,常年没有血色,皮肤白得像他扎出的纸花,他从不讨好顾客,但是生意却一直不错,或许大家觉得就应该从有着那样表情的人手上购买那样的东西。
老孙头是一个怪人,很少和人聊天,当然人们也不大愿意和做这种生意的人有什么深入交往,他总是独自阴森而沉默地坐在柜台后面的那把椅子上,那椅子很低,每次客人上门,敲着柜台大叫“老板在不在”的时候,他才站起来,每每总能吓人一跳——因为那看上去就像是他从地底冒出来一般。
直觉告诉我,老孙头的幸存绝非偶然,一定有某种原因,或者说,他用某种不为人知的方法逃过了这一劫。
我一向认为,性格古怪的人总是有非同寻常的能力,至少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
直觉还告诉我,他极有可能是唯一可以帮到我的人。
我提着一堆礼物和一堆笑容站到了老孙头的门前,我使劲敲着门,我听到有拖鞋声走近,但是它们在门口嘠然而止,我知道老孙头的那一双吊睛眼正通过那个黑洞洞的猫眼看着我,我保持身体的笔直和脸上的笑容,努力争取一个好印象。
“孙大爷,我是阿晖啊,街口鲜花店的,十年前我妈妈死的时候,纸钱都是在你这里买的,您还记得吗?”
我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门后面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回应。
最后我只好把礼物放在老孙头的门口,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些礼物原封不动地放在鲜花店的门口,很明显,老孙头知道我是谁,但是他不愿意接受我的礼物。
由此我更加确信老孙头不是一般人,我想他知道我要求他做什么。
于是我跪在了纸钱铺的门口,这是一个不要脸的举动,我一直是一个很要脸的人,但是在不要脸和不要命之间做选择,我还能选择什么呢?
周围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小伙子,你做了什么错事要下跪啊?”
“老孙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看人家跪得这么可怜,你就原谅了人家嘛!”
“小伙子,起来吧,够了,丢人呢……”
老孙头铁青着脸走出来,他关了铺子,径直上楼去了,他没有问我——他越不问我,就越证明他什么都知道。
我跟着他上楼,又跪在了他的家门口。
“求求你,救救我。”我对着门缝说:“我真的不想死,只要你能帮我度过这一劫,我可以把我的花店送给你,你要什么都可以!”
门开了。
老孙头走出来,他扶着他的老伴,一个瞎了眼的老太婆。
我立刻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臭味,那正是来自于老孙头身边的女人。
老孙头扶着她下楼去了,他没有转头看我一眼,仿佛我根本不存在。
我跟着老孙头到了医院,医生对老孙头说他的老婆肾脏衰竭,活不了几天了,老孙头抓着他老婆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别哭,别哭,”我看见老孙头的老婆摸着老孙头的头,像一个哄着儿子的母亲:“我走在头里是好事,要是你先走,剩下我一个人,又老又瞎,可怎么办呢?”
老孙头于是哭得更厉害了。
他的神情似曾相识——我想起了七年前的自己,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抓着母亲的手,痛不欲生,我想用世界上的一切把她换回来。
我知道我不用再去问老孙头答案了。
他如果有那样的办法,一定会用来救他的老婆。
3
我偷偷地跟踪老孙头。
他离开了医院,坐上一辆公车,然后在安宁公墓园停下。
老孙头上了墓山,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夜幕降临。
然后,我远远地看见他在一座墓碑前蹲了下来,从怀里掏出一把小花锄,在墓旁的一棵白杨树下挖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从土坑里取出一个黑色的小盒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张黄色的符纸,小心地放进贴身的衣兜里,然后他又把盒子埋了回去。
老孙头离开了公墓,没有再去其它地方,而是直接返回了医院,坐在他老婆的病床前,打起盹儿来。
于是我火速再次回到了墓园,并按照记忆找到了那座墓碑。
墓碑上写着:孙冲。生于1943年1月3日,卒于2003年4月5日。
孙冲正是老孙头的名字。
这应该是他自己的坟墓。
难道这就是老孙头的方法?
我听说在很早以前,某些地方有为患有重病的亲人活出殡的风俗,有的还会造一座假墓,棺材里放一具木头尸体,上面刻着病人的生辰八字,据说这样就能骗过阴间的使者,让索命的无常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便不再来寻找,而病人也就因此逃过一关。
我震撼得发抖,不是因为老孙头给自己造了一个假坟,而是因为墓碑上刻着的日期。
2003年4月5日。
那正是我母亲的忌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
我发了疯一般地从白杨树下挖出那个黑色的盒子。
盒子里还有一张符纸。
符纸的一面是黄色,上面写着:孙冲:壬午 壬子 辛酉 戊戌
符纸的背面是红色,我把它翻过来,立刻便看见了我母亲的名字:
曾永莲:癸巳 甲寅 癸丑 壬子
那正是她的生辰八字!
符纸发出古怪的香味——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闻见除了死亡气味之外的其它味道。
这说明,这种气味并不是寻常的气味。
这种符纸,也不是普通的符纸。
我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痛哭失声。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老孙头的身上出现那种气味但是他却没有死,为什么我的母亲明明没有心脏病却突然死于心脏病。
这是某种可怕的邪术。
老孙头,那个邪恶的家伙,他用这种邪术夺走了我最爱的母亲的生命,他把它嫁接到他苟延残喘的躯体里,或许正因为他是一个本应该死去的人今驱动他行走的力量本属于另一个人,所以他身上的臭气才会一直无法散去。
因为他对我的母亲做了这样的事,所以他才会那样躲着我,因为他心虚。
我捏紧了拳头,全身战栗,仇恨之火焚烧着我的五脏六腑。
4
我怀里揣着匕首,走进医院。
医院里人来人往,大家各怀心事,没有人有多余的气力去注意一个陌生人。
那几天,我找到了差不多二十个可以下手杀死老孙头的机会,但是我最后没有下手。
因为我想起了被他取走的那张符纸,很明显,他想用那张符纸去救他老婆的命,使用七年前他已经使用过的方法。
要报复一个人,要让一个人痛苦,莫过于夺走他最想要得到的东西——这远比单纯地杀死他要痛快。
我想看见他失去唯一亲人时的绝望,我就是要让他尝到这种绝望。
于是我偷走了那张符纸。
符纸黄色的一面仍然空着,但红色一面已经写好了一个名字:陈奇。下面是他的生辰八字。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会看见他的名字。
陈奇是我的情敌。
他是小雅的大学同学,我在小雅的生日会上见过他,他长得还算英俊,据说是某个公司老总的儿子,颇受女生欢迎的富二代,他也曾经在我的花店买花送给小雅,我也曾看见过他和小雅一起去看电影,小雅对他的印象似乎不错,算起来,他是一个颇有实力的竞争对手。
不过我讨厌他倒不是因为这一点,我见过太多那样的纨绔子弟,他们热衷于始乱终弃的游戏,反正有父母买单,我见过太多因此而伤心欲绝的女孩。我觉得小雅不会真正喜欢那样的人,他们在一起也不会有天长地久的幸福,可是我依旧有些担心,因为小雅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她很有可能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
我想了很久,最后把符纸放回到了老孙头的口袋里。
还有很多机会让老孙头痛不欲生,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看看他怎样去利用这张符纸?也许我可以因此得到活下去的机会。
我对这个决定很满意,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更为聪明的选择。
5
陈奇忽然得了急性肾功衰,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小雅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便晕倒在地。
医生说治好陈奇的唯一希望就是换肾。
小雅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捐肾,但她不是适合的捐赠者,因为她有先天性心脏病。
“我不能没有他。”小雅对我说:“如果他死,我就陪着他死。”
我五雷轰顶地呆立在原处,心被撕扯成一片一片——我没想到小雅对陈奇的感情竟然已经深到了这种地步。
“为什么?”我问小雅。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在他出事之前我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朋友,可是现在我知道他早就在我心里扎根了,我已经不能没有他了。他开心我就开心,他难过我也会哭,我想我不会再对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他死了,我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小雅说的话,正是我想对她说的话。
我知道小雅不是说说而已。
因为她的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出臭味。
我走出病房,发现陈奇的母亲站在门口,她的眼睛红肿,手里提着一篮水果,看来她是来看望小雅的,因为这是一个打算把自己的肾脏送给他儿子的女孩,虽然她没成功。
在陈母的背后跟着一个男人,但不是陈奇的父亲,他的长相很招人厌,左腮有一颗长毛的黑痣,这让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味更让人难以忍受。
我没有和他们打招呼,径直离开了。
隐约地,我听见身后的小雅和陈奇的母亲抱在一起痛哭——为了同一个男人。
这真让我心如刀绞。
6
深夜。
老孙头跪在一堆白色蜡烛围成的圆圈之中,嘴里喃喃地念着什么,我听不清,但估计是咒语之类的。
在他面前放着一个小小的祭台,装着符纸的黑盒子被供奉其中。
他苍白的脸在烛火中跳跃着,神情肃穆得如同死神——对于那个即将被他夺走性命的人来说,这个比喻恰如其分。
这是一幕骇人的景象,幸好是出现在郊外无人的树林之中。
这已经是第七天。
在这七天之中,陈奇的病越来越重,任何药物都无法遏制住恶化的速度。
我刚去看过小雅,她坐在陈奇的病床前,她很平静地看着他,那种平静源自于绝望——她身上的臭味已经达到极限状态了。
我拿出匕首,慢慢地老孙头靠近。
念咒声嘠然而止,老孙头睁大眼睛看着我,他的眼里流露出惊恐:
“你听我说……”他大叫!
我不想听,不管他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他是恶魔的事实,我的匕首刺进老孙头的腹部。
他的血喷到了我的身上。
现在我也不在乎得到什么秘密了,也没有时间了,我只想要小雅活下去。
要让她活下去,陈奇就必须活下去。
老孙头捂住腹部,看着我,我在他的眼里没有看见惊讶,只有遗憾。
“只差一点点。”他说,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老孙头哆嗦着把手伸进怀里,摸出一封信,塞到我手上,他的头垂下来,死去。
信是给我的。
信上沾着老孙头的血迹。
信封上的笔迹却是母亲的。
我急急地拆开。
钟晖吾儿:
真希望你永远也不要看见这封信。
因为那样的话,就说明我成功了,你将会平安健康地活下去,幸福会一步一步地向你走来,就像你一直所期待的那样。
可是如果你看到了这封信,我的孩子,也不要难过,即便你现在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即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不要怕,孩子,还得妈妈说过的话吗?人从一生下来,就是在往死路上走,死亡并不可怕,有生就有死,死亡只是另一个开始。
这句话听起来很空洞,是吗?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吧,过去我保守这个秘密,是因为我害怕它会伤害你,可是现在,它也许能拯救你。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也拥有预言的能力。只是我预言的方式和你不同,我会做梦,然后在梦里看见将会发生的一切,但我和你一样,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预言,我曾经和你一样痛苦,在我最痛苦的时候,遇到了你的父亲,他拯救了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嫁给了他,可是好景不长,我很快便梦到自己的死亡,我会难产而死,而我腹中的孩子,也就是你,你也不会活下来,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预言一定会成真,可是你父亲改变了一切,他用他的寿命换来我们活下去的机会,他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其实他原本可以活到八十岁,可是他把剩下的五十四年平分给了我和你,。
看到这封信的你,应该正好是二十七岁吧?是的,就是这个数字,这就是你父亲给你的礼物——二十七年的生命,知道吗?孩子,你和我其实早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是你的父亲给了我们一个奇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每一天,都值得感恩。
你父亲说他本是天煞孤星之命,注定无妻无子,可他有了我们,他宁可死,也无法忍受失去我们的痛苦,他想要你生到这个世界,他想让你长大成人,想让你体验生命的酸甜苦辣,想让你带着他的血脉真正地活着,哪怕,只有短暂的二十七年。他说为了你,要跟命运搏一搏,这就是你的父亲,孩子,我没有办法拒绝,因为我是你的母亲。
你的童年虽然和别人不同,但是我给了你我所能给与的全部,我们一直过得很平静,很幸福,后来我变得贪心了,我希望这种幸福不要结束,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梦境里的预言却让我越来越害怕,我梦见你爱上了一个名叫顾小雅的女孩,我梦见她为了一个叫陈奇的男子死去,我梦见你很痛苦,你为了她和陈奇争吵,在争执中陈奇杀了你,那个时候你刚好二十七岁。
我不想看见这些发生在你身上,于是我也决定跟命运搏一搏,就像当年你父亲为你我所做的那样。
我找到了老孙头,他当时得了癌症,就要死了,他不怕死,可是他放不下他的妻子,他怕自己死后,又老又瞎的老伴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痛苦,他的妻子刚好还剩下七年时间,所以我把自己剩下的七年送给了他,并把借寿的方法和符纸交给了他,而作为交换条件,他必须在七年之后,在他的时间耗尽之前,用同样的方法来救你,他必须弄到陈奇的生辰八字,在你的寿命将尽之前完成整个仪式,这样一来,那个叫陈奇的人会死去,而你会继续活下去。
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虽然这个叫陈奇的人并非善类,死有余辜,但这种做法始终可耻,我没有事先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去做选择,尤其是这样残酷的选择,我害怕你不能做出选择,所以原谅我,我先替你做了决定。
在这件事之后我就完全失去了预言的能力,我想这大概是某种惩罚,我不再做梦了,我无法得知成败,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如果最后真的失败,也不能怪任何人,其实我们已经从命运那里偷盗了很多时间,不能如愿也只因我们贪得无厌。
我真的希望你也能这样想,这样就不会那么痛苦了,是不是?
我对老孙头说,如果他失败了,就把信交给你,因为你有权知道真相,在死亡来临之前。
作为一个母亲,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永远爱你的妈妈
2003年4月4日
老孙头的尸体已经僵硬了。
我打开黑盒子,符纸的另一面,果然写着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这张符纸没有任何味道。
或许,只有当它起了作用才会散发出香气吧。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把老孙头深埋在一棵柏树的下面,七年期限已到,他注定会死,我不必去警察局自首,但是警察迟早会发现,所以我要开始另一种生活了。
我决定离开这个城市,这样就永远不会再见到陈奇,还有小雅,我也许无法阻止自己的死亡,但是至少可以让母亲预言过的场景不出现。
清理完现场之后后我返回了医院,老孙头的老婆在两个小时以前被医生宣告死亡——她几乎是和老孙头同时死去的。
也好,他们都得偿所愿了。
在离开之前,我会卖掉花店,再买下一块墓地,把他们两人合葬在一起。
在离开肾病病区之前,我忍不住去看了陈奇——他和老孙头的老婆住在同一个住院部,就差一点点,老孙头就可以成功地完成仪式,母亲的计划就可以成功,讽刺的是,我亲手摧毁了这一切。
可是我不后悔,如果我活着,而小雅却因此死去,就像她说的,那么生活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陈奇已经苏醒了过来。
我看见他和他的父母正抱头痛哭。
“妈!你做到了!你做到了!”我听见陈奇在哽咽,满脸劫后余生的欣喜若狂。
陈母的身上,正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香气。
我朝小雅的病房狂奔。
小雅的尸体正被推出病房。
她的家人都还没有得到消息,她如此孤独地离开。
“奇怪,”一个护士正嘟哝着:“怎么忽然之间就肾脏衰竭了?她只有心脏病史啊!”
“真可惜,”另一个护士叹了口气:“今天早上不是才找了什么大师来合八字吗?听说跟那女人的儿子是天生一对呢,还说要结婚冲喜呢!还说那大师是什么高人呢!”
“呸!这种迷信的东西,也信得啊?!”
我跟着小雅的尸体走进太平间。
她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