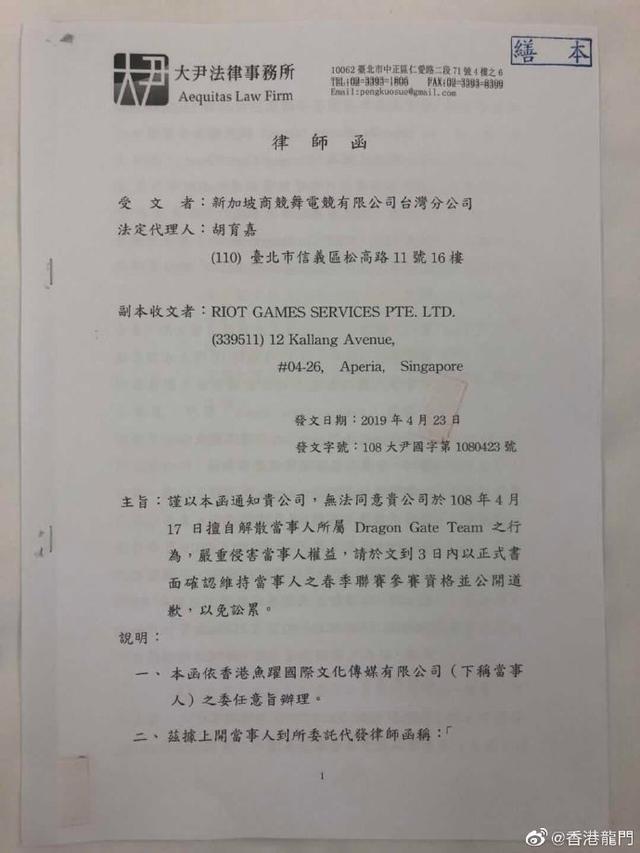【壹】
杜青衣初次见霍连桑,是在任府大少爷任祁楼留学归国的第三天。
任府早早发出请帖,准备大宴宾客为大少爷接风洗尘,还发出消息要请上海最有名的戏班子来助兴。戏班的班主因着与任府管家有些许旧交情,偷偷塞了个大红包,拿下了任府的这一活儿。
班主在杜青衣耳边再三叮嘱:“青衣啊,这次你一定要拿出绝活来把戏唱好,我们戏班子一家老小吃糠咽菜全靠你了!”
杜青衣盯着碗里的大鸡腿,如同饿狼碰见了肥兔,猛扑了上去,把脸埋进了碗里就啃,只露出一个乌黑的头顶。
这也不怪杜青衣,戏班子已经半年没有演出,早已穷得揭不开锅,整个戏班大大小小十几口人,早饿得瘦骨如柴。任府提前两天让戏班的人进府安顿排戏,虽然将戏班十几口人分配到下人住的偏僻角落,可饭菜却是管够,对戏班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十几口人来说,已经是久旱逢甘霖。
班主于杜青衣有恩,当年如果不是班主将她带回戏班,她早就饿死街头了。班主说她是块学戏的料,奈何她心不在戏曲上,学了几年,只拿得出手一出《霸王别姬》。
杜青衣此刻才惊觉懊恼,行走江湖,学艺不精,根本讨不到一口好饭吃。
可这些懊恼,在她听到任府二楼传来的一些莫名的音调时,抛到了九霄云外。与她在戏班里听到的叮叮邦邦,咿呀呦嘿不同,曲调悠扬,听到耳朵里,软糯糯的。好奇心就像是爬过心头的一只蚂蚁,让杜青衣的手都痒了起来。
任祁楼修长白皙的手按下钢琴上的最后一个黑键才悠悠起身,大步往窗口的方向走来,一把拉开厚重的窗帘,盯着窗边瘦小的脸蛋,脸上挂着微醺的笑意:“看够了么?”
杜青衣从没有看过这样好看的男子,剑眉星目,面如冠玉,一身合体的西服,更衬得他身姿挺拔,竟比她在报纸上看过的新式装扮还要好看,她不由得看呆了,脸上不自觉地爬起一丝潮红。
对上那一双星眸,她居然有了一丝紧张,偷窥还被人家抓了个现行,她趴在窗边的手做势就要收回,准备溜走。手才刚一松开,就被一双温热的大手一把用力抓住,只听头顶上响起温和的声音:“这里太危险了,快上来。”

民国一十八年的上海,欧式的洋楼甚少,杜青衣只在租界外面远远看过一眼,却没想到有一天能站在如此气派且遥不可及的洋楼里。她一身破旧的麻布上衣和黑色布裙,站在窗前局促不安地将破了一个洞的布鞋往裙底藏了藏,才怯怯地抬起小脸。
“你为什么要爬窗,女孩子爬窗多不文雅。”任祁楼坐回钢琴前,脸上还是洋溢着笑容,没有一丝被人偷窥的责怪。
杜青衣站在他面前双手捏着衣角,半响才小声道:“你弹的什么乐器,真好听。”
任祁楼挑了挑眉,来了一丝兴趣,指了指身后的钢琴:“我弹的是钢琴,从法兰西带回来的。”
任祁楼还想问什么,这时有下人敲了敲房门:“大少爷,老夫人有事找你相商,请你到书房。”
杜青衣被这一阵敲门声一吓,转身就往窗口跑去,一下子跃出了窗户往下攀爬,速度之快着实吓了任祁楼一跳,他追过去,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像猴子一样灵活落地,才长输了一口气。
杜青衣纵身一跳,落在草地上,起身时回头瞥了一眼窗户上的少年,落荒而逃。
【贰】
任府将戏台搭在了自家的后花园,还在后花园摆了十张长方桌子,上面铺着丝滑的白布,桌面摆着几盆艳丽的秋海棠,竟有着说不出的雅致。
铜锣一敲,班主就到后台催促,杜青衣对着镜子里初现虞姬模样的油彩小脸,把眉毛描得又细又长后,满意地转身登台。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受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眼波流转,葱指翻飞,台上虞姬登场,一举手一回眸,皆是赏心悦目。莺啼婉转的唱词立刻吸引了宾客的眼光,台下有人拍掌,大声喝道:“好!”
杜青衣只觉得台下觥筹交错里,有一道炽热的目光,烫得她的后背如同火烧。
她一个目光流转,就瞥见了站在台下一身月牙长袍的少年。与满后花园身着西服的宾客不同,他是一身旧式月牙长袍,笔直地站在一株秋海棠旁边,手执一透明玻璃杯,端是一身高贵清冷,遗世而独立。
身穿燕尾服的任祁楼执着一杯红酒走上来,站在了霍连桑的身边,看了一眼台上的虞姬,又看看身身边清冷的男子,扬起一个温和的笑容:“可还习惯?”
霍连桑举举手中的酒杯,回了一句:“尚好。”
这时,却有三五个年轻的男子走了过来,领头的男子一身黑色西装,衣领处带着精致的领结,嘴唇微微上挑,带着一丝玩世不恭:“我说祁楼,你这宴会可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的吗?”他看了一眼一身长袍的霍连桑,眼神里尽是轻蔑。
任祁楼眉头一皱:“顾少!”语气里略带警告和责怪。
顾少是都督的儿子,与任祁楼是同门师兄弟,一起去法兰西留学,感情甚好。而霍连桑,不过是近两年才从杭州搬到上海的绸缎庄老板的儿子。这一帮贵圈的子弟,见顾少出手刁难霍连桑,没有一个要出手帮忙的意思,都等着看好戏。
霍连桑的目光从虞姬身上收回,周身的温度也跟着降了好几度:“怎么顾公子喝了几年洋墨水,披了一身洋装,就连尊重长辈四个字也忘记怎么写了吗?”
“你!”顾少手上青筋爆起,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拳头就要挥过去,被任祁楼一把拉了回来。
身边一帮纨绔子弟好奇心大起,纷纷开始咬头接耳:“顾霍两家什么时候攀起亲戚来了,我怎么不知道?”
“前阵子,才听说顾家大小姐与霍家大少爷有婚约,没想到是真的。”
“这么说来,霍家少爷也算是顾少的姐夫了,说是长辈也不为过,啧啧。”

每听周围的人多说一句,顾少的脸便黑一分。顾家老太爷此前与霍家老太爷有过生死之交,给自家晚辈订了一桩包办婚姻。顾少打心底里瞧不起这个充满铜臭味绸锻庄出身的霍连桑,一身旧式月牙长衫,一看上去有几分迂腐。
这么一想,顾少就有了几分怒意:“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想当我顾家的姑爷?迂腐!”
霍连桑遥遥指了指戏台上与西楚霸王爱得难舍难分的杜青衣:“在顾公子眼里,就连这些戏曲也是迂腐的吧?”他讥讽一笑,语气不温不热:“刚刚击掌大喝一声好的人,我想应该不是顾公子。”
霍连桑没想到,他一句简单的反击,就让戏班丢了到手的饭碗。入夜,宾客散去,杜青衣还在与一只鸡腿奋战,管家拿着几个大洋丢过来:“你们明天不用上台了,拿了钱今晚走吧。”
杜青衣将手里的鸡腿一丢,张开手拦住了管家的去路:“管家,宴席还是还要开两天吗?我们唱得好好的,为什么赶我们走?”
管家不耐烦地摆摆手:“走吧。你可知道,今天来任府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这一出《霸王别姬》已经惹得客人不快,若明天再唱,”说着,管家伸出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我这任府管家也做到头了!”
【叁】
霍连桑再次见到杜青衣时,她躲在霍府门前高大的石狮下,豆大的雨打湿了她的衣服,紧紧贴在她瘦骨嶙峋的身上,凌乱的头发贴着她苍白的小脸,只露出一双楚楚可怜的大眼睛,甚是狼狈。
黄包车刚在霍府门前停下,她就如同一只愤怒的小狮子一样扑上来,撞倒了车夫,扑上车子压在他的身上,冰凉的手掐着他的脖子,带着哭腔喊道:“都是你害的!”神情狰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
管家撑着伞上前,怒不可遏地指着鱼贯而出的家丁,喝道:“都是干什么吃的,还不快把人拉开!”
家丁还没上前,霍连桑就轻轻摆手,眼前前一秒还张牙舞爪的小姑娘,刚才那一扑,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此刻早已经昏了过去。整个人软软地趴在他的身上。
霍连桑淡定地抱着一身湿漉漉的杜青衣,从黄包车里走出来,管家撑着黑布雨伞连忙上前,他冷眼一瞥,扔下一句话:“去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接着抱着娇小的人儿大步进了府门。
管家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回报给霍连桑时,霍连桑手里正拿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中药在细心地吹着。管家看了看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杜青衣,心中暗想:从小到大少爷还从没有亲手照顾过哪位姑娘呢,这姑娘真是有福气。
可躺在床上的杜青衣却不这么想。霍连桑吹凉了药往她嘴里灌时,她一个警惕醒了过来,一伸手就将霍连桑手里的药打翻了:“不要你假好心!”
苦涩的汤药淋了霍连桑一身,可是他面色不改,而是温柔出声:“你淋雨受了风寒,昏睡一天了,你不要想太多,把身体养好要紧。”
怎料霍连桑话一说完,她就从床上跳了起来,直接抓着他的衣领,慌慌张张地说:“我睡了一天了?”
霍连桑连忙扶住她:“你快躺下。”
杜青衣松了手,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不冲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哭:“来不及了,班主,你不要走,不要丢下我。”
霍连桑追了出去从后面一把拉住她,万古不变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怒意:“你疯了!你还发着烧,你要去哪里?”可看着她哭泣的脸,语气又忍不住弱了下来:“你要去哪里,我找人送你。”
“车站,我要去车站。”
此时的上海,正下着蒙蒙的细雨,车站里人群穿梭,在这个世事动荡的年代,到处可见生离。杜青衣发了疯似的在人群里穿梭,每看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马褂的中年男子,都要冲上去喊一声班主,声音是那样无助彷徨。
终于汽笛长鸣一声,从上海开往北平的火车叫喧着开走,杜青衣双手抱着膝盖缩在月台上抽泣:“班主,不要我了,他不要我了。”

她的人生,又回到了十一岁的原点。
她是孤儿,流浪街头乞讨为生,为了争半个馒头与人打架,为了一二毛钱硬拉着过路行人的裤腿苦苦哀求,直到有一天,一个男子蹲在她面前问她想不想唱戏,进戏班,虽然生活清苦些,可至少有个地方安生立命,她忙不迭地点头,跟着男子进了戏班。
那个男子是戏班的班主,时至今日,她还清楚地记得班主跟她说的第一句话:“你给我磕三个头,我认你做我的关门弟子。”
那一刻,她突然觉得,她有家了。
如今六年过去,她已然十七岁,戏班解散了,班主回了北平谋生,这一次,没有人要她了。
霍连桑撑着伞站在她身边为她挡去了所有的风雨。听她断断续续地讲着那些不堪的过往,可是他却不知道好何去安慰这个跟他一样大的姑娘,他没有经历过朝不保夕的生活,无法感同身受。直到她停止了哭泣,他才拉住她的一只手臂:“你跟我走吧,我们霍府还缺丫鬟的。”
他一出声,就激起了眼前这个小姑娘的怒意,她一把推开他的手,一脸倔强地瞪着眼前这个罪魁祸首:“我才不给黑心肝的奸商打工!”话毕,一头冲进雨雾里,倏尔不见了踪影。
【肆】
拒绝了霍连桑的好意后,她重拾老本,在上海街头靠卖艺为生。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攒够了火车票的钱,去北平找班主。
她拿着个破铁盆一敲,一个跟斗翻去就在街头演起了美猴王,她从小古灵精怪,演起美猴王来也是得心应手,再加上年纪小,很快就吸引了群众围观,她一个翻身,兴奋地拿着铁盆个从人群里走了一圈,走到半路,一双白皙如玉的手扔了一块大洋进来,她抬头看去,面前的少年正笑容和煦地看着她,她霎时红了脸,吞吞吐吐叫了一声:“任……任少爷。”
明明前脚才说不给黑心肝的奸商打工,后脚就跟着任祁楼的脚步踏进了霍府的大门。霍府的管家还认得杜青衣,她一进门,管家就冲上来,毫不客气地指责道:“我说你这个小姑娘真不让人省心,我们少爷发了多少人去找你!”
杜青衣把小脸别开,心想,他对她这般好,莫不过是良心不安罢了。
任祁楼把手放到嘴边,轻咳了两声:“管家,你们少爷现在可在府里?”
管家自是认得任祁楼,当下也不好跟杜青衣计较,毕恭毕敬地将两人引到了书房。
杜青衣还是头一回认真看这个少年。
偌大的桌子前,是堆积如山的账本,他坐得笔直,一手翻着账本,一只手有条不紊地将算盘拨得噼啪作响。明明和她差不多年纪,却是不言苟笑,老成持重,周身带着一股疏离。
任祁楼上前,一把将他手里的账本按住,打趣道:“看,我把谁带来了?”

霍连桑抬眼,看了一眼虽然狼狈但还算完好的杜青衣,脸色才稍稍缓和:“有劳。”他似乎是不多话的人。他跟任祁楼谈事情,杜青衣就无聊地在他的书房里到处走,她似乎对这些笔墨纸砚都很好奇。她东摸摸西看看,也怡然自得,就连任祁楼走了,都没有发现。
她在书架 拿了一本《增广贤文》翻了起来。窗外散落的阳光细碎地落在她的身上,带着异样的柔和,纤细的手指,捏着泛黄的书页,与前两日张牙舞爪的样子判若两人。
霍连桑走到她身后,盯了一眼她手里的书,有一丝诧异,也有一丝欢喜:“你识字?”
许是他的突然出声惊了她,她手里的书颤了颤眼看就要掉下去,突然身后伸来一双大手,稳稳地将书托住了。他温热的呼吸打在她的脖子上,她立刻像被蜜蜂刺了一下,跳开来,心中小鹿乱撞。
意识到他问的是她,她又摆出一副满争锋相对的样子:“难道只允许你们这些贵公子读书,我们穷人就不可以识字了么?”
听到她话里的讽刺,霍连桑眉头一皱,“我没别的意思,只是那天听你说十一岁就进了戏班,”他顿了顿,又问得极小心翼翼:“那你是十一岁之前识字开蒙的?”
他眼睛紧紧地盯着她,生怕错过她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就连呼吸都变得不稳定了。她把书扔回到他手里,兀自走到他的桌子上拿了茶就往嘴里倒:“这么久的事情了,我哪记得那么多?”
霍连桑没有再追问下去,但神色却是有松了一口气的轻松,不似先前的沉重。
【伍】
自那日起,杜青衣便顺顺当当地在霍府做起了丫鬟。掌管着霍连桑书房的笔墨纸砚。活儿倒是比旁人轻松。就连她偷懒看书,霍连桑也没有责怪。
她原本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自然不会细想霍连桑为何待她不同旁人,她只当他心中有愧。大多数时候,她在一旁看书,他在一旁看账本,将算盘敲得如雨点细密,两人难得没有先前的剑拔弩张,倒也井水不犯河水。
但这样的宁静也仅仅维系到霍连桑回新式学堂念书当日。
民国一十八年,新式学堂传教洋文化,任祁楼归国之后,当了新式学堂的教书先生。
杜青衣寻了由头跟着霍连桑的屁股后面,溜进了新式学堂,她装模作样地坐在课堂的角落里,立起厚厚的课本,却贼头贼脑地往讲台上瞧。
只见台上的任祁楼拿着瓶瓶罐罐一一打开,整个课室顿时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他两手各拿一瓶液体左右倾倒,却突然砰的一声窜起一束火苗,杜青衣如同被针刺了一下,脑海里闪过一幅幅熊熊大火的画面,她无比惊慌地大喊一声:“着火了!”话音未落,人已经像疾风一般冲上讲台,将任祁楼扑倒在地。

霍连桑黑着脸大步走上讲台,将趴在任祁楼身上的杜青衣拉起,课室里顿时哄堂大笑,嘲讽之声尖锐响起:“哪来的土包子?”她不明所以,任祁楼起身扶额,却没有恼怒:“这是西方化学品,我在演示实验,不会有事的。”
她的脸顿时如同火烧,在讥讽的声音里,那句“土包子”硬生生砸中了她的心。她踉跄起身,扯出一个尴尬笑容转身逃离。
入夜,她在霍府大门外来回行走,直到月上柳梢头,才进了府内。她开门见山,笔挺地站在霍连桑面前,目光灼灼:“我要进新式学堂念书。”
霍连桑停下手中的笔:“为什么?”
她扯出一个冷淡的笑容,不似之前的不谙世事,而是带着刺骨的咄咄逼人:“因为,这是霍家欠我的!”
霍连桑手中的笔,啪嗒落地。
她终是想起来了。
任祁楼手中的那一串火苗,将她的回忆带回了十一岁的噩梦。入眼皆是熊熊的大火,将黑夜撕裂,漫天艳丽的染布化为灰烬,斑斓的染料流了一地,房梁断裂之声此起彼伏,杭州百年传承的杜氏绸缎庄付与一炬。
杜氏夫妇参与救火,被断裂的房梁砸中,死于大火之中。同日,杜氏独女杜青衣不知所踪。而杜氏的死对头,霍氏绸缎庄一夜间垄断了杭州绸缎生意,将绸缎远销海外,卖给了洋人。
那场大火并非天灾,而是人为。杜青衣受不了双亲离世的打击,失去记忆六年,堂堂杜氏绸缎庄的大小姐,沦为卖艺为生的落魄戏子,霍家不止欠她两条人命,更欠她一个安好的未来。
霍连桑如何能不答应?
【陆】
霍连桑早就知道她是聪慧的女子,只是不曾想,她学起洋文,学起西式课程来也不逞多让,短短半年,竟赶上了他。
只是霍连桑不知道,她这般努力,只为了一个任祁楼。
那时上海男子流行佩戴怀表,西方舶来品自然价格不菲,杜青衣捏着买北平火车票的钱,再搭上在霍府当丫鬟的工钱,才换回了一只怀表。
她鼓起莫大的勇气,在任府大门前将任祁楼拦住,将用手帕包好的怀表塞进任祁楼的怀里,转身就跑,结果一转身,就撞进了一个坚硬的胸膛。
霍连桑皱了皱眉,拉住她:“你慌慌张张地做什么?”
任祁楼捏了捏手里的怀表,反手将她拉过来:“竟然来了,不如进去坐坐?”
两个同样高大的男人,一人一边拉住了她的一只手,霍连桑脸色顿时暗沉了下来,拉着她的手越发用力:“不必了,天色已晚,再打扰终归是不妥。”
杜青衣厌恶地挣脱他的手,语气带着异样的疏离与抵抗:“少爷未免管得太宽了。”
霍连桑拉着她的手,一瞬冰凉,他紧抿着嘴唇,终是放手扭头进了自家的车子,绝尘而去。
杜青衣回到霍府时,已是半夜,走过昏暗的前厅,却瞥见一个身影站在黑暗里,紧紧盯着她,仿佛与黑夜融为一体,只见霍连桑缓缓走到她面前,淡淡开口道:“你喜欢任祁楼?”
她扯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带着一丝漫不经心:“不劳你操心。”
霍连桑抬了抬手打断她的话,走出前厅时脚步顿了顿,丢下一句话:“他并非你的良人。”

这句话像是当面泼了一盆凉水,她突然笑出声来,像是自嘲又像是讽刺:“他不是,难道你就是?”她自顾自地说下去:“说起来,我也曾与霍少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杜家还未失势时,与霍少爷也曾有过一纸婚约。只可惜,霍少贵人多忘事,而杜府也被一把火烧光了。”
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而此后,杜青衣刻意避开他,真的就不曾碰面,他好像越来越忙,就连新式学堂的课也不再去上。杜青衣知道,像他这样人家的少爷,早过了启蒙的年纪,他去新式学堂上课,不过是因为霍家如今的生意与洋人打交道,所谓知此知彼,才不易吃亏。如今这个年纪,他更重要的事情是接手自家生意。
那日从新式学堂归来,管家拿了食盒匆匆忙忙出门,在门槛处绊了一跤,摔倒在地崴了脚半天起不来,看到杜青衣,把手里的食盒往她手里一塞,便吩咐道:“小丫头,回来得正好,快给少爷送饭去。”
杜青衣还没回过神便被塞进了黄包车,拉往了霍家的染料坊。
漫天飞舞的丝绸,色彩斑斓,迷了她的眼睛,这一幕,与她小时在杜家所见别无二致。她抚过那些摊晾的丝绸,在飞舞的丝绸后,瞥见一身淡青长衫的霍连桑站在染料缸旁边,亲自给染布师傅打下手,神情专注,没有一丝一毫的架子。
她拿着食盒走过去,才发现,他手里染的,是一块大红的龙凤呈祥的南京云锦,耀眼大红,刺绣逼真,凤凰欲飞,这是嫁衣所用的布料。
只是不知哪位女子,这般有福气,让霍家少爷亲手染嫁衣。
估计是那位她还未曾见过的顾大小姐吧。
心像被一根羽毛轻轻扫过,酸酸痒痒。但很快,她脑海里就浮现了任祁楼温润如玉的脸,也好,她有她的心上人,他有他的娇妻,一人走独木桥,一人过阳关道。
【柒】
霍连桑与顾家大小姐解除婚约是在民国二十一年。
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新青年提倡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包办婚姻,本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奈何众口悠悠,硬是将此事传得沸沸扬扬。
杜青衣看了报纸,想起霍连桑亲手染的那匹嫁衣,怅然所失。
顾家虽不满意与霍家结亲,可她看得出顾家小姐对霍连桑并非没有情意。霍连桑这则启事一见报便失去了顾家的依仗,霍家绸缎庄在上海的生意开始举步为艰。
霍连桑忙得整日不回府,算起来,她与他同住一府,却已有二个月未曾碰面。整个霍府都处于低沉的气息之中。
霍连桑出事那天,杜青衣从街上听到了整齐的步伐声,巡捕房的人开着车源源不断往黄埔港口开去,那天的上海,天气昏沉,行人避让,皆不敢大声说话。有几个人窃窃私语,杜青衣站在一旁,本是好奇心重,却不料听到霍连桑三个字。
她着急地拉了一个卖烧饼的老人家,塞了一个大洋,才打听到霍家卖给洋人的货物,被巡捕房的人截获,从那批货里面搜查出了大批枪支,弹药。
几乎是猝不及防的,霍府的大门被贴了封条。有巡捕房的人重兵把守,将霍府翻了个底朝天。管家从霍府里抢出一只箱子交给了杜青衣,里面是一身大红嫁衣,一小匣子金条,还有一张发黄的求婚聘书。
管家说这是霍连桑留给她的东西。
她从未如此的茫然过。
并不长的甬道,她走得踉跄,终于在昏暗的牢房见到他,他还是如此,一身长衫,站得笔直。两人隔着一道栅栏,她睁大眼睛,只重复问他:“你会不会死?”
“放心,不会的。”

他难得给她一个笑容。说起来,她很少见到他笑,却从没有发现,他笑起来,会这般好看,嘴角微微提起,眼神温柔,让她忐忑的心,一瞬间稳当降落。
顾小姐与霍连桑临近婚期,却被霍家悔婚,顾都督哪里咽得下这口气,霍连桑入狱,只不过是想将霍家彻底赶出上海的一个手段罢了。
杜青衣去求任祁楼,任祁楼当夜买通巡捕房的一个警员,弄了一出火灾,原本是想在巡捕房救火的空隙,将霍连桑带出来,却不曾想,关押着的一群亡命之徒趁机越狱。
杜青衣在车上等到霍连桑的时候,整个巡捕房连夜出动,街上是整齐的步伐声,有枪声从耳边呼啸而过。
她再次见到他,竟然觉得恍若隔世。
她忽然想起那件大红的嫁衣,想起那刊登于报纸上解除婚约的告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她伸手抚上他满是胡茬的脸,内心突然有了答案:“霍连桑,如果这次平安脱险,我就嫁给你,可好?”
任祁楼开车将他们带到码头,“等你们过去,渡轮就开了,到时他们也追不上,你们就不要再回来了。”
正说着,枪声呼啸而来,车子一个震荡,发出刺耳的刹车声,眨眼间撞上一堵墙,玻璃瞬间破碎,霍连桑俯身,将她牢牢压在身下,只听他发出一声闷哼,抱住她安慰道:“别怕。”
任祁楼急得满头大汗:“车坏了,时间快要来不及了,只能跑去码头了。”
连多谢都来不及开口,霍连桑拉着她的手,拼命跑起来,他带着一丝微笑:“看来,我们快要亡命天涯了,你怕不怕?”
她摇摇头,主动握住他的手,“霍连桑,只要有你在,去哪里,我都不怕。”
这是他们此生,最后的一次对话。

他们赶往码头的时候,靠在岸边的渡轮,正响起急促的长鸣。
霍连桑用进力气将她推进任祁楼的怀里,终于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任祁楼,答应我,此生不要负她。”
杜青衣有些心慌了,“你呢?你不走吗?”
身后的枪声越来越紧密,他用力将他们推开,大声喝道:“快走!”
此时轮船已经慢慢离开海岸,任祁楼去拉他的手,被他一把甩开,“我走不了。”话说完,他的嘴角流出一丝血迹,接着他挺拔的身影轰然崩塌。后背扎着一大块尖锐的玻璃,已是血迹斑斑。
任祁楼死死抱着拼命挣扎的杜青衣,在最后一刻登上远渡重洋的轮船。
此生,霍连桑从未说过他爱她。可是流水无声,他的爱那般深沉,等她发觉时,已厚达千尺。
只可惜,此去经年,暮霭沉沉楚天阔。
—完—
你好,我是连城,纸媒作者,文艺女青年一枚。喜欢阅读,喜欢写作,喜欢旅行,喜欢美食,总之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有趣的灵魂,外加一颗天真未泯的童心。
坚持原创,保持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