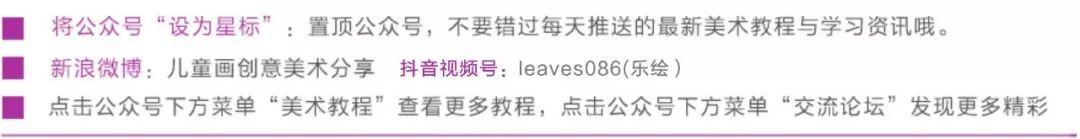乘氢气球打松塔的作业现场,打塔人的人身安全系于牵引至地上的绳子。 (受访者供图/图)
海林市山市镇处于山区和丘陵浅山区,天高云低,林多地少。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最鼎盛时期,这一黑龙江省偏远小镇曾是全国第二大松子集散地,随着产品交易市场搬至海林市区,小镇逐渐沉寂下来。一位旅店老板称,全镇只剩下3家旅店仍在营业。
只有每年9月打塔季是例外。各色口音的打塔人涌入小镇,30元一天的旅店来了生意。打塔人清晨四点多起床,赶着第一缕晨曦入山,在没有讯号的密林中劳作整天,天黑后方归。
打塔,指的是用爬树、乘氢气球等方式采摘松树顶的松塔,是一项风险高、保障少、监管难的工作,但因其门槛低、收入高,吸引了诸多缺乏经验的外乡人加入。38岁的辽宁人胡永旭原本是来山市镇探亲的,结婚对象要求买房买车,差一笔钱,想在短时间内赚些外快。打塔工资是日结,工作半月收入便可过万。湖北恩施人刘成会在2021年打塔季曾来山市镇“考察”,待了半个月左右,决定“买个气球赚钱”。在他眼中,乘氢气球打塔并不难,“只要没恐高症就能行”。
两人共同乘坐了那个白色的氢气球。在9月4日那天,地面上两个拽球的人同时松了手,氢气球飘走了。他们曾有过一次逃脱的机会,胡永旭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天没有风。我们两个人就连蹦带跳地往下压。飞到一个树边,离树尖挺近的。我先抓树尖,然后他(指刘成会)顺那个树往下爬。但他一下,就失去平衡,我就飞了。”
这一飞,便飘了三百多公里,也飘上了热搜。万幸的是,胡永旭死里逃生,飘了十余小时后,跳到树上受伤落地,9月6日被搜救人员寻获。
“这个不用教,挺简单个事儿”
两名打塔人此前均无经验,但得到了“山主”李裴林的青睐。
李裴林是山市镇道南村人,在山市镇的林场内承包了百余亩的红松林,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雇用了自带氢气球的刘成会,约定每打满一袋松塔,支付其170元。刘成会则以每天600元雇用胡永旭乘氢气球打塔,再雇两人拽球,日薪200元。
“山主—球老板—打塔人”,这便是打塔行业的普遍雇佣关系。打塔人紧缺,“有的时候是给别家干完了,给我家再干。”李裴林的妻子说,“工资多是多,但有的人不敢上树,这个活儿也挺危险的。”
招工难的背后,是中国松子供需缺口较大的现状。果松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凯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中国每年需求量在10万吨左右,但国内产量只有3万到5万吨,加上从俄罗斯、朝鲜等国家进口,总供应量达到8万吨。据他观察,2022年红松产量更低,估计在2万到3万吨。受气候影响,近3到5年红松每年产量处于平均值以下。
“松子的营养价值高,需求量大,产量却不高。现在国内松子主要的产量还是在红松松子,主要生长在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两个地区,面积比较窄。”一颗红松子能延伸出一条长产业链。松子为初始产品,之后可将松子加工成蛋白粉、松仁油等,还能用松仁油提取卵磷脂等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处于链条最前端的打塔人们模糊地感知着这一产业的趋势与变化。
李裴林的妻子注意到,雇用打塔人的费用年年在涨,前一年还是日均450元。而花大价钱买了氢气球的刘成会只是觉得奇怪,2021年镇上的氢气球没多少,2022年怎么多了许多。
登上氢气球前,刘成会没有接受任何培训,“这个不用教,就是挺简单个事儿”。
首日打塔很顺利,打了十多袋,扣除工人劳务费,盈余虽不算多,但刘成会有信心这个月能赚五六万元,“后边就越来越好打了,等松塔老了以后,只要树一摇它就下来了”。
第二日一早,开工不过一小时,气球飘上了天。
刘成会记得,自己和胡永旭在氢气球上,地面上有八九个人,一些在捡松塔,有两人分别握住两条绳,一个挪动拖拽,一个绑树固定位置,每打完一棵树,他们便会向下喊话,让拽球者移动位置,但有一瞬间,底下负责拽球的两个人同时松了手。
事前是显露了些端倪的。在事发前一天,胡永旭认为两个拽球人不适宜干这活儿,“那时候我就说了,说这俩不大行。他们岁数有点大,不太灵巧”。其姐夫刘金祥也多次向刘成会提出由自己替换,但遭到拒绝。
刘成会事后的解释是,这百来亩松林,一个星期就打得完,这两个拽球人都是李裴林找来的,可以再凑合个五六天,“给他家打完了就算数”。
南方周末记者未能联系到两名拽球人。刘金祥曾在派出所与两人打过照面:“没说什么,就好像说先让当事人备案。”胡永旭出事后,他们没来探望过。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山市镇林业派出所和当地其他公安部门,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空中放气也不管用?
已经有二十多年打塔经验的马涛(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市镇兴起氢气球打塔是在2017年前后,大多数老板使用的都是“凯欣气模”的氢气球。
那个飘走的氢气球同样来自凯欣气模,刘成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花1.8万元购买了这款氢气球,又花了7500元充气,和胡永旭一道将气球拉上山。两人体重分别为110斤、130斤左右,再放块石头上去,配重符合要求。
刘金祥称,凯欣气模老板是山市镇红松林交流群成员,人在沈阳,通过线上方式对接有意向购买者。根据其提供的联系方式,企查查显示号码对应公司为沈阳市凯欣舞台设备经销处,曾用名沈阳市东陵区鸿喜达空飘球加工厂,目前已为注销状态。该公司负责人名为冯翠霞,名下关联企业还包括佛山市鸿喜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显示仍在经营。
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凯欣气模老板电话,均未接通,其微信个性签名标注售卖舞台、灯光架、桁架、拱门、空飘球等物品。刘成会曾在事后与凯欣气模老板通过电话,对方称生意已受到很大影响,“别人也不敢买她的球了,说她的球有问题”。
据公开资料,此前也有乘氢气球打塔飘走事故,或与氢气球应急安全设置有关。
2017年8月,吉林省汪清县一男子乘坐氢气球打松塔,固定气球的绳索被大风吹断,氢气球飞行的地图直线距离超过五十公里。同年9月,吉林省集安市两名农民在准备登筐过程中,一人撤出筐后,气球失控快速升高,被球带走的人就此杳无音信。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靠轻于空气的气体产生升力的气球遇突发情况时,应当有可使球囊放气的装置以保证安全的应急着陆,还要求气球中应有基本设备,包括高度表和升降速度表,还需配置最小可抛放压舱物和一个罗盘。
此规定是在2022年9月1日实施,在此之前,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于2007年3月公布的《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中同样包含上述内容。新规将混合气球纳入适用范围,规定了相应的适航审定要求,并完善了技术性要求和飞行手册要求。
目前使用氢气球打塔缺乏安全操作技术规范。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牡丹江分院森林生态研究中心主任魏彪曾向媒体表示:“用什么样的气球、气球能飞多高、几根绳固定、如何规划路线、如何规范操作流程和从业者资质,这些都需要制定一个安全操作技术规程。”马涛称,自己没有看过氢气球相关使用说明书,厂家会把使用方法告诉购买氢气球的老板,老板再告诉工人。
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部分受访者表示氢气球的球囊放气装置缺乏效用,且并无配置气球中应包含的基本设备。马涛觉得,氢气球吊篮里一般容纳2人,承重方面没有太大质量问题,但氢气球不抗风,一有风就干不了活。
他曾遇到大风吹刮氢气球的危险情况,吊篮里除了作业工具没有其他设备,如果氢气球飘走了,只能拉阀门放气让其下降。“但关键是放气也可能没用,如果飘得太高,风很大的时候,拉开阀门把气球里的气放走,风又会重新灌进气球里,根本降不下来。”
这一点,胡永旭颇有感触。“我们气球飞了不到一分钟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那个安全拉链儿(指救生阀门)拉开,气儿根本放不出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就在气球上给她(指厂家)打电话了,拉链拉下来也不好使,问她那怎么弄,她也没说出来什么。”
对于该氢气球的放气装置是否起到作用,作为氢气球的所有人,刘成会称厂家在电话中给出的自救方式是打开救生阀门,自己已第一时间将阀门打开,球出现下降趋势。
他认为这次事故同氢气球质量无关,就是拽球者不够负责任,“绳子拴好就啥事都没有”。

工人正在氢气球上打塔。 (受访者供图/图)
曾发文严禁氢气球打塔
胡永旭飘走后,氢气球打塔法的安全性再次引发争议。
马涛说,胡永旭出事后,当地林场便禁止使用氢气球打松塔,改用传统人工爬树方式。而据黑龙江媒体报道,这一安全提示的发布时间在胡永旭出事之前,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发出红松种子采收安全提示,明确严禁用氢气球等危险方式进行红松种子采收。
相关安全提示并未在网上查询到。“这个工作提示是我们内部发的。”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据其官微公众号发布,9月6日,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召开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会议指出,正值红松种子采收的关键时期,要教育承包人及雇用人员,备好安全工具,杜绝用氢气球采种。
长期以来,打塔手段比较落后,方法选择较少。
目前规定可行的方式为人工打塔,工具采用前端固定弯钩的长杆。根据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12月发布的《红松天然林球果采摘技术规范》,采摘方法应当是由采摘人员攀爬上树,晃动树枝或将球果打落,地面人员收集装袋。
而实际操作中,乘氢气球是许多打塔人的备选项,甚至首选。用马涛的话说,“爬树危险,氢气球稍微比爬树好一点。”
其他采塔方式大多因现实操作困难未能实施。辽宁省本溪市实验林场的李立夫曾在2018年的论文中提到数种替代人工采集松子的尝试,包括高空摄影无人机、热气球、液压高空操作平台、驯养猴子、以拖拉机带动的球果采摘机,“最终所有设想都以失败而告终”。
杨凯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行业内曾尝试过专门采塔的机械装置,但在林子里移动不方便,相比人工采塔成本更高。而且除了采塔季,其他时间用不上。而多数松林是私人承包,用不起大型机械。“南方地区尚能训练猴子上树采塔,但东北地区没有这种猴子,只能是人工爬树”。
研究者们正在尝试将松树变矮,从源头解决问题。“现在我们要将红松进行矮化密植,变为果用红松,进行园艺化管理。让树结顶,矮化一些,不让它长那么高,这样人不用上树,拿杆儿一打就下来,就像苹果一样。”杨凯称,红松产量与树种有关,树变矮也不会减少产量。
据悉,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组织有关单位和企业,组成果松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研究红松短周期果林和红松矮化经营果林,目前已有审定良种超过20个,在东北三省推广。“要全部变成果用红松,高枝嫁接要五年以上,栽小苗儿应该是在十年以上。”
“实施具体管理的是承包人”
在此之前,耸立在打塔人面前的仍是高约25米的松林。
打塔事故频发。有关安全保障“只能是自身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林子比较多,采摘的人也比较多,我们作为监管部门,其实也做过安全培训了。具体到现场监督,我们也都有安全监督员。但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山比较大,不可能每一处都配备安全监督员。”
更多的安全保障,倚赖各红松林承包人提供。
胡永旭出事后,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召开的相关安全会议指出,各单位和局机关相关部门领导要工作下沉,亲自到承包人家中或山场进行巡查,督导检查各项工作。雇用人员需参加意外人身保险,否则发生问题由承包人和被雇人员自己负责。
前述工作人员认为:“我们是和承包红松林的承包人签订了合同的,发生一系列安全事件,其实都是由承包人去管理的,实施具体管理的是他们。”
被问及合同中是否涉及安全管理相关内容时,李裴林并未正面回应,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必看承包合同,自己雇用的是氢气球老板刘成会,是刘雇用了其余几名打塔人,“他给他们开支,跟我没关系”。
李裴林的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氢气球飞走后,丈夫吓坏了,“脸回来就煞白,吓得够呛,咱没经历过这个事儿”。
李家以承包红松林为主要收入来源。作为林场职工,他们会通过抽签的形式决定红松林的承包面积。李裴林承包过两次,第一轮抽过四十余亩,合同期限10年,这一次,他抽中的是三十余亩,期限5年,“又从别人手里买了点儿,买了三四个号,才凑了一百亩”。
他们决定扩大规模,是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承包机会,李裴林已经买断工龄不再上班,到退休年龄后便不再有资格参与抽签,也难以到外地打工谋生,“都五十多岁了,不好找活儿。”其妻说,他们原指望着雇人打塔能赚点钱,但出事儿之后,招工更难了。
此外,他们有为打塔工人买保险:“松子采集险是近些年才有的”——因采松子摔伤致死事故频发,这一险种应需而生。
一位售卖松塔采摘专项险种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松子采集险都是按月保的,通常只持续一两个月,保额30万至100万不等,“上树都是高危险行业,打松塔的都买”。但他售卖的险种“管的是爬树”,“保不了”氢气球作业。
是否购买保险取决于“老板”的负责程度。上述保险从业者提到,在一些林区,“低于60万的保险,老板不让上树”。但如果老板不购买,一些打塔人没有购买保险意识,亦不清楚雇主是否为自己完成这一保障。
胡永旭的保险是李裴林购买的,1000元。保单显示对应险种为气球采摘,承担采摘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最高可获60万元赔付。
这个身上有着大片黑紫色瘀斑的男人仍在牡丹江林业中心医院养伤,经诊断,伤情包括肋骨骨折、创伤性血胸、脾破裂、肺挫伤以及腹部闭合性损伤和多处软组织损伤等,其姐夫刘金祥对此忧心忡忡,治病要钱,受伤耽误挣钱,这些都是要操心的。目前保险尚未赔付,“保险公司现在没给,等出院之后才给的”。
他收到了刘成会支付的2000元酬劳,和李裴林给的2.8万元医药费,但刘金祥认为这些并不足够,“我小舅子药费现在没人拿,没人管,医院催费了,我给那个老板打电话,老板不拿,看不了病了”。
各方因经济赔偿问题产生了不小的纠纷。“正常来说应该是球老板(指刘成会)拿钱,医药费是我交着呢,按人道主义我做了。”李裴林说,这两天松塔没打完,雇不到打塔人,“都知道我山里球跑了,给多少钱都没人干,我损失老大了”。
刘成会也觉得自己亏大了,原本能用五六年的新气球下落不明,自身也受伤了,还要被工人家属追着索要赔偿。他自顾不暇,决定先返乡养伤,“我气球飞了,搞得没有钱了,看病的钱都没有了”。
但被问及今后是否还会再次打塔,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去肯定得去,但不会到这个地方。”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彭乐怡 胡世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