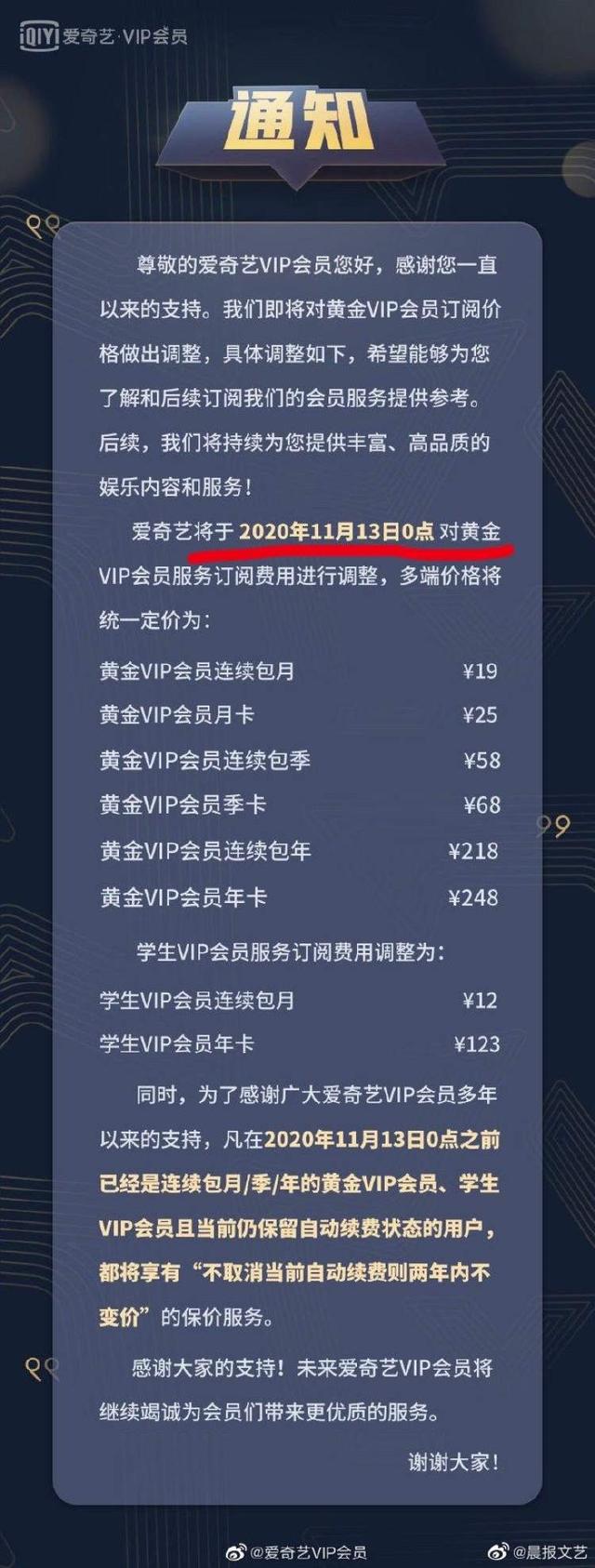我是喜欢海的,准确地说是海边。在海洋深处,面对起伏巨大的深邃幽蓝,心中难免泛起无助的恐惧和面对深渊的噬人寒意。而来到海边却是截然不同的,海边是沙滩,是滩涂,也是安全和收获。这里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惊喜,几只横爬的小蟹或者几枚美丽的贝壳,甚至对于年幼时的我非常神奇的——住在螺中的寄居蟹,不一而足。

2017年夏,我又来到了海边,带着老婆和儿子,依然随着母亲。海水蔚蓝,阳光充足,让我短袖外的手臂“着色”非常明显。天空万里无云,没有台风,但是繁星点点的夜晚或者浸润晨曦暖阳的早间,在咸湿的海风吹拂下,渔民们修轮船的嘈杂声让回忆起了那个八十年代的海边和那座台风中的小岛。

那时的我很年幼,一如我懵懂中的儿子。我的父母那时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与当时来说,绝对的小布尔乔亚式新青年。跨着双镜头的苹果,哦!不对是友谊牌相机,并且自己DIY了个暗房。当然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只能有很多DIY的产品。
旅游和摄影是他们共同的爱好。幼时的我去的名山大川并不多,但却跟着去了不少家乡周围的好风光。一个相机,一个或两个绿色或蓝灰的帆布包,于现在而言绝对属于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小小的我并不知道是不是说走就走,反正我跟着去了好些地方,比如那次的小岛。
那个小岛叫北麂,在温州的辖境内。对于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生活在温州瑞安的我们也是一次长途的旅行了。我们是坐着木壳的轮船出海的,蓝色的油漆和“突突突”的柴油机一如那个年代大部分海边的轮船一样。晕船与否我已经不记得了,甚至忘记了有否看见盘旋的海鸥和海面跃起的鱼儿,我只记得我是快乐的……
扫兴的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台风很快来了。请饶恕我完全忘记了台风前我们可能的愉快、兴奋,总归应该是有吹吹海风,抓抓螃蟹,挖挖贝壳之类的,于是只好从台风来后讲起了。

当时的船都很小,只是些漆着蓝油漆的木壳船。台风中我们被关在岛上了,没有出海回程的轮船,当然也没有了渔获。那时我们寄住在渔民的家中,当时并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几星级酒店。父亲总是早早出去打听回程船的消息,但连天的失望而归。台风天中的小朋友就更不能跑到房子外面了,所以我只记得了我跟母亲顿顿吃腌制海螺度日的时光——没有其他渔获了,只有腌海螺,而且品种单一。
螺肉很难挖,母亲的发夹却是那么的神奇,总能挖出我所辛苦而不得的螺肉,于是我依然总是快乐,我并不理解父亲忧愁的眼神。(台风会把油毛毡屋顶的工棚刮破,让父亲小厂子的机器变成废品)。现在的我依然爱吃螺,只是当时而言不能出去户外让我觉得好生无聊,如果小小的我脑子里有无聊这个词汇的话。百无聊赖的我在餐桌边的条櫈上把螺壳玩出了很多花样,我甚至能发现不同花色和大小的螺壳能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三天后,风小了,父亲终于帮一家人找到了可以回陆地的船。我们喜悦的回到大陆这边的码头,回家的路上雨依然很大,风依然时时的把雨伞掀起,把水倒在我们身上,在离家只有大约一里路的地方,雨伞经不住大风的摧残终于歇菜了。等了许久雨依然越下越大,父亲看着躲在毛线市场棚下,已经淋成落汤鸡的一家人耐不住母亲的劝阻冲进的雨中……大约二十分钟后,爸爸回来了。那时小小的我当然不知道二十分钟的概念,只知道过去了好久好久,只记得好久以后在暴雨中爸爸回来了,回来时爸爸的白衬衫已经变成了一件肉色的紧身衣,湿漉漉的搭在身上,那一刻我觉得好感动。当然这是后来才学习到的一个词汇,三岁的我并不能用什么准确词汇描述我的所思所想,所能记忆的只有模糊的片断和情绪,包括忘记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饥饿!在父亲从家里拿来的雨伞庇护下我们终于回到了家。在换完干燥衣服后,饥饿这一强烈的感觉从一家人的胃里强烈地传递而出。遍寻家中的粮食,只一块旅行肥皂大的黄油和几片面包。这是父母的友人很久前赠送的礼物。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叫黄油,只知道怎么面包刮上这个奇怪的东西吃起来那么的香甜。当时的黄油是绝对的奢侈品,以至于我长大后才再次确认到原来那时吃的是黄油抹面包。
三岁的儿子在沙滩上嬉戏着,看着他,我知道他是快乐的,一如那时的父亲看着我。这份快乐会带给他很多的回忆。意识的,潜意识的,苦涩的,甜美的,林林总总。即便在幼小的心中不能精确地用词汇描述,就像早逝的父亲带给我的。
人经常寻找记忆中的味道,却总是分不清寻找的是那种味道还是那份记忆,至少我再次吃到黄油面包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只是这个啊。又或者长大了后在轻松挖出海螺肉时发现原来是这样的简单啊。
它们就是这么的简单,只是发现不了,找不见了而已。
只是,找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