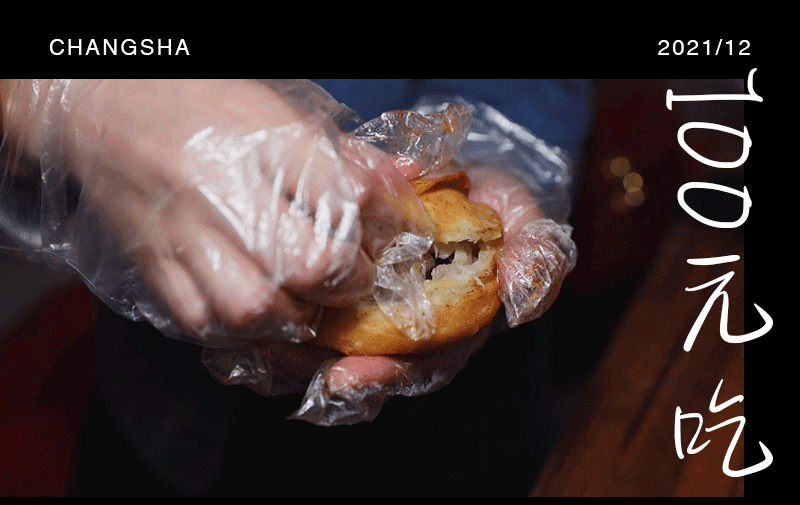登上2002年第5期《内蒙古画报》封面的敖德巴拉

年轻时的敖德巴拉

郭丹和姥姥白乔氏、养母白质文、哥哥郭贵州合影

1982年,郭丹和养母白质文在沈阳北陵公园留影

1976年郭丹在满洲里市第二中学就读时与同学合影

都贵玛“中国十杰母亲”等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国家的孩子”们看望原呼伦贝尔盟保育员莫德格额吉

“国家的孩子”们和照顾他们的保育员莫德格额吉合影

“国家的孩子”们向莫德格额吉汇报取得的成绩
第四章 永生难忘
“天之苍,地之茫,天地苍茫有爹娘。走多远,回头望,那是故乡,永生不能忘!”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主题曲《永生难忘》唱出了所有“国家的孩子”的心声。
2018年春天,在短短两天和来自内蒙古各市、盟、旗的近100个“国家的孩子”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的积极向上、坚韧顽强,深深体会到他们那种对于家乡和生身父母的怀念。因为在他们的言谈之中,表现更多的是对草原的感恩,对草原养父母博大胸怀的赞美和对他们的培养、教育的感激,也包含着对家乡的向往和对生身父母的挂念。他们说:“养育之恩要报答,生育之苦也不能忘记。”
这并不是我的思维有多么敏感,也不是我的观察能力有多么细微,那是因为我的妻子也是一位当年来自南方的“国家的孩子”。
虽然妻子很少提起南方、提起家乡,甚至从来不提生身父母,但是我能感受到她对家乡的向往和对生身父母的牵挂。
其实在我俩刚认识时,我就对她的身世有所了解,虽然并不是十分详细,但也知道她是抱养的。那时有人对我母亲说:“您家儿子的对象是一个朝鲜孤儿,也有人说她是越南孩子。”
为了弄清楚未来儿媳妇的真实身世,母亲找到了当时曾经负责接收南方孤儿的邻居。这个邻居叫张边一,是扎赉诺尔矿区中蒙医院的院长,1961年曾经担任接收这批“国家的孩子”的医疗小组组长。
张边一院长对我母亲说:“白质文老师的女儿我知道,好像是叫郭丹,当年她也就两三个月大,是最小的几个孩子之一,是我为这个孩子检查的身体。”
当时,张边一院长十分详细地把当年的情况告诉了我母亲,可是母亲并未跟我说,怕儿媳妇想起伤心事,她也不允许家人谈起孤儿的话题。
很多年后,当我妻子郭丹和十几位当年来满洲里的“国家的孩子”想要了解当年的情况时,张边一院长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他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而此时,我母亲对这件事情的记忆也是不太完整,她告诉我们:“当年张边一院长对我讲过,所有孩子都要在托儿所住上一段时间。因此,托儿所也扩大了规模,招收了临时保育员。来的时候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小牌子,那上面有编号和他们的生日,这些信息是和交接记录相符的。从接收到被领养,孩子们要经过多次身体检查,而且都是有详细记载的,符合领养要求了才能让养父母领回家去。在领养前,孩子们的所有费用都是由政府承担的,领养后孩子白天也可以送到托儿所来,晚上由养父母接回家,但是需要交托费,所以很多孩子被领养后就不再回托儿所了。”
据当年帮助白质文夫妇把孩子抱回家的付桂芳大姐说:“那时郭丹身上确实是有一个小牌子,她穿的棉袄棉裤是到托儿所后做的,有点大,一件蓝色的金丝绒披风是从南方来时穿的。”
1961年3月,我妻子和其他南方孤儿一起跨越长江,经过长时间的辗转来到了呼伦贝尔草原,来到了边城满洲里,她和其他25个孩子一起被送到了当时的扎赉诺尔矿区。
由于当时来的这些孩子身体条件都比较差,所以先在扎赉诺尔矿区托儿所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和恢复,并且接受了严格的医疗检查,对每个孩子的情况都进行了详细记录,当孩子们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才先后被养父母领回家中。
我爱人的养父郭景元在留给我爱人的遗书上写道:“这些孩子刚来时有的非常小,而且刚到草原饮食不太习惯,喝牛奶会拉肚子。所以,当时在扎赉诺尔矿区托儿所工作的哺乳期妇女都给孩子们喂过奶,有的甚至早晨不让自己的孩子吃奶,为的是到托儿所让这些可怜的孩子多吃一口。”
我妻子也曾经和我说过,她就吃过几乎所有哺乳期阿姨的奶水。然而几十年后,当这些孩子看望当年的刘秋萍阿姨提起这件事时,刘秋萍阿姨坦然地说:“那时我的奶水多,不吃也浪费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那个时候缺衣少食,孩子的奶水是不够吃的,把奶水给了别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就需要用其它食物来补充。
我妻子应该是很幸运的,她被一对夫妇领养,养父是当时扎赉诺尔煤矿的一个中层干部,养母是扎赉诺尔矿区一所小学的人民教师,当年担任扎赉诺尔矿区托儿所所长。他们家有固定的收入,虽然已经有一个男孩儿,但是他们希望再领养一个女儿,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完全有这个能力。
养父母把这个女儿当成了掌上明珠,事先为她准备好了衣服、被褥、奶粉,还托朋友为她每天订一瓶牛奶。要知道,扎赉诺尔是一个矿区,只有一个国营养牛场为乳品厂提供原料,订一瓶牛奶并不容易。
在我妻子不到两周岁的时候,一次高烧后她的右腿开始出现肌肉萎缩,影响到了走路,医院确诊为小儿麻痹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脊髓灰质炎。这是一种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主要有发热、咽痛和肢体疼痛,部分病人可发生迟缓性麻痹。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很多孩子都患上了这种病,因为没能及时治疗,有些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为了治好女儿的病,养父母带着郭丹四处求医问药,并且不辞辛苦地用各种偏方治疗,虽然见到了效果,但是没有完全治好。他们不甘心,后来听人说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军208医院专门治疗小儿麻痹症,效果很好。于是,他们就带着女儿来到了长春市。
果然来这里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很多,这里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埋线穿刺疗法,不能使用麻药,非常疼,而且还需要连续做三次,每做完一次需要休息15天再做第二次。经过两次穿刺治疗后,郭丹对这种治疗产生了恐惧感,第三次因为持续高烧没能继续治疗,他们只好返回扎赉诺尔。幸运的是这次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郭丹并没有留下太大的后遗症。
1967年,平静幸福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一场苦难悄悄地降临在了我妻子郭丹的身上。
一天,她家里来了十几位陌生人,他们翻箱倒柜,家里被弄得乱七八糟,然后这些人强行带走了她的养母。后来听别人议论,说她的养母是国民党特务。养母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她开始和那些人争辩,没想到换来的是更恶毒的语言:“你只不过是个要来的野孩子、外来种、小高丽棒子、越南来的没人要的孩子……”
虽然她当时还不知道这些语言的含义,但从那些人的表情中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话。她没有能力反抗,只有默默忍受。心灵上那块伤疤在这种情况下被无情揭开,会更加的痛。
不久养父也被带走,罪名同样莫名其妙,郭丹和哥哥小小年纪就离开了父母,没有了父母的呵护。
当时家里只有80多岁的姥姥和两个孩子作伴,姥姥做好饭后需要他们分别给养父母送去。郭丹那时只有六七岁,经常会把稀饭弄得满身都是。
养母每天除了反省、交代问题,还要早晚打扫全校所有教室。还没上学的郭丹十分懂事,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到学校帮助母亲打扫教室,委屈了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
落实政策后的养父曾经说:“是我女儿救了我。”原来,那时养父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在一个大雪天一个人偷偷出去,准备就此结束生命。
那天,郭丹似乎感到了什么,养父走在前面,她便悄悄地跟在后面,她跟着养父走了很远,小脸冻得通红,养父无意间回过头来看到了跟在后面的女儿。瘦弱的女儿艰难地在雪地里走着,养父停了下来,看到可怜的女儿那冻得冰凉的小手和那红红的脸蛋儿,终于忍不住抱着女儿哭了。他知道女儿离不开他,他不能就这样离去,他要把女儿抚养长大。
1977年高中毕业后,郭丹到学校当了代课老师。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养母把她送到南方自己的哥哥那里,郭丹的表姐还给她找到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当时她标准的普通话很受领导的重视和学生的欢迎。1979年,养母落实政策后退休,郭丹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草原接养母的班,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此,她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38年。
在这38年当中,她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草原人民养大的,她要用全部的精力来报答草原人民,报答她的养父母。她为草原煤城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生,多次被评为盟、市、区级劳动模范,优秀教师,教改能手。1997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后,她负责社区关工委的工作。
1981年的一天,郭丹对我说:“和我一起从南方来的一位姓尹的大哥找我了,我们要去寻亲。”我从她的话中感到了一种伤感。我告诉她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支持。
我利用从事新闻工作的优势帮助他们收集素材,制作了寻亲的影像资料。他们的豁达、开朗、乐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天我应邀参加了一次他们的聚会,席间他们一起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我曾无数次听过,只有这一次真正打动了我。虽然他们的歌声并不优美,但是他们唱得非常动情,感情发自内心,歌声伴着哭声,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爱人说的尹大哥是和我爱人一批来满洲里的52个孩子之一,他比我爱人大一岁,当年是在满洲里火车站被养父母抱走的。他的养母没有工作,养父是一名铁路工人。
开始的时候,养父母也是把他视如珍宝,特别是奶奶更是视他为掌上明珠。6岁那年,养父母离了婚,养母没有能力抚养他,从此他由养父一个人抚养。后来养父再婚,娶了一个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女人,他只好和奶奶从满洲里道南搬到了道北,靠养父每个月给的30元钱抚养费生活。在当时,30元钱的抚养费应该不少,可是每天养父还要到他们的住处喝酒吃饭,这30元钱的抚养费中包括养父每个月12.6元的酒钱,剩下的钱买完供应的米、面、油、肉也就没有多少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和奶奶去满洲里西山捡粪、刨白菜根子取暖、做饭,为的是能省下几个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