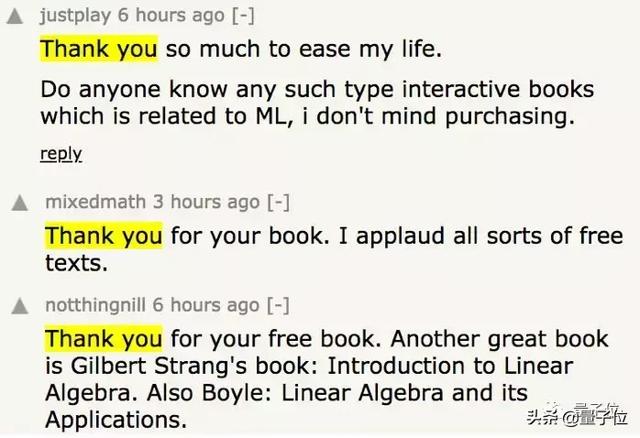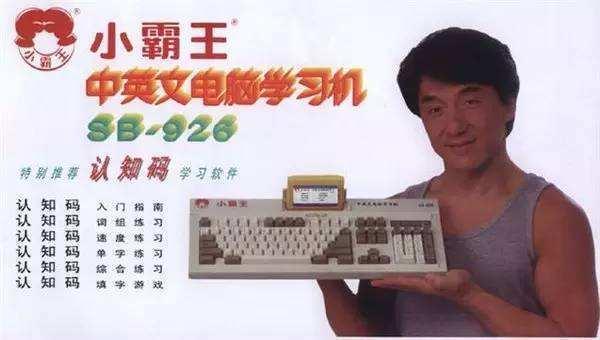渐行渐远的故乡故乡,在梦里,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想念渐行渐远的故乡 渐行渐远的故乡?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想念渐行渐远的故乡 渐行渐远的故乡
渐行渐远的故乡
故乡,在梦里
模模糊糊却又清晰可辩
于是,我才盼望黑夜又害怕黑夜
故乡,在思念里
总想忘怀却更索怀
于是,我才希望沉静却不敢沉静
故乡,在信里
沾着老父的血和老母的泪
于是,我才眺望小路却不敢踏上小路
故乡在云里
虚无飘渺,随风而散
故乡在月里
美丽动人却可亲不可近
故乡在远方
在游子的心里
这首《故乡》是我第一首思乡的诗。当时,我是深圳市武警支队驻深圳大亚湾核电站武警大队部副连职管理员。1990年9月19日黄昏,我正在大队部战备值班,看着通信员给各位战友派信。忽然诗潮袭来,提笔写下了这份感伤。
我十四那年的七月高中毕业。当时是没有六年级、初三、高三的,因而虽说是高中毕业,实则是九年义务教育,后来国家还不承认这个高中学历。毕业当年的夏收夏种时节,或许是生产队见我是几个高中生里面学习成绩好,又或是看在我爸是个修理拖拉机的能手的份上就叫我当了拖拉机手。由于我尚未满十六岁不能正式登记为主劳动力,所以我只能拿成年人的一半工分。到了九月,我在老师的要求下回校复读准备次年再参加高考,但由于自知没有读书的天份加上其它原因,我上了不到一个月的学就彻底地离开了学校又回生产队当了拖拉机手……当年冬天,伯父叫我不要在生产队混了,带我去了广州东郊一个叫车陂的地方的一个大山里,在一个干亲戚开的砖窑打工。自此,我开始浪迹天涯过了好几年的农民工生活。十八岁那年参军入伍正式离开了家乡……家乡不仅变成了故乡,而且在我的生命里已渐行渐远。时至今日,我已经认不出她,她也认不得我了。
离家青头归鬓霜,故乡已非旧模样;
童音未变乡音改,误认错步到异乡;
邻人八九不相识,今日方懂贺知章。
我的故乡是珠江的西江支流冲积而成的大南围。从空中鸟瞰或在地图上察看,大南围实则似一个橄榄浮在水面。因而叫大榄围更确切,不知是不是原来真的是叫大榄围,后来是因口音误传变成的大南围了。大南围分上南、中南、下南,是历经千年数代人的整治,成为一个四季飘香的沙田水乡。有一部叫《香飘四季》的长篇小说,就像是描写我家乡的风情风貌一样的。我的家乡河网纵横,土地肥沃。除了台风带来涝灾、洪水会造成缺堤之外,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因此,香蕉、荔枝、龙眼、桃子、番石榴、枇杷等等岭南佳果随处可见,夏秋两季稻浪翻滚,冬春时节甘蔗甜美。猪满圈、鸡鸭满栏。河中鱼虾成群……
可惜这种景象现在已不再了。我的家乡建起了工业园区,已难觅儿时的模样。村人除了土地分红外,还有出租屋的收入等等,已经不再是脸朝黑土背朝天地觅生活了。村里住了许多外乡客,南腔北调都有,就象是“联合国”一样。我自己倒成了异乡人了。村人的生活富足了,这是儿时想都想不出来的好生活。但是,那些小朋友却小小年纪就辍学了,整天只知道玩乐,父母们不懂教,也教不了他们。唉!令人揪心啊!我偶回故乡,一时感慨,写了几首小诗:
(一)
离家日久归故乡,良田变作旧厂房。
龙眼荔枝无踪影,那里能闻桃花香。
虾爽蚌肥儿时事,河水如墨无鸭荡。
蔗甜稻黄不再有,蛙鸣鸟叫梦里响。
村人八九不相识,南腔北调似异乡。
(二)
农夫不作农耕事,度日如年坐待币;
车子票子子子有,大富不足小康余。
QQ麻将游戏机,日上三杆始睡时;
张家长来李家短,杯中酒尽意不知。
可怜妹弟不读书,误认财富得来易;
书到用时方恨少,待尔明时悔恨迟。
(三)
故乡归来伤感多,物换星移匆匆过;
儿时常思衣食足,得尝所愿又如何?
说实在话,我对故乡的记忆大多是停留在十八岁之前。小时候,家家户都养一头猪、一群鸡、鸭、鹅。放学后,几个小伙伴背上小竹篓,一起到广阔的田野里,一边嬉戏一边割喂猪、鸡、鸭、鹅的草。或者是早上将鸡挑到收割后的稻田里放养,晚上待鸡回笼后又挑回家;或将鸭、鹅放在田野里吃草什么的,我们就追追打打……那时治安很好,家畜随便放养都不会丢。村里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民风纯朴。
土地肥沃加上村民勤劳,理应生活富饶,但我的童年印记却是十分清苦,经常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成年后,我将我们的贫穷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大环境不好,生产力极度低下,经济流通不畅。如水稻一年两造的总亩产只不过是600到700斤左右,而且所生产的粮食大部分是当公粮上交了。每到农历五、六月份青黄不接(即水稻当熟未熟)的时候,我们每天只能吃一顿稀得再不能稀的稀饭,或以番薯(地瓜)、芋头、鬼葛(木薯。因其分泌物含有锖化钾毒素,容易误伤人命,所以村人称之鬼葛。吃此物时要先将其剥皮、抽筋、斩段,用水泡几小时,再放小许生姜、一把米或小白菜同煮,可确保安全)之类的淀粉类食物为主食,甚至是用芭蕉或芭蕉树头等植物的茎充饥。现在,此类东西成为餐桌上难得的座上宾。酒足菜肥之时吃此物的确不错。但当你连续一个星期甚至是一两个月仅吃这种东西且没盐没油的,那滋味就不一样。尝试一下,看能持否?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挺过来的。我记得村里有位叫“恩伯”的阿伯对着我叹了口气说:“让我放开肚皮吃顿白饭(即没有菜伴吃的白米饭)。立即叫我死都愿意了。”唉!种米的人没米吃,那真是悲哀!因此,我觉得“南袁北李”真伟大,提高了粮食产量,让种粮人能吃饱饭,无论奖他们什么都不为过。
也许是饿怕了。后来能放开肚皮吃饭后,我每餐都吃几大碗,结果吃成大胖子,再一点一点地节食减重。唉!人真是瞎折腾!当年,自家养的猪一年才长成120斤左右(刚好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相当,所以又称未成年人“不够称”)也要先送去食品站(食品站收猪要120斤以上才收,而120斤以上的猪虽然吃得多,但长得快,农民却要等钱用,就把猪给卖了。当年的猪靠吃青草、谷糠之类的食物,很难养到120斤。我每天都要割一篓喂猪或其它禽畜的草才能吃晚饭。当年的猪和其它禽畜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现在已没有人干这种经济效益不高蠢事了。)食品站无偿地收去75%,剩余的还要委托他们的人帮忙卖“高价”,又索取一点(食品站拿我们的猪肉卖牌价,钱归公社。牌价肉很便宜,但要凭票供应,而这些票子只能是住在镇上不用种粮而能食饱饭的人才有,我们称他们为吃国家粮的人。实质上,他们是抢劫了我们的劳动果实。我小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当工人,做城里人,这实则是我最原始的追求。)因此,一头猪养一年才能得到20到30元,这已是家里最大一笔的收入。除了买仔猪的钱,实在是……那些鸡鸭什么的也要上缴一部份给食品站后才能在圩日(即每月逢七之日的集市)拿去卖,换回一些盐,或按布票扯几尺布[当年是按年龄分布票。好象是:10岁以下的每年3尺6寸,11岁至16岁(16岁就属成年,可以当生产队的壮劳力)是4尺8寸,成年人是1丈2尺。所以,也用3尺6或4尺8来替小孩的年龄。]小时候我没有穿过新衣服,不是父母不疼爱,实在是先将有限的布料集中起来给去劳动的成年人做衣服,再给年长的子女。这样一个一个往下传。故此,我只能永远都穿姐、兄的旧衣服,到弟妹时情况有好转了)当年,经济环境不好,那些鸡鸭也仅能卖3、2块钱一只,只能是镇上的人才有钱吃,或者有些农村人做红白事时才买(我们只懂养鸡,难尝鸡肉味)农村人仅靠这些家禽畜来维持日常开支,所以,虽然很想吃肉,也只能忍痛将肉拿到市场换些血汗钱、救命钱。
当年,河里很多鱼虾,但连捕捞的工具都没钱置办,甚至饿得连拉网的力都没有,那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鱼虾。有时候为了能吃点肉,我天蒙蒙亮就到生产队的鱼塘去巡视,看有没有死鱼……现在,看到这些东西你会掩鼻而过,当年真是好东西啊!现在稍肥一点的肉都不吃,当年能有一块“猪糕(即猪的肥油)蒸糖”,那真是天下美味。那时村里有句顺口溜:猪糕蒸糖,食死志祥(志祥是我们村唯一的地主。这地主也和我们一样住稻杆搭的房,我们叫它茅寮。只是他家的茅寮比我们多几根杉树做顶、做梁、做撑等等而已。所以。在那斗地主的年代,我没见过志祥挨斗。我觉得他很和善,不象书上讲的地主那样凶恶。
到了七十年代,由于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鸡鸭都要限养,连那三分自留地都只能种一些自用的瓜菜,能卖钱的经济作物都严禁了,那生活就更贫苦了。说起那自留地,我现在还经常在梦里看到自己挑着两桶粪便,颤动着走过那条近三十米的独木桥。那是我小时候经常重复去做的一件事。
当年农村贫困(包括现在某些农村人贫困)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多生孩子。我觉得:夫妻加一子一女是最完美家庭。一个家庭超过三个孩子就负担太重了。想当年,一家子生近十个小孩子,等于妻子只能生孩子做家务,那还有什么时间来工作挣钱。家庭只靠父亲去工作维持生计,加上当年的经济活动并不活跃,甚至是空白的。靠天吃饭,那有不贫困之理。以当年的环境条件,生那么多孩子,不要讲教育,就是能让他们存活就是一种奇迹,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也挺佩服这些父母的。可惜,他们结婚后只能为儿女辛劳,没有那一天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而他们的子女也只能重复着他们的生活,甚至会更贫困。因为,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人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只能与现代文明的差距越拉越远。国家的计生政策当然是压抑了人的某些欲望,但也把我们这代人从父辈的那种原始的愚味中拯救出来,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现代文明生活。
说到计划生育,我就想起前段时间回乡时遇到一个邻家姐姐----华姐所引发的感慨。华姐是我小时候的邻家同姓姐姐。她妈妈是村中的赤脚医生,她弟是我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她爸爸或许我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很早就不在人世,至少我没有他的任何的印象。
华姐只有初小文化,长得并不漂亮(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很有青春气息,挺贤惠的。华姐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演员,这也许得益于她妈妈是村医的原故。虽然唱歌跳舞都是挣工分,但唱歌跳舞总比下田插秧舒服。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因此,虽然大队文艺宣传队演戏并不好看,没有多少文艺欣赏价值,但凡有演出都很“爆棚”的。我们这些小孩子肯定是“粉丝”,连晚饭都不吃就霸个头位等着开铹。
华姐演了许多戏,其中三个舞台形象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个是扮演和孩儿争着为革命队伍送情报的母亲;一个是扮演新农村的女拖拉机手。印象最深刻的是扮演一个受“多子多福”思想影响而多生育的贫困农妇。这个类似话剧又似小品的节目中的某些唱词,至今我仍记得:“一早起身家务忙,不知做得那一样……喂得猪来忘记了鸭……顾得阿大阿细又漏了阿二和阿三……”台上的华姐形容枯槁,污秽不堪。这位农妇为了生育和照顾家庭,无法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能靠丈夫一个挣工分养妻活儿,生活陷入无边的困境。结果,丈夫为了生活竟然偷盗,被人唾骂。他们感慨地说:“这些都是多子多福封建思想惹的祸啊!”这是我最早接受计划生育的教育,少生优生的观念深深扎在我的心里。
华姐的丈夫叫章哥,是大队的拖拉机手。章哥是我伯父的干儿子,也是我父亲的徒弟。华姐和章哥很早就恋爱了。章哥参军后,华姐怕他受苦,经常寄零用钱给他。后来,我当兵后才知道部队并不是想象中的苦,我有些战友还将津贴节省下来寄回家。我也从战友身上学会节约,从不要家里寄钱、物。由此可见,华姐待章哥真的无话可挑。章哥退伍后进了派出所工作,他们结了婚。不久,我也离乡远行。偶尔回家也会与华姐擦肩而过,但不会了解她的生活等近况。
伯父去世,我不见章哥来尽孝,倒是见到华姐忙前忙后。从乡人的口中知道章哥工作、生活不如意,经常酏酒,早已不成样子了。我不知道章哥到底遇到什么挫折,但作为一名经过军旅锻炼的人,堕落成这样,我就有点瞧不起他,所以就没有去详细了解他的情况。华姐的样子与当年台上的形象有点相似,只是干净利索一些,唯一不变的仍是整天笑微微的。我们有缘一起同台吃饭。从她们闲谈中知道华姐为了“追个儿子”,竟然生育了五个女儿,其中两个送给别人抚养。这使我十分震惊。不要说我们这些公职人员,就算是我们村里的同龄人也没有见过如此疯狂的,许多有钱人家也不会生育那么多小孩子了。看着昔日台上教人要少生优生的华姐,如今变成的传宗接待的生仔机器,我唯有摇头叹息。为了所谓的香火而累及一生,值得吗?
其实,人死后归于土,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是否得到香火又有谁知晓呢?世上痛爱孩子的父母千千万万,但孝顺的儿子有几个,包括我在内也都是没有很好地尽孝。生儿育女,延续族类是每个人的责任,但事要适可而止,顺其自然,切莫强求。象华姐那样为了香火而付出的牺牲,我觉得太不值得了。
人啊!活在当下是实实在在的,身后事身后了,一切随缘吧!别为了一些虚无飘渺的将来而放弃现实生活。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故乡渐行渐远……渐渐变成了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