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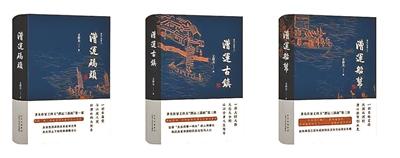

主题:王梓夫“漕运三部曲”新书发布会
时间:2021年5月16日14:30
地点:东城区第一图书馆
嘉宾:王梓夫 作家
解玺璋 学者、文化批评家
主持:侯磊 《北京文学》杂志编辑
主办: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壹
以漕运和运河为主题
注定是一部史诗之作
侯磊:今天的主题是长篇小说“漕运三部曲”——《漕运码头》《漕运古镇》《漕运船帮》。“漕运”这个词很古,是清朝三个国家垄断行业——漕运、河道、盐运之一。它们单走一脉,漕运总督从一品,不受六部管辖。它有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整个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古老的运河,貌似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和我们很近,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这是在北京,北京的水系都是相通的。没有古老运河,我们的祖上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也就没有北京城的今天。以漕运和运河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注定是一部史诗之作。
今天两位嘉宾,作家王梓夫老师是北京通州马驹桥人。解玺璋老师是著名记者和编辑,文化评论家,对北京地方文化也很熟悉。
首先请王老师谈一谈跟漕运文化的关系,为什么要写漕运?
王梓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住运河边上,每天倒垃圾要往河滩里倒,上厕所要到河滩旁边的厕所。那时运河里面流的水都是黢黑黢黑、黏稠的,每天晚上我们睡觉都要关窗户,否则臭气会飘进屋子里。那么一条水沟,名字却非常吸引人,叫“京杭大运河”,通州是它的北端头,旧时漕运码头。我经常坐在运河边上想,从小听到的都是老一辈人讲运河的辉煌、两岸的繁华,运河人可歌可泣的故事,没有人知道这条小水沟当年是怎样的历史,好像过去辉煌都被岁月风尘淹没了。我就有一种创作冲动,要恢复运河往日繁华。
我当年走向文坛,写的都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当时这个领域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浩然,一个是刘绍棠。我20岁那年认识浩然,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一起创作过一部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当年还有一定的反响。刘绍棠更不用说,刘绍棠就是通州人,当年他右派帽子还没摘的时候,有一次我拉他到我家喝酒,从早上十点钟喝到晚上十点钟。这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我们这代人特别幸运地赶上了新时期文学,历史给了我们这么一次伟大的机遇,我们非常荣幸地走向文坛、走向创作,而且很快从事专业创作。当时搞得非常红火的就是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刘绍棠把我和刘锦云比喻成“乡土文学的两架僚机”——他是主机,我们是僚机,这是在青岛一个很大的农村题材座谈会上他提出的。但是我们俩人都不大愿意当僚机,不大愿意走他和浩然的老路。我三十多岁才考虑自己的文学主题是什么,我也像刘绍棠一样,把目光瞄准大运河,也要写大运河。但是我不能像他那样写现实的大运河,我把目光转向大运河的历史,转向大运河最主要的功能漕运。
侯磊:在座的年轻读者可能很难想象浩然和刘绍棠当年的影响力,浩然当过《北京文学》的主编,代表作《金光大道》《艳阳天》。
王梓夫:当年刘绍棠是神童作家,神到什么程度?他高中一年级发表的作品,被收在高中二年级的课本里。高中二年级要讲刘绍棠的作品,主题思想、段落分析。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
侯磊:而且他20岁上下就出了五本书,拿五本书的稿费在西城区光明胡同(西什库对面)买了一个四合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别天才的一个人,才思敏捷。1936年出生,可惜1997年去世了。
贰
既写了清代的上层社会官场
又写了清代的民间社会
侯磊:“漕运三部曲”,是王老师给我们建构了一个与运河相关的,整个清代从朝野到民间的世界。运河和漕运是这里面的一个视角或者线索,是一根线把这些都串联起来。我大致说一下书的架构是怎么回事。
第一本《漕运码头》,写的是道光年间的事。道光皇帝要治理漕运积累的弊病,派钦差大臣爱新觉罗·铁麟查河道漕运的事情。漕运最高的官员是总督,往下一级一级有监漕御史、各个省有督粮道,再往下,管监察、管运输的等等官员。到船上,每艘漕运的船叫漕船,每艘船是8-12个漕丁(兵丁)。它是非常严密的一个架构,这里面“吃拿卡要”的事、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必然有。你空降一个官员管这个事,怎么管?这是非常精彩的历史故事。
王老师既写了清代的上层社会官场,又写了清代的民间社会。漕船上的那些漕运兵丁就是民间社会,他们可能不怎么识字,世世代代来应这个工、扛这个活的。漕船从杭州将漕粮运到北京以后,到了通州走通惠河,漕运的兵丁是不进北京的,他们跟着空船回去。漕运的运输路上每天走多少里,到哪个城市停歇,每天走到哪儿,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专门有一本书叫《转漕日记》,一个官员写的每天漕运都干什么。
通州和张家湾都是因为漕运而兴旺起来的地方。张家湾最早是码头,后来成为一个大镇子。通州全是漕粮集中的仓库。在旗的人吃的粮食都是通州或者北京周边这些仓库里面陈年的米,作为军饷、俸禄发放的。
京杭大运河分成七段,北京到通州是通惠河,通州到天津叫北运河,天津到山东临清是南运河,再往下鲁运河等,一共七大段。北京主要是通惠河和北运河。所以通州是通惠河与北运河交界、转换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交通要道。通州自古是有城墙的,有好多文物古迹,有街道、有胡同,格局非常好。
“漕运三部曲”整个要涉及这么广大的场域,这么多的故事,怎么上交漕粮,怎么回去。把清代上层社会的斗争和下层民间的生活,都给打通写到一块儿,这可是高难度。想请教王老师,您这几十年是怎么考察漕运码头这个历史文化的?
王梓夫:说来有点难,《漕运码头》是2003年1月出的,《漕运古镇》是2013年出的,《漕运船帮》是2021年出的,差不多十年一本。我写《漕运码头》前十年,至少有十年的准备时间。那时候没有百度,没有互联网,你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查资料连复印机都没有,全是手抄,而且提供的资料很少。所以我的经验,一方面钻故纸堆,这是很枯燥、很累、效率又很低的事;另一个就是走出去,沿着运河走。每个地区差不多都有一个或几个特别热爱、了解那个地区文化历史的人,我把他们称为“民间史官”。我最早探访、交朋友最多的,就是这些“民间史官”,从他们那里搜集大量资料。
叁
青帮因漕运而生
漕运码头就在通州
王梓夫:后来差不多到二十一世纪就好了,因为各地政协都比较重视。最早的时候政协有一个文史办,开始搜集地方的文史。现在升级叫文史委,作为政协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陆续出的书也比较多。我写《漕运码头》搜集资料非常非常难,到《漕运古镇》好多了,到《漕运船帮》更好一些。因为《漕运船帮》我写青门,材料很难找到。我搜集青帮的历史怎么办?只好到台湾去找。
青帮因漕运而生。早期的青帮是类似民间工会性质,维护自己利益的团体。青帮一共128帮半,断漕之后损失大半。后来有些人跑到上海滩,像杜月笙这些人,整个把青帮变成另外一种黑社会。所以我们印象中一提到青帮,好像就是打打杀杀独占一方,其实早期青帮远远不是这么回事。
1949年以后去台湾的青帮还有26帮。我的《漕运码头》中一个人物是青帮的,一个老英雄。《漕运码头》在台湾出了一个繁体字本,《漕运码头》电视剧又在台湾两个电视台播出,引起青门堂主的注意。他们说大陆写青帮都是把我们当成黑恶势力去写的,居然还有一个人把我们写成正面老英雄,很难得。这个堂主是兴武六的堂主,他们多次到北京来想找我,结果找的门路不对,找不到。
后来大概2008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一个会议上,跟全总一个处长聊天,说想找一个作家,写过《漕运码头》,叫王梓夫。这个处长说:“你别找了,这是我叔叔。”他是我一个老首长的孩子,于是带着他到北京通州找到我。2008年第一次见面,给我讲了很多青帮的故事。第二年他又带着30多人来寻根——青帮因漕运而生,漕运码头就在通州,而且青帮当中的门外小爷就是通州人,包括当年乾隆的三帮九代,跟通州领帮当家的都有关系。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内部秘籍式的资料。后来市场上出现许许多多关于青帮那些小册子、书、影印本,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真正说对的不多,好多都不知道传到哪去了,传得很乱。
后来他们又邀请我到台湾去了一趟。台湾现在的青帮大概还有十四五个帮,比较大的有六个帮,都在高雄和台北地区。他们在帮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党政军的高层人物。写完《漕运船帮》第二次去台湾,是罗英导演跟我一起去的,她拿摄像机把我去的全程都录下来。正好赶上一个契机,就是潘祖360周年大寿,开大香堂,拜祖,整个这套仪式仪轨我们都给记录下来了,很多珍贵资料。这是我的幸运。
侯磊:这个太难得了,这个学问很珍贵,现在能研究这些以及真正接触到的人真是不多了。有一个前辈老学者叫王学泰,他研究这些,但是他前些年去世了。过去民国时候很多名流,包括很多戏曲曲艺演员,都是在帮的,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京剧老爷戏李红春就是在帮的。青帮里面也有行话,他们那个行话跟现在北京、天津流行的戏曲曲艺界的行话还不一样,那是更深一层的。
王梓夫:青帮应该叫通漕,洪帮叫海底。你刚才提的那些艺人应该叫春典。南为春,北为典。
肆
小说家处理历史题材需要想象力
同时又必须尊重历史
侯磊:解老师,请您谈谈对王老师这部作品的印象,您觉得《漕运三部曲》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
解玺璋:刚才梓夫说了,他选择写这个历史,要跟刘绍棠、浩然划清界线,走自己的路。用什么方式处理历史题材?这肯定是梓夫老师这么多年来探索的一个东西。因为历史浩如烟海,这里面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不光是漕运的历史,还涉及到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发展史、很多宗教方面的历史、很多民间神秘文化,包括行帮的历史。这是很复杂的东西。
当我们读一本历史小说的时候,我们期待它带有传奇性。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无奇不传”,小说就承担这样一个任务,它要把很奇特、很神奇的东西传播出去。包括写现实生活的《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它也是有一个神秘的框架——在灵河岸边有一块石头和一棵草,它们之间还泪的故事;《水浒》也是天罡地煞的故事框架,如果没有这个框架,《水浒》可能减色很多;《西游记》更不用提;《三国》本身,大家说它是七分实、三分想象,同时它也有神奇的框架。再比如《说岳》,岳飞也被赋予一个大鹏金翅鸟的东西,他死了以后,他的沥泉枪跑到长江里变成一条龙消失了。
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往往有一个传奇的框架,把历史的内容装进去,读起来才兴趣盎然。我看《漕运船帮》,觉得梓夫老师找到一个很好的叙事框架,这是带有小说家想象力的。他笔下船帮的形成过程,是带有神秘色彩的。
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一个问题,讲科学、反迷信,把很多有趣的东西全都给反掉了。包括戏改,改了很多戏词,为什么?觉得戏词迷信,不合道理,不科学。我记得汪曾祺先生在好多文章里讲过京剧院怎么改戏词,改得狗屁不通,为什么?就是把过去那些认为是迷信的给改了,实际上这个迷信在那时候人的眼里是认可的。
所以文学家、小说家处理历史题材需要想象力,但是小说家又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不是表现在一个具体的人物或者事件上,而是表现在他尊重那个历史时期整个的社会形态和环境,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人是相信有这样的事,他是承认这个的。我们现在懂得科学了,历史、社会发展进步了,我们觉得这事很可笑,但是那时候的人就是这样的。你只有这么写,那时候的人才有真实感。
比如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安清帮形成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神秘文化。在这一点上,梓夫老师特别大胆,他充分表现了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这是这本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
再有一个,我惊叹梓夫老师肚子里的东西太多了。《漕运船帮》跟第一本《漕运码头》比,展开的不光是层次还是天地,都更广阔了。特别是在思想方面,他讲的儒释道三家同源,把儒释道都跟老子联系起来了。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显示出来雄厚的文化积淀特别让人敬佩。一个作家,能够把中国的思想史渗透到小说里面,而且写得这么活灵活现,至少我自己看的书里面还很少。这应该是值得大力推广的,梓夫老师在这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王梓夫:写“漕运三部曲”,我尽可能让自己的作品有一定的文化承载量。《漕运码头》主要写漕运文化,而《漕运古镇》是写丐帮。如果说《漕运码头》写的是横断面的社会生活,《漕运古镇》就是写一个人的命运,从一个小乞丐熬到刑部侍郎三品大员,他的成长过程。而《漕运船帮》,当初我把整个故事和人物构思好之后,两三年我都没动笔,我总觉得缺个东西。其实整个帮会文化足够了,但我仍然觉得缺一个画龙点睛的东西。
一个特别巧的机缘,有人请我和罗导去品香。那套品香的规矩、仪式太棒了,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如获至宝,我立刻把这个东西放进去,跟人物命运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时候我觉得可以写了,从2019年10月10日开始,到第二年4月10日,整整半年时间,一气呵成写完了。
伍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片土壤
确立文学主题跟生活的地域相关
侯磊:王老师同时还是一位剧作家,像《漕运码头》的电视剧,您就是编剧。做编剧对写小说塑造人物有什么影响吗?比如《漕运码头》主人公铁麟,我特地查了,真有这么一个人叫铁麟,而且这个人做过仓场总督。但铁麟这个人,历史上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履历表,只有他哪年担任了什么。对那些历史上大家已经知道的人物,您怎么塑造?像铁麟这种历史上仅仅有几行简历的人,您又是怎么塑造的?
王梓夫:我觉得小说第一要紧的是让人看得下去,这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办法调动读者的胃口。这个办法跟我搞戏剧有关系。我觉得最好的故事是用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把一个人物放在巨大的矛盾冲突当中,放到巨大的两难之中去折磨这个人物,在折磨过程当中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
侯磊:王老师不仅有传统叙事的故事技法,同时这些作品始终在古代人们的氛围中,这里面的人物始终没有出时代。这也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历史剧要求太难,大家都往古装剧发展,说难听一点,也是糟践历史文化、瞎编一些古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的历史,宫廷里面的起居住,各种史料已经记载得非常详细,你再记载雍正想一个什么酷刑把人杀了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看到王老师的《漕运三部曲》,又让我们重归对历史小说的向往和坚信。
王老师同时还是一位“通州通”,您是通州人,2012年的时候还写了《通州赋》,您谈谈小时候的老通州是什么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马驹桥、张家湾、通州是什么样的?
王梓夫:我写《漕运码头》的时候,通州城还是比较完整的。我早上起来八点钟工作,工作到十一点、十二点。下午基本不工作,整个北街,我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走,每天都去走,不止一次。可惜我当时缺一个相机,那时候还用胶卷相机,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我最早在北大街住过几年,整个北大街的胡同我是反复走的。我在《漕运码头》里写的所有地名、走的路线全是真实的。其实好多虚的东西,你一定要细节真实,细节不真实,人物真实也没有用。所以我尽可能让细节真实。通州城最早破坏是1968年、1969年,拆鼓楼,把北大街破坏了一部分。但是后来保存很长时间,一直保存到2000年之前,通州城大的格局没有什么变化。
马驹桥也是,我当年在马驹桥工作了六年,没什么变化。每条胡同差不多家家户户我都认识,每个商店都知道。包括马驹桥那个桥,我们叫罗锅桥,站在南端和北端人互相看不见,那个坡非常大。当年传说马驹桥的来历,乾隆骑着一匹母马到南苑打猎,这个母马生了一个小马驹,所以叫马驹桥。当时桥的两边有两个亭子,亭子有两个碑,乾隆御笔记载马驹桥的历史。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片土壤,这片土壤是很重要的,不仅仅影响这个作家本身的性格气质,也影响他的文学主题。还是那句话,确立自己的文学主题跟自己生活的那片地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网络文学好像不讲这个,什么赚钱写什么。其实那是另外一个路子,咱们也不能说人家的不好,我们做的事比较笨,下的功夫苦一点。
整理/雨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