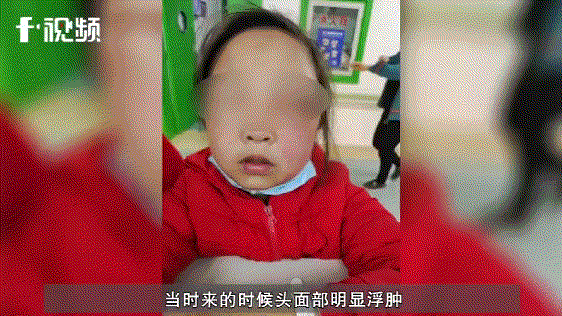逻辑原子的提法和黑格尔的整体主义针锋相对。罗素所理解的黑格尔整体主义大致是这样一种主张:世界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所有个别事物都是这个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从一个部分推导出另一个部分,脱离整体的个别事物不过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一些假象。我们可以从绝对是舅舅开始,但是,有舅舅就必然有外甥,于是,作为绝对是舅舅的反题,我们就有了绝对是外甥这个命题,两个命题合在一起,就是绝对是舅舅和外甥构成的整体这一合题。然而,这一整体仍不完美,因为一个人必须有姊妹才能当上舅舅,于是“我们被迫扩大我们的宇宙,把姊妹连姐夫妹夫一起包括进来”,如此扩展,直到把万有都合在一起的整个宇宙。与此相反,逻辑原子主义主张,世界是由个别事物组成的,这些个别事物是最真实的存在,它们互相独立,我们无法从这一事物的存在推导出另一事物的存在。“原子”不是常识所认为的那些个体,例如项羽、这张桌子、这个地球,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些复合事物。我们会想,项羽是由心肺眼鼻四肢等很多个别器官组成的,心肺眼鼻又可以继续分解下去,一直分解到夸克。但这是物理学的分解法。从认识论角度看,物理对象必须以某种方式还原为知觉。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一颗客观存在的星星,但实际上这颗星星可能早已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它在若干年前发出的光线而已。我们对对象属性的认识既然依赖于我们的神经系统以及其他条件,我们实无理由断定物理对象本身一定具有这些属性。简单说,从认识论来看,项羽是由如此这般的体貌、如此这般的行为举止组成的,体貌举止可以继续分析下去,直到不能再细分的、真正简单的对象,或逻辑原子。罗素有时也说,世界是由简单殊相构成的,每一简单殊相只包含简单性质,简单殊相之间则只具有简单关系。
真正的简单事物,或逻辑原子,是些什么呢?罗素很长一段时期称之为感觉与料(sense-data),虽然后来放弃了这个提法。罗素有时也说,逻辑原子只是理论上的结论,我们无法得到真正简单的对象,这是因为,无论从物理学上说还是从认识论上说,事物都是无穷可分的。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简单对象,这个概念总是非常困难的。一小块红色是个简单对象,一小块粉色也是简单对象,然而在红色和粉色之间也许存在着无穷多种半红半粉的颜色。物理学最后也许会分割出最小的物质体,感觉生理学最后也许会确定各种感觉的阈限,但这些都离题太远。因为这里要考虑的不是最小的物质体或感觉阈限,而是构成意义的基本单位。即使我们确定了有限数量的简单对象,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可以是无限的,在很重和很轻之间、在远近之间,都可能有着无限多的分隔。何况,关系本身也必须被视做对象,如果关系不是对象而只是包含在对象本身之中的可能性,那我们很快就要回到罗素一向努力批判的内在关系说了。
不难看到,罗素关于逻辑原子的本体论主张是和认识论紧密联系的。按照罗素的看法,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分成亲知(acquaintance)和描述(description)两种。我们的常识不难理解通过描述得知和亲知有别。我到过北京,在那里见过天安门,那么,我知道北京,知道天安门,知道天安门在北京,这些都是我的亲知。你没到过北京,但通过交谈、读书、照片,也知道北京,知道天安门,知道天安门在北京,但你的这些知识不是亲知,是通过广义的“描述”知道的。
亲知是第一手的所知,听说是第二手的,一切从描述获得的知识都要还原为亲知才能最终具有意义。我不知道项羽,但我可以亲知读书读不下去是什么样子,可以到乌江边看看乌江,可以到博物馆去亲眼看看楚汉相争时代的文物,有了这些亲知,我就能从“那个少学书不成的人”、“那个在乌江岸边杀汉军数百人的人”来了解项羽。项羽已经死了两千年,我们谁对他都没有亲知,但我们仍然知道他,靠的就是这些描述。当然,即使真能把关于项羽的知识一一还原为各种亲知,那也会是个漫长的程序,罗素无法细说,我们也很难做到,多半要凭想象来完成。此外,每个人还原为哪些亲知,也各不相同。于是,“项羽”一词对于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意义,有人想到的是他见过的一个勇士,另一个想到的是一个男人对着一个美人边哭边唱。
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平常你会说,你到了北京,亲眼看见了天安门,但这只是个日常说法,真正分析起来,你看到的不是整个天安门,而是一片红色,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巨大梯形,梯形中间的一些门洞形状,梯形顶上的金黄颜色和这些颜色块的形状,等等。分析可以进行下去,直到不可分析的最终元素。这些最终元素,就是“感觉与料”。在“看见天安门”这件事情里,真正称得上“亲知”的,就是对这些感觉与料的感知——看到天安门可以分析为这一个那一个感觉,天安门可以分析为这一个那一个感觉与料,其实,在分析的这一终端,感觉和感觉与料两者已经合一,既不属于主体也不属于客体,这样的主张叫做“中立一元论”。除了感觉,记忆和内视也能提供亲知,我们能通过回忆亲知过去的事情,通过内视(introspection)觉知自己在觉知事物,觉知自己的欲望以及心灵里发生的别的事情。
所以,你只是在间接的意义上看见了天安门,你直接看见的是感觉与料,你对这些感觉与料进行整理、推论、组织,形成了对天安门的整体认识。非亲知的知识可以说是从亲知出发所作的推论。例如,我只能对我自己心灵里发生的事情有亲知,但“我们通过对他人身体的知觉,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与他们的身体相关联的感觉与料”知道别人心里的事情。“要不是亲知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内容,我们就不能想象其他人的心灵,因而我们就绝无可能知道他们具有心灵。”
亲知原则有它很通俗的一面。我们很少有人活见过鬼,但我们都懂得“鬼”这个字的意思。鬼长得和人差不多,不过特别轻,昼伏夜出,诸如此类,人我们都见到过,分量轻,夜里出行,这些我们都很了解,因此我们也大致知道鬼是个什么东西。有疑问的是这么两点,一、哪些是我们的直接经验或亲知?它们是一些感觉原子吗?二、宇宙从大爆炸产生,这是我们推论出来的,鬼、他人的心灵,这些也是推论出来的吗?如果是,它们似乎是很不相同的两种推论。如果不是,我们是怎么知道鬼或他人的心灵的?
通过罗素对亲知和描述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原子主义和感觉主义合在一起的总体面貌。原子主义和感觉主义都来自休谟。“感觉与料”大致相当于休谟的“印象”。事实各自独立这一提法也见于休谟:“凡存在者都可以不存在。否定一个事实绝不会陷入矛盾。”复杂事物由简单事物组成,复杂观念可以分析为简单观念,这都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主流观点。所以,与其说罗素在这里有什么新见解,倒不如说他是在利用新时代的逻辑工具阐发传统英国哲学的观点,赋予它更精致的形式。
——陈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