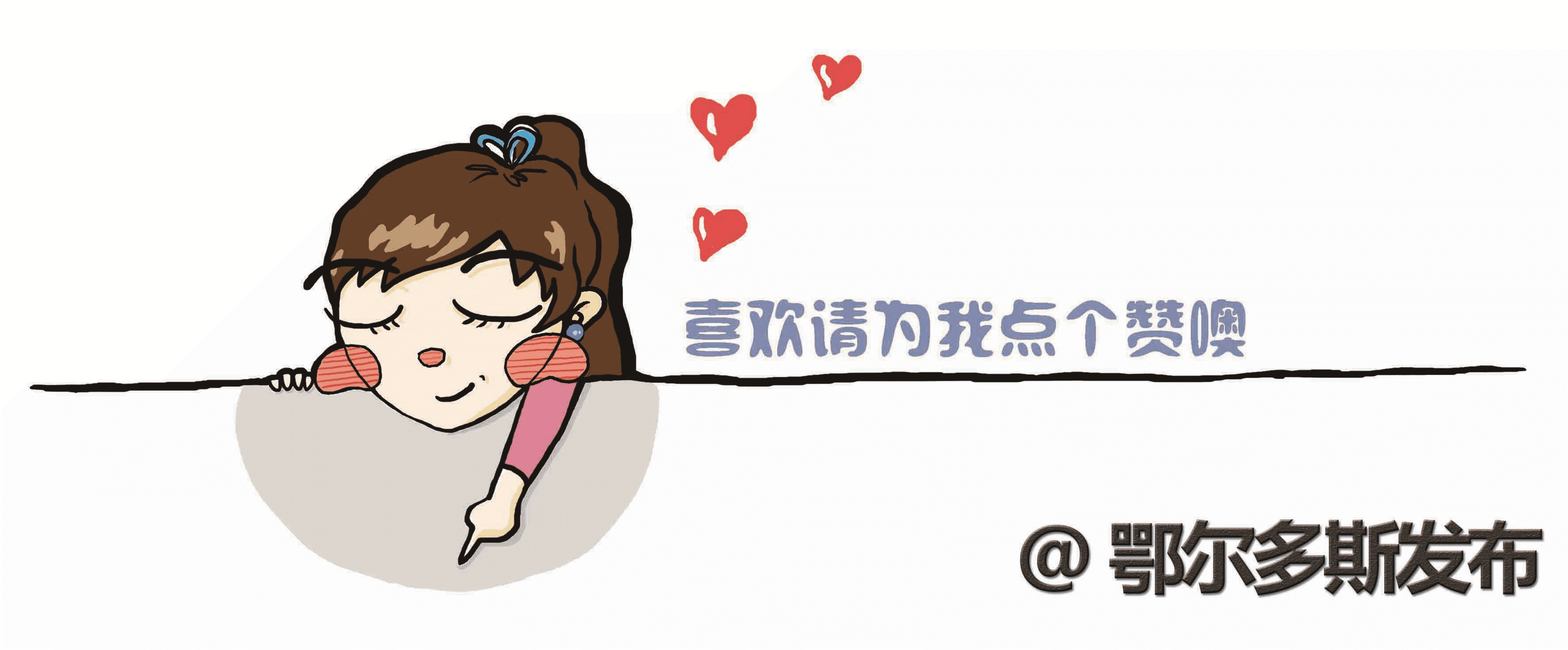此图为娟子采摘园园主,诗人-----张娟。请看着她的眼睛你会发现------她,戴美瞳了!
“每一天,我和草木共荣”
五月底的周末,陕州区张汴乡西王村娟子果蔬采摘园外,前来采摘的人们围坐在石磨垫成的桌子旁,品尝着瓜果。张娟一边麻利地切瓜,一边介绍:“这是羊角蜜,这是天鹅蛋。咱们还是先尝羊角蜜,再吃天鹅蛋吧。羊角蜜酥脆度比较高,但甜度不如天鹅蛋。咱们如果先吃了天鹅蛋,再吃羊角蜜就不感觉甜了。”大家品尝完,她将一只只垫着花布的篮子递给大家,带着他们走进了大棚。
“呀!怎么这么多虫子呢!”女游客惊叫起来。大家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叶子背面爬满了黄色的小虫子,又看别处也有不少。张娟忙解释,“瓜果成熟前,为了保证安全性,我们就不再打药,所以才会造成腻虫泛滥,不过这种虫子现在只伤叶子,不影响瓜的生长和成熟。”
吃过张娟瓜果的人都说她的瓜果特别甜,有人调侃:“到底是写诗的人,种出来的瓜果都有灵魂。”其实,瓜果的香甜只与付出相关。我注意到,张娟采摘园每个大棚的外面都堆着大堆大堆的羊粪,正用塑料布盖着发酵。她说这些都是从灵宝和观音堂拉来的,一个大棚一料地要用到四到五车羊粪。她在手机上下载了《头条》APP,关注着几十个农业专家,跟着他们学习农业种植新技术。她采用粘虫板、烟驱虫、大蒜油杀虫,这样不但成本较高,而且杀虫效果也并不太理想,但张娟却坚持用。她还带头使用红糖生物有机肥,以增加瓜果的甜度……她说有机瓜果不是靠嘴上说的,必须是实实在在的。
张娟带着游客摘完香瓜、吊网西瓜、西红柿等,来到接待处统一过磅收款。这些瓜果有的是她家的,更多则是合作社其他成员的,张娟要负责给客户算账、收钱,最后再分钱给大家。张娟麻利地过秤、报价,有时一个顾客买了好几样瓜果,她一时手头没纸笔记录,便用指甲划在地上。
这几年,张娟不断被当地和外地媒体宣传,大小也算是个名人了。她一直说,你给合作社的瓜果多宣传宣传吧!农村人没文化,赚钱真不容易。
临近中午,她催合作社的其他人赶紧回家吃饭,她自己仍然守在大棚。“一般下午人会多,一会儿又得忙了。”张娟说着,脸上的笑容荡漾开来。

“如果我走了 就让我躺在诗歌里”
张娟从小就爱看书,也爱写写画画,学生时代在《洛神》发表诗歌处女作《如果》。经营饭店、超市时,她在网上成立了新时代网络诗人协会,写诗、编诗、评诗,忙得不亦乐乎,协会最多时有好几千号诗人。
问她为啥写诗。“我这人懒,诗比较短。”说着自己先笑起来。她的笔名是紫岩,还用过暗香的名字。她认为诗歌除了讴歌,便是医治。近些年来,对她来说,诗歌更多是医治功能,“我常常用诗歌做熬药的引子”。
张娟在土地上劳作时,背上却已生出翅膀。她的诗质朴,灵动,不造作,不扭捏,她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没有功夫无病呻吟,她写立春、惊蛰,写脚下的土地,写自己生活的西王村,写西王村里的人和事,她笔下的田园生活不光是鸟语花香,更多的展现生活的忙碌、无奈和愁绪。我在她的诗歌里常常读出疼。“拉着近百米的棚膜/哼哧哼哧地,一步一步走着/心里说,不是为了死/就是为了活”。
诗歌带给她什么?“总算可以用攒下来的长短句子/缝补生活与梦想之间的裂痕”。多年来,她的诗都出现在QQ里,和诗友的交流也在这里。有一年下雪,张娟拍了几张照片发在QQ里,其中有一张小狗阿黄的,有诗友问:为啥小狗放着台阶不走,而选择在旁边的斜坡上蹦跳。张娟回复:“刚刚我问阿黄了,它说,它从不走寻常路!”在和诗友交流的时候,她会变成另一个人,睿智、机敏、幽默、风趣,完全放松下来。她很享受这样恬静的时光,她的QQ几乎都是深夜更新的,放下锄头,拍拍尘土,她在这里找寻一份宁静和慰藉。曾经听一位诗友建议,她把自己的一首三行诗印在了果箱上,“心生蝴蝶,因你/一年四季鲜花不败,水果丰盛/笔不尽墨,诗不止歇”。两年前,她在QQ上给苹果打广告。由于下了冰雹,苹果表皮留下深深浅浅的坑。她写道“这些果子与精品果之间只有一到两个酒窝的距离”,把苹果的疤精妙地比喻成酒窝。
张娟写诗没有主动投过稿,大都是诗友推荐,或者编辑索要。写诗的人不图稿费,但她很喜欢领稿费的感觉。2015年4月,有杂志社告知有38元稿费,虽不多,却也能济点小事,她顾不上去领,却早已安排好了用处--买只三黄鸡吃火锅,这是证明文字也有价值的最好方式。
几年前,脑瘫农妇余秀华一炮走红,那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红了整个中国。而张娟认为,她和余秀华“唯一胆大又卑贱的是/我们只在诗歌里意淫”。
四年前,三门峡当地的几位女诗人与张娟取得了联系,以文字谋面的诗友突然来到了活生生的现实中,她的喜悦和感恩藏都藏不住,她称她们为姐姐,“姐姐,你疼惜的目光/我该如何才能好好收藏”“ 姐姐,你能来/是比开花还要幸福百倍的事情”。 姐姐们送的《瓦尔登湖》和《同城》,她一直视若珍宝。后来,有一位姐姐的微信屏蔽了她,因为她在微信朋友圈发广告。对此,她能理解,“一个真正要创作的人是不应该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打扰。”讲到这里,还很善意地提醒,“你把我也屏蔽了吧,我真的是天天要发广告。”
诗歌是张娟的心尖。“如果我走了/就让我躺在诗歌里。”可是在她看来,首要的是把生活搞好,其次才轮到诗歌。她不愿意整天沉浸在诗中,却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面对苦涩的生活和无穷无尽的难题,她常常恨恨地问自己“要诗歌何用?”恨完,抱怨完,该劳作时掂锄头,有灵感时依旧写诗。
“常常在下雨天更像一个女人”
张娟42岁,中等个,瘦,皮肤是太阳色,脸上的皱纹略深,齐肩卷发拢在耳后,头发分两截,梢部是黯淡的酒红色,根部是新长出的黑发,眉尖明显描画过,耳朵上挂着圆圆的银耳环,脖上戴着玉石项链。她穿着黑色的蕾丝的上衣,下穿黑色哈伦裤,脚上是一双紫色带花凉鞋。
她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我有不可曝光的黑和不可公开的丑”。因为长年劳作,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略大些。去年有一位年轻妈妈带孩子采摘,让孩子管她叫奶奶,这让她感到很受伤。 此后,在采摘量大的日子里,她会刻意收拾一下自己。“别急,等我画好眉/三月最好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年轻”。可是脸上和疲惫却总是遮不住。去年冬天,初中几个女同学来采摘,拉住她的手,眼睛立刻就潮了,“你咋操连成这样,可得拾掇拾掇。”“哪个女人不爱美。咱天天在地里刨,齐整不了。”她手指甲都略长,左手大拇指指甲更长,藏着泥。这指甲得留着,因为要掐芽,瓜果苗的茎要随时掐掉,防止疯长。
地里的活似乎永远也干不完,张娟也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白天可供安排。对于农人来说,雨天让人沮丧,对于采摘园更是如此,雨会挡住人们前来采摘的脚步。而对她来说,有时候下雨心底会冒出一丝小小的窃喜。因为“我是个安静的孩子/常常在下雨天更像一个女人”其实雨天,也不影响棚里干活,可她却可以借机懒一下。“不如感谢雨/时间臃肿起来”。在这臃肿的时间里,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写诗和收拾一下自己。两年前,她的QQ曾经有一张照片,她着一袭白色连衣裙,双手相握,很优雅地站着,配文“40岁的老清新,严禁细打量”。有空的时候,她还会画画,画地坑院,也画美人。只是这样休闲的时刻,对她来说,似乎有些稀缺。美术是她中专时的专业,似乎除了在设计瓜果包装箱时派上过用场,自己和周围的人很多时候都已经完全忘记了。
“我秃顶的男人”
张娟在诗里多次提及丈夫朱春生,用的都是“我秃顶的男人”。 在外打工期间,她结识了朱春生。当年,朱春生送给张娟一首诗,“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一下打动了她。多年后才晓得是德国诗人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她“质问”朱春生欺骗她。朱春生实话实说,“我又没说是我写的。”1999年,张娟嫁到了张汴乡西王村。朱春生是老小,家人都称他“老五”。俩人结婚时,老五的父母都已70多岁,不仅没房,连安家的2眼窑洞都是临时买来的。她形容老五是“光尾巴猴”,啥都没有。家里三四亩地,种些土豆、西红柿,由于没水浇,产量质量都不高,收入少得可怜。贫穷的日子,随着2000年儿子朱云涵的出生更加拮据,买奶粉都要出去借钱。夫妻想过不少致富门路,都以失败告终。
那年夏天,村里人上后山挼连翘,一斤能卖块把钱。正在喂奶的张娟也加入到这支队伍。凌晨两三点结伴出门,天亮才能到。到中午,正干着活,奶憋上来,她只能找个角落忍痛挤掉,一面心疼儿子吃不上,一面觉得浪费,心里面,那个滋味……后来,弟弟告诉她,电厂门口有个小饭店转让,她借钱盘下,开了“好心情饺子馆”,雇了个师傅,就和老五干开了。随后,开曼、恒康建厂,她又在厂附近盖了小超市,给建厂的工人卖些日常用品。小两口的日子忙碌又充实,生活也不似从前那么紧巴了。
2013年,张汴乡搞退宅还田,号召村民发展大棚,张娟不想回村,干农活太苦了。老五先回去,一方面是父母年龄大了要照顾,另一方面他觉得村里比城区空气好,在城里他老生病。老五先种了一个大棚。第二年,张娟回村,她觉得还是两口子在一起比较好彼此照顾,当年种了四大棚葡萄。结果由于技术原因,又赔了一塌糊涂。种葡萄时,她听说草莓好卖,就试着在葡萄苗间种了些。谁知,捎带种的草莓竟然卖了八千多块钱。第二年,她种了一棚草莓,丰产又丰收。草莓成熟时节,前来采摘的车辆排起了长队。这之后,她们开始种西瓜、香瓜、西红柿,基本上都成了。随着位于邻村北营村的陕州地坑院景区的日渐火爆,采摘园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在很大程度上,老五并不完全理解她,尤其是不理解她写诗。这个男人,高高大大,“从不轻易说苦,不轻易说甜/不轻易说爱”。 最难的日子,两人相互搀扶着一起走了过来。“偶尔/和秃顶的人抱头痛哭 ,抖抖压在心上灰土”。老五原来脾气很急,现在慢慢回了性。她背疼,晚上老五会帮她按摩、艾灸。生活渐渐好起来,2015年,她们在县城按揭买了房。儿子今年18岁,在县城上高三,学的是音乐。虽然俩人忙大棚很少管孩子,但孩子很懂事,这让两口子感到欣慰。
“有多苦的花就有多甜的果”
生为农民,张娟却并不喜欢这个出身,可是没得选。她很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没能跳出农门。但她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十六岁时,因为不喜欢陕县职专的专业,跑到三门峡中专学美术。在外打拼多年又重回土地后,她下定决心要当好农民。
农活本就累人,大棚更加耗人。地里的活总是层出不穷,一个个排着队焦急地等着,一年到头都要忙,“再也没有给时间松过绑”。大棚里不分季节,只要外面有太阳,里面就是夏天,又热又闷,一天流一斤汗绝对不是夸张。如果刮风,就更是提心吊胆,很多时候,和风较一天劲,人都累了,风还不累。冬天,最怕下大雪。今年元月,连续降雪让她和老五满心忐忑,怕棚塌,先把下面的雪铲掉,再用塑料膜把腿裹住,小心翼翼爬到棚顶,把快积到膝盖处的雪一锨锨铲下……
农家的生活是艰辛的,她和老五要“养谷子,养儿子/养房子,养车子/血盆大口的生活”。即使近几年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她还是惶恐,心里依然不踏实。“我也有新房,可我随时会失去它/这根本入不敷出的农事,这/越滚越多的利息,这/出过n次小事故的五菱面包,这日子”。
对农村的苦,她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乡亲的日子,和她也并没有两样。“他们背日头,从早上背到黄昏/从年头背到年尾” “拿力气换白面”。杨守强的大棚种了西瓜,由于浇水多导致烂根,一棚半人高的西瓜秧全部烂掉。枯萎耷拉的秧苗,让张娟心疼;守强叔蹲在地上把头埋在双臂间的样子,让她的心疼了又疼。还有前年冬天的大雪压塌了村里四个大棚,至今说起,她心里头都是沉沉的。两年前,有村民到大棚找到她,请她帮忙卖苹果。我问:“为什么大家要让你帮忙?”“我也不知道,他们可能觉得我能帮上忙吧。”上个世纪90年代,张娟在保健品公司打工,担任过一个城市的营销经理,管着六七号人,还配有车,在乡亲们眼里大小也算个能人。张娟从不忍心拒绝眼含期望的乡亲,于是开始卖苹果。她组织包装、发广告、发快递,帮着乡亲们卖了四五千斤,当然自己也挣了些辛苦钱。
2015年,张娟和老五成立春生农业专业合作社,如今有7户社员,20个大棚。她胆子大,敢闯敢干,张汴塬上的草莓、圣女果都是她带头种的。她寻思着,老几样,种的人多,都卖不上价了,想引进火龙果和甘蔗,可心里又没底。
如今,她和社员的地头已经立起了“陕州区扶贫产业基地”的醒目牌子,合作社不仅可以让村民农忙时到大棚打工挣钱,还直接带动了十多户贫困户发展生产。2017年,她当选为张汴乡人大代表。对于这个身份,她很看重。她为农民的困境忧虑,为果蔬卖不出去而发愁,老想着找出路。“你说,我思考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超出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了?”她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我道:“有一种人,天生就是带着使命感来的。”她很深地点了下头。她爱操心,是由于身为老大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受母亲影响。母亲曹蜜蜂,在村里干妇女主任多年,热心公道,找她的人总是很多。张娟觉得母亲就像蜜蜂一样,为儿女忙,为村民忙。她也想像母亲一样,多为乡亲做一些事情。之前,她和合作社的社员都种西瓜、草莓,来采摘的都找张娟,她便将来人推荐给其他社员,社员们再不用开车到城里叫卖,不仅省了时间,价钱也高。用朱菊朋的话说“她对我们心足了。”可是,张娟觉得这不是长法。从去年开始,她引导社员搞差异化种植,香瓜试种了8个品种,西瓜分红瓤和黄瓤,西红柿也分大西红柿和圣女果。这样,游客这个棚进那个棚出,各家都有收入。
张娟希望更多人关注农业,这样农业才会发展得更好。她希望乡亲们的日子都能苦尽甘来,她坚信“有多苦的花/就有多甜的果”。
最后,我想用张娟刚写的一首短诗来结束这篇文章:
我听见了你的忧伤
虫儿在雨夜的长音
声声慢,声声凉
这安静里按捺的畅想——
除了飞扬的
浩浩荡荡
这黑暗里包裹的曙光——
除了呐喊的
把呐喊封藏

后记:感谢资深作家晓晓用最动情最用心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当潇洒相当感性的女人,张娟的人就如她的采摘园一样实在,大气。借用曾经的一张合影表达一下对张娟的念想----无论何时,努力的女人总是最美丽。好久不见,愿你安好如初。(来源辛小鱼在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