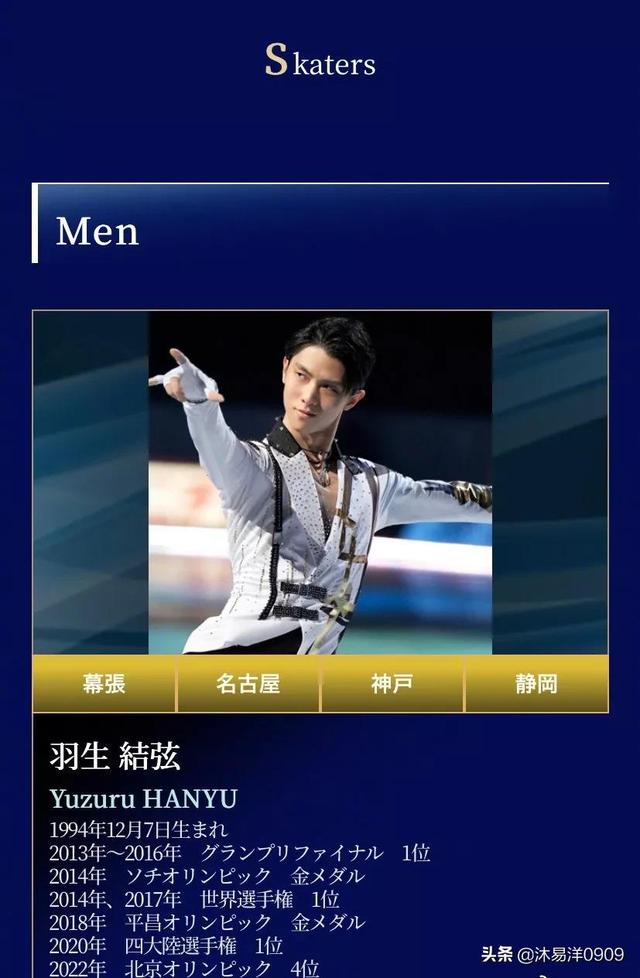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是我就读初中的阶段。那时每学期都有农忙假,忙假里就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大田劳作,倒也情趣盎然,因为除了干农活,还尽享老老少少的谈天说地、人间活剧和“上下八沙”的传闻逸事。
生产队里有五、六个年轻人,年龄比我稍大些。他们志气相投,喜好相近,干起活来不买帐,玩耍时也别出心裁。记得我读初三那年的“三秋”忙假里,不知是哪位兄长忽发奇想,要玩一次“放洋灯”。
我从没见过放洋灯,不知洋灯为何物, 更不知如何放。

放洋灯一般是元宵节前后几天里的玩项。队长是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不想招惹多余的口舌,想了个折衷办法:“贴工不贴钱” ,也就是工分队里记,费用自己掏。队长也有他的难处,因为“条条沟里有‘赤眼鳝’(一种红眼的鱼,借指那些善于找茬的人)。”
所说的“洋灯”,和现在流行的“孔明灯”相仿,只是洋灯要大得多,它是用很薄的白纸(也有用牛皮纸制作,但重量稍大,不易放飞)粘贴成的一个正方体,每个面用4张整张纸拼接而成,俨然是个庞然大物。正方体下面开有直径20多公分大小的圆洞,安装上一个细铅丝圆锥架,架子顶端扎上有两个拳头大小且浸足煤油的棉布球,洋灯下面的4个角上系有2米左右长的细蜡线,线上均匀缚扎着红、蓝、黄、白的小纸团,用于增加可看性。
被取名“洋灯”,大概形同当时乡间农家照明所用的煤油灯(也称“洋灯”)之故。有人告诉我,制作洋灯的关键是拼接缝处绝不能漏气。
一丛人小心翼翼的把洋灯搬到空旷的田间,队里男男女女数十号人都围了过来,叽叽喳喳,说这道那,欢声笑语,再或就是纵情调侃,总之,田间充满着少有的欢乐。
要点火了。提角的忠于职守,拢线的全神贯注。四周原先的那种热闹场景很自然的被暂时“封存”了,每个人都凝神专注着那位“玩火者”。
不知是谁走漏的消息,相邻的一队、三队社员成大部队过来“看白戏”了。尽管乡下的“瘾君子”大都抽最蹩脚的“勇士”牌香烟,来客中的多数人还是不忘向我们的队长敬上一支,以示打个“招呼”。舞台是露天的,其实也无所谓。
大凡“等”的时间容易显长。左等右等,洋灯就是不起身。我是个急性子人,大概那些慢性子人此时也和我差不多,都想能尽快看到究竟。原本静得出奇的田间,还是被人打破了,有人悄声发问:“要是火油烧干了怎么办?” 有人超前假设:“一旦火星子落到洋灯上,会不会烧起来?” 更有人大胆质疑:“上面风大,说不准会被吹倒过来。” ……

我根本耐不住寂寞,就四面转圈探看,自然也不忘探看一下洋灯底部那个燃烧着棉布球的神秘圆洞。纸箱里烟雾重重,棉团依然燃烧正烈。此时,突然有人大声吆喝:“嗨!……”我被吓了一大跳,“下面不能瞎看,男小囝一看以后就寻不到娘子!” 那是爱逗乐子的先伯拿我开心。等我明白过来,满场子的人早已一片哄堂大笑,连我父亲也夹杂到了大笑的队伍里,只有我母亲给了他一个不痛不痒的回击:“没大没小,叫你先伯也馊香!”
不知多长时间后,洋灯象被充过气似的渐渐鼓了起来,开始飘飘欲仙的左右晃动着。“观众们”开始了骚动:“起来了!”“起来了!”其实还没到真正飞起来的火候。
“拎住!千万不能松手,还没到‘熟’的时候!” 小康是放洋灯的“始作俑者”,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而今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指挥官。那些“一线”人员既紧张又兴奋,哪敢掉以轻心。
终于,洋灯朝着顺风的方向摇摇摆摆向上浮升起来,于是,提角的人、拢线的人都随其自然撤手了。四角细线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小玩意在天空中随风飘荡,煞是好看。人们都“疯”起来了,欢声笑语充满着偌大的原野。那个场景数十年后我仍难以忘情。农田乐,实实在在的农田乐。
洋灯越飞越高,也越飞越远,最后一直到无形无踪。社员们意犹未尽,仍然翘首远望,他们是在遐想它能否有回归奇迹的发生?
全过程的时间,似乎很长很长,又好像只在瞬间……
之后,我再没看到过放洋灯。据那帮玩家说,后来不允许放洋灯了,因为放洋灯是易造成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
而今,我已届古稀年龄,少小的这次亲历一直挥之不去,其中的乐趣,也只能存留在记忆里,陶醉在回忆中……心语
版权声明:本公众号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授权发布,任何媒体及个人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授权,并在转载时标明出处及作者,谢谢合作。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END -
—
—
作者简介
郁尚高笔名一冰,1947年出生,崇明竖新镇人。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上海第三十五棉纺织厂退休。现为崇明文史研究会会员,十多余年间撰写地方文史资料40余万字。在市级与本地刊物发表文艺作品多篇。
—
—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合作!欢迎关注陆安心的私媒体“心语”。(anxin20141124)也可扫描上面二维码或长按二维码关注。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