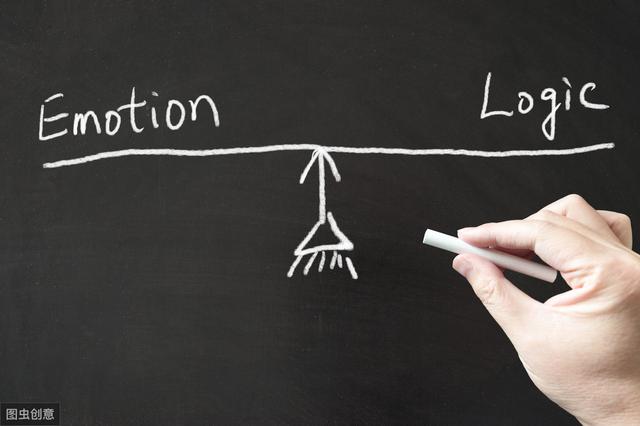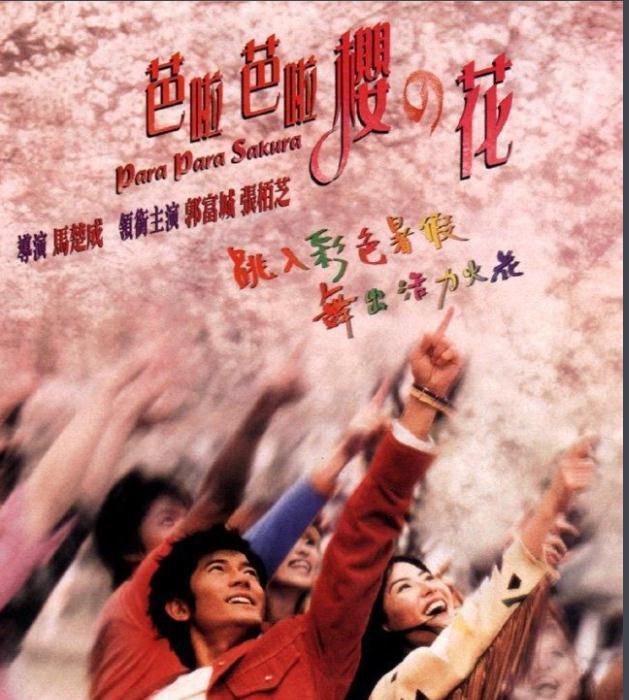王家能/摄
抒幽愤成就山水散文之绝品
——《永州八记》新论
文/王启鹏
摘要: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的产生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他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把幽愤寄托在山水之中,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山水审美观,传神地展示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山水典型,从而成就了我国游记散文的绝品。
《永州八记》是家喻户晓的游记散文名篇,篇幅不长,不少文句还经常挂在人们的嘴边,要想在这样一组经典文章中写出具有新意的论文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苏东坡说:“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敦秀才失解西归》)遵照苏东坡的读书方法,我对原著反复诵读了好几遍,果然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永州八记》的写作技巧非常特别,抒幽愤贯穿行文始终;而艺术成就也特别高,已成为游记散文的绝品。现分析如下:
一、《永州八记》的产生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
我国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有壮丽的河山,也有宽阔的草原。古今文人都喜欢旅游,喜欢观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于是对大自然的“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山水散文。
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产生却很特殊,他在唐代永贞元年(805)因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到永州,“居是州,恒惴憟”[1]762,心理压力非常大。再加上生活不安定,“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与杨京兆书》)[1]790所以一直没有游览山水的兴趣,直到元和四年(809)九月的一天,秋高气爽,他坐在法华寺西亭上,突然发现过去没有注意的西山风景很特别,于是他才开始探求永州的奇山异水,写出了“八记”中的前4篇:《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直到元和七年,才完成了另外4篇,中间相隔了两年多。
还应该指出的是,柳宗元笔下的这些景物,不是现成的,而是他带领仆人“斫榛莽,焚茅茷”[1]762得来的。所以,他笔下的自然景物是他通过披荆斩棘的艰苦劳动才得来的,和历代的山水散文的产生有着极大的不同。
二、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忧愤寄托在山水之中
寓情于山水是所有游记散文的写作方法,或是借眼前之景物以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或是借眼前之景物以歌颂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或是借眼前之景物以抒发自己的感受,不同的是抒情的侧重点不同罢了。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所表达出来的“情”,就与大多数作者不同,他抒发的是他遭贬后孤愤的身世之感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幽愤之情。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写道:“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所怀绥伊郁,讵欲肩夷巢?”[1]1189他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登临揽胜的,其目的是借外在的景物来排遣胸中的郁闷,正如他在给李建的信中写道:“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与李翰林建书》)[1]801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贬谪到永州后柳宗元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差的,常怀恐惧和矛盾之心:“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一个“恐”字,就把他当时的心态写得活灵活现了。恐什么?“涉野有蝮虺大蜂”,“近水即畏射工沙虱”。所以,即使他出游了,也只能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1]762这就把他那个步履迟缓、毫不经意、不自检束的形象写出来了。这样,柳宗元在写作山水游记时对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也就特别在意,而手法也非常巧妙了。
手法一,借奇特之景物抒发激愤之情。写景状物,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是山水散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而柳宗元与前人的写法不同的是,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痛苦之情,巧妙地渗透在景物描写之中。由于柳宗元对这些景物有敏锐的观察,所以他笔下的景物都写得活灵活现,恰当地表现出他此时此刻的特有思想情感。如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那“突怒偃蹇”“冲然角列”的奇石,实际上就把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写出来了。他把溪水和小石潭的水写得那么“清冽”,实际上也是衬托出他品行的端正和思想的高洁。他把小丘写得很美,奇石遍布,可这样美好的地方,却没有人要:“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这样写,实际上就是隐喻自己像这座小丘一样,虽然品行美好,有才能,可得不到重用,只能废弃在这偏远的山区。其他的景点,如小石潭、袁家渴、石渠、小石城山等,虽然风景美丽,很有特色,可是得不到人们的认可,这实际上都是柳宗元的自况,隐喻得不到当权者的赏识和任用。
手法二,柳宗元在写景后突然插入一两句饱含感情的话,令景物更具特色,而自己的难言苦衷也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了西山的高峻之后,接着写道:“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这虽然是写景,实际上却寓有更为深沉的含义,表明了他不愿与腐朽的官场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行。又如《钴鉧潭记》,在具体地描述了钴鉧潭的状貌后,发问:“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用一个“乐”字来托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忧愤哀怨之情。《石涧记》也是这样,在描写了石涧的状貌后,又写道:“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意之日,与石渠同。”这里同样是用一个“乐”字来衬托自己寄情于山水的苦闷,何“乐”之有?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在写完小石潭的清幽景色后接着笔锋一转:“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把自己被贬后那种抑郁失意的感情融化于景物之中,显得余味深长。
手法三,采取整段议论的方法,直接抒发心中的愤慨。柳宗元不是空洞的议论,而是在叙事的基础上带着深厚的感情,或是用比兴手法,或是采用曲笔,使文义显得委婉含蓄而具有韵味。如《钴鉧潭西小丘记》末段:“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鄂、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夫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1]766在这段议论中,柳宗元先是借小丘无人赏识,隐喻自己虽有为民的抱负却不被任用,无辜被贬谪永州。接着,他就借这个小丘终于碰上了赏识它的人,使它的命运得到改变。这样写,柳宗元是借题发挥,表达了“小丘有遭而自己无遭”的愤慨。
又如《小石城山记》的末段,柳宗元极写了小石城山奇特风景之后,提出了造物者有无的问题。他以山水自况,痛惜小石城山“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还说“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这实际上也是感叹自己空有杰出的才能,却遭贬谪,冷落在荒州,不得施展才华抱负。所以,明代学者茅坤称此文是“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2]111
三、成就了中国游记散文的绝品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虽然篇幅不长,文字总量不多,但由于他是在贬谪期间抱着一颗愤愤不平的心态来写作的,所以他的艺术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游记散文,其艺术成就更是别具一格。具体说来是:
(一)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山水审美观
我在文章开头就说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自己通过“披荆斩棘”才写出来的。所以,他对山水的审美就有自己的心得。他凭借敏锐的审美感觉和审美经验去发现美、营造美、赞颂美,提炼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1]730的著名论点,并把山水的自然美归纳为旷、奥二境。他说:“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丛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永州龙兴寺东丘记》)[1]748从美学观点来看,“旷”和“敞”是同义的,属于“空而宽阔,没有遮拦”的美学范畴;而“奥”和“邃”亦是同义的,属于“幽深、神秘”的美学范畴。《永州八记》所写之山水,正好体现了“旷”和“奥”的美学思想,可见柳宗元是有一套独特的山水审美理论的。
(二)传神地展示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儒道释诸家都有阐述。“天”,道教、道家多指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庄子认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受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的约束,便失去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因此,人类讲究修行,将人性解放出来,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正如王生平所说:“天人合一的美是通由天人同构的途径完成的……但‘人’去‘合’‘天’,又必须以‘天’为根据,对照‘天’的特点找出‘人’与之类似的特点,这样‘人’成了‘天’‘合’的对象。于是,可以称为天人合一。”[3]82
柳宗元笔下的景物描写,确实是找到了“人”与“天”类似的特点,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如,描写耳目神心与山水太空互相交流感应的文句:“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潭西小丘记》)[1]766又如,描写自然环境与作者自己的感受的:“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1]767最为精彩的还是《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那几句:“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1]763作者与山水景物的关系确实达到了“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了。
从上面所引用的语句可以看到,柳宗元能够写出如此美妙的天人合一的文句,其根本原因就是,柳宗元能够细心观察事物,并进入静观冥思状态,体味出自然界景物的气韵与精神,达到了与心灵相通的境界,因而就能够把这种美感物化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作品。
(三)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山水典型,使之成为一幅幅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水画
清代林纾曾经指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不能谓其漫记山水也。”(《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袁家渴记》下)[4]163林纾的意思是说,山水游记写的虽然都是高山小丘、清潭曲溪、绿树花草等自然景物,对于一般作者来说,其笔下的自然景物多少都有一些相同的美学意念。而柳宗元游记笔下的景物却不同,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不可重复,没有雷同化的毛病。
同样是写山,柳宗元笔下的西山和小石城山就不同。
西山,柳宗元本意是写它的高峻,可他的笔墨一点也没有用在西山本身,而是采用侧面烘托的笔法,写自己在西山上看见的情景。由于西山高,所以“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仅此一句就把西山之高写得非常形象。紧接着,柳宗元就具体写他在西山上所见的自然景物。由于是居高临下,各种奇异景色都历历在目。“尺寸千里”,虽然自然景物遥在千里之外,可看上去好像在咫尺之间,这实际上又暗写了西山的高。
对于小石城山的描写就完全与西山不同,柳宗元采用正面直接描写的方法,把这座自然形成的小石城山,写得就像是一座古代城堡的遗址:断裂的土墙间隔着两条小河,前面乱石堆积,横挡了小河的去向。只见堡顶虽然没有土壤却长满了树木和小竹子,把城堡的景色装点得格外奇丽。竹树有疏有密,有俯有仰,好像是经过巧匠精心设置的一样。
写溪水同样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石涧记》着重写石态水容:“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环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前3个“若”字写出了石头的奇姿异态,后2个“若”字写出了石上流水的形状和音响,令人叫绝。
而《石渠记》则着重写渠水的出没变化:“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这样的写法,显然是不同于石涧的。
《永州八记》虽然是用文字书写而成的,但细细品味一下,每一篇“记”实际上就是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水画,真正达到了苏东坡品评王维诗的艺术效果:“诗中有画”。最为经典的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不会画画的人读了这篇文章后,也能够想象出一幅美妙绝伦的山水画来。“全石以为底,近岸,巻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这就写了潭的石质结构,石头的各种形状,是名副其实的“石潭”。“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写潭上面的景物:青青的树木,翠绿的藤蔓,随风摇摆。“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几句写游鱼,是最为精彩的。它通过鱼儿的活动,潭底的鱼影,让读者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小潭“水尤清冽”的情景。至于写游鱼与游客相乐,更是让读者叫绝。最后又写流入小石潭的溪水:“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斗折蛇行”,比喻溪水之曲折,“明灭可见”,形象地写出了曲折的溪水有的可以看见,有的看不见。由此可见,柳宗元写小石潭的景色,由水而山,由石而树,由树而鱼,一层层地描绘得十分细致生动。细细品味一下,这实际上就是一幅层次鲜明的构思奇特的山水画。
《永州八记》的山水形象那么鲜明,除了作者具有敏锐观察力和迅速的捕捉能力外,还与他具有娴熟的语言能力有关。他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能够选择到最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力求做到语言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他虽然没有选用浓墨重彩的词语,可他笔下的景物形象却十分鲜明。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石头:“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写溪水的:“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奇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这些语句用的都是平常的语言,没有特别深奥的文字,但其表达效果特别好,字字清丽,句句有景,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客观景物的神态。这种用“常言”就能够达到形象鲜明的艺术效果,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5]118的艺术境界。
(四)采用连环式的结构使八篇游记成为一个整体
《永州八记》是自成体系的一组作品,前4篇写于元和四年(809)秋天,后4篇写于元和七年秋天,中间虽然相隔了两年多,但这次搜奇探胜是一次有计划的前后互相衔接的游览活动。从地域来看,是集中在永州州治西南一隅的近郊,以西山为中心而进行的,这8篇“记”就是这次活动全过程的记录。以《始得西山宴游记》始,文末标明“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中间的篇与篇之间有衔接的关联词或文句,如“钴鉧潭在西山西”,“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等,清楚地反映出游览的顺序,最后以《小石头城山记》终。所以说,这8篇游记是一个整体,是一组文章。
值得商讨的是,《游黄溪记》虽写于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多数人认为它不属于“八记”。实际上,此文是柳宗元游览永州山水后的一个总结:“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数百,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数百,黄溪最善。”[1]759这就是柳宗元通过游览永州山水后得出的结论。所以有人说,应该把这一篇放进去,成为《永州九记》,这是很有道理的。
综上述可知,由于柳宗元在游览永州山水时是怀着愤懑的心情来抒写他遭受贬谪后的苦闷,所以他的《永州八记》在写作风格、写作体制,艺术成就等方面,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我国的游记散文中堪称为“绝品”。
参考文献:
[1]柳宗元集校点组,《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
[2]转引自吴小林著,《唐宋八大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3]王生平著,《从“同构”到“人化”之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
[4]转引自高海夫著,《柳宗元散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5]颜中其著,《苏轼论文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