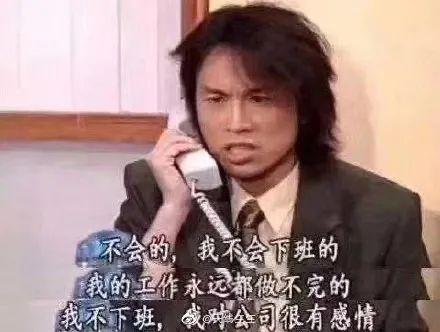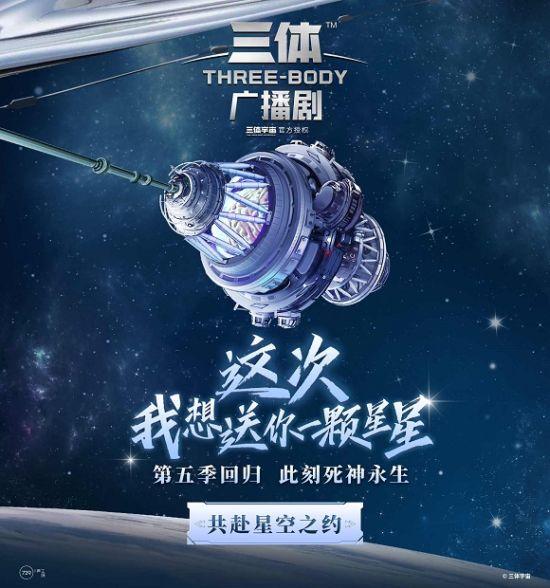作者:Evan Louison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Filmmaker(2022年1月12日)
大概没有什么电影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窃听大阴谋》对后现代悬疑类型的影响更大了。
该片对一个被卷入欺骗和背叛之网的孤独窃听者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一个里程碑,以及极富创意的原始文本。然而,在公映50年后的今天,这部电影仍能准确无误地描述了所谓的情报工作的道德滑坡,对所有参与其传播过程的人的影响。

《窃听大阴谋》(1974)
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后来却后悔拿了钱;一项古怪的任务,导致了良心危机;一个强调行事惯例、心态镇定的职业人士,只有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谋杀案的同谋时才能被动摇——这些线索都指向了《窃听大阴谋》及其矛盾的主人公哈利·考尔,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它们已经成为了该类型电影的典型参照。
影片上映之时,由吉恩·哈克曼扮演的考尔是新好莱坞经典电影中的一个异类。不过,虽然《窃听大阴谋》的元素——一个复杂的反英雄,角色研究和惊悚片的结合,以及一个走向毁灭之路的结局——早已成为悬疑片的范例,但直到它1972年斩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之后,观众才开始对其另眼相看,只能说明这些元素的组合在当时是多么史无前例。

考尔脾气乖戾,性格孤僻、多疑,不愿与他人共事,而且对自己也不诚实——在他的圈子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任何一类人。在这个故事中,往往祸不单行,而考尔穿着一件麦金托什塑料雨衣,似乎时刻预防着不测。他是一个极其专业的技术人员,窝在室内进行工作,对人的声音和背景环境音进行记录。这么说来,你可能会误以为考尔是一名剪辑师。

沃尔特·默奇对于研究20世纪电影的学生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他不仅长期担任弗朗西斯·科波拉的西洋镜电影公司的御用后期大师,还常常参与影像和声音剪辑的工作,以及出任了《教父》《现代启示录》《天才雷普利》和科波拉正在进行的个人修复项目等数十部电影的后制总监。但是,作为蒙太奇艺术孜孜不倦的传授者,他本人的工作很少成为焦点。
默奇在1995年出版的《眨眼之间》(暂译,In the Blink of an Eye)一书,也许是其剪辑理论的唯一记录性证明。而他的功劳——直到今天,他的许多贡献都没有得到官方认证——与他在无数纪录片中出现的频率相形见绌,这些影片揭秘了他与合作者的工作,以及剪辑艺术的神圣。

78岁的他脾气暴躁,恨不得让自己的酒杯满溢出来。关于这些电影,尤其是《窃听大阴谋》,可能和默奇本人一样,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前年,里亚托影业发行了由科波拉本人监督的35毫米全新版本《窃听大阴谋》,而最近电影论坛电影院(Film Forum)重映该片时,本刊有幸与默奇进行了交流。
问:据说早在《教父》之前,科波拉就有了《窃听大阴谋》的构想。作为创作圈子的一员,你对于早期的草稿有多少了解?
默奇:唔,让我想想。我这里有......(拿出一个装订好的、仿佛到处都是涂改痕迹且稍微泛黄的剧本)这是第一稿,可以追溯到1970年。弗朗西斯大概从1968年开始就一直在创作它,但并没有准备好印制初稿。
而这个剧本是1970年春天交付给华纳兄弟公司的大包裹里的一部分,当时包裹上写着:「这是西洋镜电影公司想拍的电影。」其中包括《窃听大阴谋》,《现代启示录》和《黑神驹》。还有其他三、四个项目最终没有拍成。从初稿到制作,大约相隔了两年时间。这期间主要在拍摄《教父》。

问:所以《窃听大阴谋》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在《教父》后面拍的,华纳当时看了拍摄计划之后有什么反馈?
默奇:他们拒绝了所有的剧本。他们一个都不想拍,甚至要起诉弗朗西斯,要求他赔偿开发这些项目所花的所有钱。那个诉讼是弗朗西斯接受拍摄《教父》的原因之一。此外,还可以赚点钱,以及把他自己从一个可怕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问:在科波拉的作品中,有很多要么出自他由衷的热情,要么是履行任务,或许他比任何导演都更愿意亲自上阵,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接受公众极为严苛的监督。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父》的成功是否为《窃听大阴谋》打开了大门?
默奇:确实如此。

问:科波拉一直都致力于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制作重新剪辑或重新配乐的版本,例如去年的《棉花俱乐部》和《小教父》。不过《窃听大阴谋》似乎一直以来都没有经受过这些改动和更新,它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默奇:嗯,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部电影是他的最爱。所以没必要多此一举。
问:《窃听大阴谋》是你担任剪辑师的第一部电影。你创造并发展的剪辑点概念,是对古典好莱坞的线性叙事,以及苏联时代的蒙太奇辩证形式的回应吗?很多剪辑和段落似乎都预示着这个概念,而且你早在写作中就花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它。当然,在这之前也出现过一些创新:安妮·考特斯和哈尔·阿什贝就是逐渐拓宽剪辑工作边界的标志人物。但《窃听大阴谋》的剪辑在许多方面似乎都是一个分水岭。它的大胆之处在于,它与那个时代其他节奏狂热的美国电影相比,显得过于朴素。尤其是理查德·莱斯特和丹尼斯·霍珀的电影。
默奇: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好借用一下树枝的比喻,树干上的结代表着必须做出决定的地方,树木生长的方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问:确实有这么一种关于树木生长的理论,长出枝桠可以看作是树木的自然智慧的表现。蒙太奇的剪辑点理论似乎假定,叙事的纹理,镜头的切换,可以遵循同样的有机衍生。无法总是保持完美的对称性,但会有一些启示性的时刻,在这样的剪辑中显现出来。
默奇:我当然知道,就像木工的每一种材料都决定了你要做的家具的结构一样,我所使用的木材——《窃听大阴谋》的素材,很少以匹配剪辑的方式处理。从主题的层面来看,似乎更多的是分野明确的剪辑,动作处于即将发生但还没发生的状态,然后你进行剪切,下一个镜头带入运动。就当时而言,这是电影找到自己风格的一种直觉,我认为每部电影都是不同的。后来我才发现这与我的特定风格更相关。这是慢慢形成的,因为当时我的剪辑经验还并不丰富。

问:在最开始的剧本中有更多人物,不过你剪掉了很多素材。
默奇:被删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与背景故事有关的场景,即哈利的另一种生活。在剧本中,哈利秘密地拥有他所居住的大楼,虽然他的租户都在抱怨大楼的维护问题,但旧金山的那个地区将有一个大规模的重建计划,所以他不想为大楼投入任何资金,因为他知道它将被拆毁。
问:所以有一个平行版本的故事,哈利是一个业主——黑心资本主义的同谋,这也将会成为电影批评的核心议题之一。
默奇:没错,不过这些都不复存在了,只留下了一点点的幽影。

问:这部电影被压缩到了很小的范围之内。
默奇: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剧本没有拍摄。事实上,有两个大场面与故事的结局有关,但都没拍。因此,当我进行剪辑时,是用原版故事80%的内容来拼凑出一部电影。
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即使是像《窃听大阴谋》这样的经典影片,也需要在剪辑过程中绞尽脑汁,以应对拍摄时导演留下的选择不足的问题。
默奇:当然。有一个片尾的重要场景我们没拍,因此,影片中哈利的幻觉和他在磁带中反复听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对素材缺失的一种补救。

问:在你和迈克尔·翁达杰合作的访谈录《剪辑之道:对话沃尔特·默奇》(暂译,The Conversations: Walter Murch and the Art of Editing Film)中,你说:「在制作这部电影时,我常常产生一种分身的感觉。在深夜剪片时,看着哈利·考尔整理磁带的画面,我仿佛感觉我们俩的手在同时操作。甚至有几次,我是太过疲惫,头脑都不太清晰,哈利·考尔就如同心有灵犀一般地按下了停止播放的按钮,而我更感觉震惊的是,电影居然没有随之停止。」
默奇:唔,在连续工作18个小时、一直熬夜到凌晨三点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恍惚的状态也不算奇怪。

问:但这种体验,除了剪辑是一门孤独的艺术,以及你与影片中的事件和人物变得亲密无间的原因之外,似乎也呼应了观众在观看电影时的体验。观众被带入了与考尔以及其他人物共生的状态,我们的观影感受甚至与事件本身达成了一种同步性。
默奇:哈利·考尔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电影主角,这也是弗朗西斯感兴趣的一点。在其他类型的电影中,这种人物最多只有两到三分钟的镜头。变成一个送磁带的平平无奇的家伙。
问:在观察人物的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被吸引了进去。
默奇:没错。当弗朗西斯邀请我担任这部电影的剪辑师时,他说:「你有处理声音的经验,所以你会理解他的。」但是,因为哈利不是一个天然吸引人的电影角色,所以面对这种问题时,我们奉行的标准之一是不让观众产生退避的念头。《天才雷普利》也是如此。他们不是观众通常会希望成为的主角。

问:在《窃听大阴谋》面世后的50年里,这种情况确实很少。
默奇: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观众要么自愿参与,要么心甘情愿地被电影裹挟。没有回旋的余地。
问:观众往往不得不屈服,因为有一种大手在幕后操纵,正如你所提到的,一些看似突兀的运镜会迫使观众投入注意力。
默奇:没错,但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产生了这种吸引力。
问:你很难找到一部比《窃听大阴谋》更早的美国电影,让观众被深深地卷入这样的侦探故事中,并与叙事产生如此奇怪的联系。
默奇:的确,影片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实时性,观众和哈利知道的一样多。

问:但有些事情似乎是哈利不该知道却知道了的。他在凶案发生前就预见到了。他在没有任何理由出现在犯罪现场之前,就看到了自己身处其境。在记忆中他看到了监视小组视角内的特写镜头,但从他的角度来说,他不可能看到这些画面。
默奇:没错,这是不可能的,打破了规则。弗朗西斯对于当时的监控摄像技术也很感兴趣,它们可以和动作检测传感器相连。有时,哈利离开画面之后,镜头并没有及时跟住他,而是在隔一段时间后才跟上,慢慢平移,把他重新纳入画面。
问:但是这种美学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默奇:确实会随着布景的不同而变化。我们选择的空间有三种不同的风格:联合广场的纪实风格,覆盖了四个隐藏的摄影组;拥有更多景深的传统设计风格,例如哈利工作室所在的仓库;然后是没有空间感的空间,即哈利在工位上完成的作品,就像是一个二维图像层面的蒙太奇。他的脸、卷轴、扬声器、录音机,还有手。这些想象中的组合影像,似乎是从记忆中浮现在这个没有空间感的空间里。

问:哈利记得一些他从来没亲眼见过的画面。
默奇:是的,仿佛我们钻入了他的大脑。
问: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如此。这部电影中有一种梦的逻辑,而且成为了影像剪辑语法的一部分。它创造了一个嵌套的叙事,首先有一些透明的素材,然后被覆盖,慢慢地有更多画面补充进来,形成了完整的影像。
默奇:还有一个例子是,哈里在听录音时,突然感受到了对一个词的强调,而此前听到它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在一遍又一遍的播放之后,语义发生了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我们被锁在哈利的大脑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理解的方式。他想让他的监听对象成为那家企业的受害者,最后他意识到事实恰恰相反。

问:影片对于匿名的强调似乎超过了隐私,也超过了孤独。《窃听大阴谋》似乎在质询一个问题——你是否可以完美隐入人群,但结论是,不能。就像两个随机的人可以成为监听目标,并被距离他们十分遥远的人发现一样,任何人都可以被找到。片中有一个角色吹嘘自己窃听了一场总统竞选活动,并为该候选人的失败立下了颇大的功劳。是否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在挖掘后越战、后肯尼迪时代弥漫的恐惧氛围?而且此时,水门事件才刚刚浮出水面。
默奇:在我看来,弗朗西斯从1968年开始写这个剧本,自然对尼克松和汉弗莱的总统竞选有所指涉。当时,我认为我们最关心的是,人们可能会把这部电影看作是对水门事件的一种回应,但水门事件发生时,影片已经在制作中了。当时,公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一部电影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来制作。我们不希望影片以这种方式被误解。

问:观众似乎与考尔也有某种错位的关系。考尔是一个十分偏执、技术高超的人,抛开整个阴谋事件,坐在影院的观众似乎在和他一同找寻真相,将各种线索拼凑起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观众也变成了控制那些旋钮的人。
默奇:这让我想到了约翰·休斯顿的一句话:「真正的投影仪是观众的眼睛和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