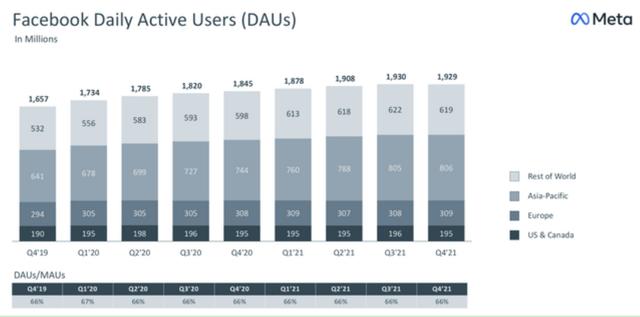林乃卫在B站的第一支正式视频,意想不到地爆了。
这并不是一支十分精致的视频:旧手机拍摄,画质不高清,也没有讲究的构图剪辑,文字选择的是老派的宋体,配乐听上去也更像是父母辈的风格。
但真正吸引观众的是视频里的内容——那是他耗时大约4个月造出一个纯手工自制CPU的全过程记录。
密密麻麻的电路板和各种元件,让人很难相信一个人也能造出一个精密复杂的CPU来。
但他做到了。

这个视频在B站获得了158万播放,最高冲上过全站排行榜的第51名,有6298条弹幕和4385条评论。
网友纷纷留言赞叹,“原来小作坊CPU是真实存在的。”“新人都是魔鬼。”也有人打趣,“梦回苏联,妇女用针线一针一针缝制CPU。”“你这防止老年痴呆的方法太硬核了。”
媒体也开始找到林乃卫。报道中,在广西北海做程序员的他,被冠上了一个颇有几分霸气的名号——“B站焊武帝”。
与林乃卫一样在B站上发布着硬核的科技视频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内容和人们印象里B站上以二次元和鬼畜等为主的视频类型明显不同。不过,从“焊武帝”们的走红可以看到,原本人们眼中“高高在上”,需要有一定专业知识才能看懂的科技内容,在年轻UP主们的加工和调剂下慢慢变得接地气,一个气质特别的科技区开始在B站生长起来。
人们发现,原来真的有人,而且是很多人,在B站上看如此硬核的科技内容。
就是喜欢做科技视频
林乃卫最早有手工自制CPU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大学。
林乃卫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在报专业之前,他就已经对机械、电子和软件等等技术有了浓厚兴趣。大三就经常会写单片机玩,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产生了对程序运行机制的好奇,第一次有了自制一个8位CPU的想法。
CPU是中央处理器的英文缩写,被形容为计算机的大脑,用来解释计算机指令以及处理计算机软件中的各种数据。因为结构过于精密和复杂,很少有人,哪怕是学习相关专业的人会想到去手工制作一个CPU。但林乃卫没想那么多,他就是对这事儿感兴趣。
“自己做CPU,不仅可以打发时间,还能经常动脑防止老年痴呆,一旦成功了,毕业后可能也比较容易找工作。”他在自己的B站专栏调侃道。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也很实际。

在完成了前期设计之后,林乃卫花了当时两个月的伙食费采购了一批芯片和设备,并打印好了电路板。只是还没来得及焊接组装,大四毕业设计来了,自制CPU的计划只好暂时搁置。直到新冠疫情,他从之前的工作地深圳回到老家北海,计划才得以重启。中间过去了五年。
“终于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他在自己的专栏写道。
很多搞技术的人似乎都喜欢写专栏博客,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这些文字里都能看到,他们在做的事情,往往都是兴趣驱动。另一名B站UP主“Ele实验室”也是如此。
去年年初新冠疫情刚刚爆发时,你可能也在各类社交平台看过一支题为《计算机仿真程序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还没到出门的时候》的视频。
视频利用一个自制的仿真程序,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向观众直观科普了人群流动意向对疫情传播的影响。尽管其中出现了许多一般人看不懂的编程语言,但好在视频的呈现和解说都足够通俗,整体并不会给普通观众造成太大的理解困难,里面对不听劝阻硬要出门聚餐的亲戚的吐槽,反而令很多人共鸣。

这个在B站获得了402万播放和9543条弹幕,并一度冲到全站排行榜第三名的视频,正是出自Ele实验室之手。
和林乃卫一样,Ele实验室背后的创作者也是一名程序员,本科学习的都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并且也是1992年生人。在2019年底成为一名UP主之前,Ele实验室更常“出没”的地方是知乎,喜欢在上面更新一些技术相关的文字笔记;线下的他则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会经常给公司内部的其他同事做计算机方面知识的相关培训。
“当时感觉自己对通过语言和图像来展示一个知识还是蛮擅长的,所以才考虑试一试做一名UP主。”
他起初并没有想到视频能这么火,“心情其实还挺诧异的,不知道为什么它能传播得这么广,诧异过后又感觉,可能确实这个会对别人有一定帮助,还挺高兴的。”
“可能这个视频所带来的现实价值、社会价值都非常大,这样会感觉到自己的劳动会带来比以前做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大的价值,这本身对我的创作是一件非常有激励的事情。”他接着补充。
在那支爆火的视频之后,Ele实验室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长远目标:成为B站计算机通信领域的头部账号。
一个很累的手艺活
从今年三月重启自制CPU的计划后,林乃卫一干就是四个月。
大学时候完成的前期设计,现在看来已经非常落后,他只能重新进行设计。一般情况下,他会在下班回家后从晚上八九点一直做到十一二点。中间也尝试过持续一个月的高强度制作,一直到半夜两三点,为了“肝”这个视频,甚至会经常头疼。
制作CPU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其零件太多了,组装需要时间,挑bug也需要时间。“这要是扯断根线,不得找半天。”有网友在林乃卫的纯手工自制CPU的视频下留言,林乃卫回复说,“最长的时间是找了两个星期。”

因为涉及到许多专业的原材料和知识,比起像美食、游戏、生活和舞蹈等等其他品类的视频,科技类视频往往需要更久的时间来筹备和制作,也会消耗创作者很大的精力。这也是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的B站科技区UP主看起来都不那么高产。
Ele实验室目前的视频更新频率是每月更新一次。因为他的内容更多以用计算机手段科普知识为主,这就要求他首先得保证在最基本的知识解读上不出错。
“科普视频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创作者去查阅大量文献,否则很容易给观众带来误导。即使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知识,在创作的时候也需要去翻很多文献,否则很可能会出问题。”
在B站运营着账号“大谷的游戏创作小屋”的UP主大谷也有类似的“烦恼”。
主职是做游戏开发的大谷自从2019年产生对AI(人工智能)的兴趣,便开始试着去边学习边做一些应用,比如利用AI作曲、绘画和修复老照片等,并将这些发到B站上。
许多人还记得他做的《我用人工智能修复了100年前的北京影像》。视频里,他将拍摄于1920-1929年、原本是黑白色的几段老北京影像利用AI技术成功还原为了彩色。

类似的视频大谷还做了很多,目前基本保持着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条的速度,这很不容易,因为视频制作十分繁琐。
比如验证AI还原出的颜色是否合理的过程,就需要非常细碎的工作。
因为AI是自动上色,参考学习的是数据库里的图像,如果遇到某个数据库里没有的物体,最后上的色便很容易和现实有出入。在做100年前北京影像的AI修复时,大谷就主动去了解了许多关于故宫的历史资料和论文,做了很多查证,比如里面衣服、建筑等等的颜色到底对不对。

“我不希望一个作品最后产生误导观众的效果,尤其是当视频有了一定受众之后,会更加鞭策自己去把内容做好,避免让观众产生一些历史歧义和理解偏差。”大谷说。
除了准确,他们也要考虑视频的传播度。
“因为一个科普视频,它可以讲得很深,也可以讲得很浅,不仅仅是要把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还需要在深浅之间取一个合适的折中。如果讲得太浅,很多人就会说看了个寂寞,如果太深,很多人又会说看不懂,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
今年刚满19岁的手工科技UP主“017_凌十七”,在B站已经有了37.5万粉丝。此前他制作的《造一把小刀》,“高燃”的剪辑最终带来了189.8万的高播放量。他觉得,播放效果好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个视频能让人看懂。

这也是他认为自己所有作品中最特别的一个,因为足够简单,能让观众持续看下去。两个礼拜的制作,最终浓缩进了一个只有约5分钟时长的视频里,为了能让呈现更加通俗,他放弃了很多对于步骤的解释,“基本上已经没有过程了”。
观众在视频里看到的,只是他全部制作过程的冰山一角,“虽然在视频里也能看到不少过程,但相对于实际的制作,比例一定是非常非常小”。
为什么是B站
这些UP主所制作的视频,似乎并非B站赖以快速崛起的视频类型。但他们似乎都认为B站是最适合这些硬核科技视频的平台。
事实上,吸引他们的并非这里有没有科技视频的土壤,而更多是作为用户感受到的来自创作者的启发,以及社区的氛围。
今年刚上大一的凌十七正是一名典型的B站用户,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时,他身边的同学也几乎都会玩B站。最开始,凌十七也没有特别关注B站上的科技类内容,而是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看一些B站特色的鬼畜视频。
在从用户变为创作者的过程中,B站迅速走红的何同学给了凌十七很大启发。
2019年,还在上大二的“老师好我叫何同学”靠《有多快?5G在日常使用中的真实体验》一夜走红。当时还在上高三,并已经拿过许多机器人、科创相关比赛奖项的凌十七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把自己擅长的东西转化成真正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
大谷的经历也与此类似。他是B站最早一批用户。他从小就对动画制作感兴趣,本科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了美术学专业的艺术策划和管理方向,研究生又去纽约视觉学院学习了计算机艺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制作了自己的第一款Flash游戏《Eddy紫》,一些玩家在视频网站分享玩这款游戏的录像,大谷就建了B站账号来分享这些视频,之后感受到的良好氛围让他一做就是4年。
像大谷一样,很多创作者一开始选择B站并非认为这里适合科技类视频,而是这种社区互动的吸引力。

在成为UP主之前,林乃卫并非典型的B站用户。他对B站的所有了解仅限于“里面年轻人会比较多”,关于B站为数不多的记忆是去年在这里观看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发射直播。曾有网友在他的视频下留言,“我以前在部队里面待过,但是一直忘记是哪个部队的,看到你的视频之后,才想起来是三连。”他花了几天才明白过来,这个网友说的原来是一键三连的意思。
比起B站,林乃卫在贴吧要更如鱼得水一些。在有重启自制CPU的想法之后,他起先想到的是在贴吧发帖,用文字记录下来整个过程。在“显卡吧”写下自制CPU的计划后,帖子很快火了,开始有吧友建议他可以把过程拍成视频发到B站,大意是,“这类型的手工视频发到B站也许会有更多人看”。
他接受了吧友的建议。而在意识到自己的视频在B站火了之后,他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慢慢体会到B站的更多乐趣,他也开始去花心思思考怎么才能把视频拍得更好,“比如可以去掉组装之类的比较枯燥的情节,多加一点介绍和对运行效果的展示,让视频整体更好看一点。”
越来越多的硬核科技视频的背后,B站也在做着拉拢人才的工作。
据B站向品玩介绍,早期B站上其实就有很多科技类内容,只不过当时科技区的建立更多是用户自发的结果。2020年,因为社科人文、科普等内容的增加,科技区曾短暂地更名为知识区,直到今年6月对知识区再度分拆,才有了现在用户看到的共分为数码、软件应用、计算机技术、工业工程机械和极客DIY共5个二级分区的科技区。
“如今再度分拆,也是为了适应用户内容需求的发展。我们发现用户对计算机、软件、极客DIY等内容有非常大的需求,应该单独建立分区。”B站表示。
与此同时,可以明显看到B站也加紧了对科技区的运营。其中既包括了对一些科技圈热点,譬如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1024程序员节等事件的跟进,也包括了许多针对不同科技区品类和UP主的活动和定向扶持,比如有针对数码品类的“星际漫游计划”,针对科技区全品类的“科技猎手计划”活动等等。

这些举措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林乃卫。而对于另一些已经有了几年经验的科技UP主来说,他们其实更看中B站为他们带来的更深层的连接。
Ele实验室也曾试过在其他同类平台发布视频,但体验并不如B站好。“说白了在其他平台发视频,数据好不好我其实根本不care,感觉在这些平台我更像一个编辑,而不是一个创作者,把内容分发出去就完了,没有一个回馈的过程,其实这个感觉挺不好。”他把在这些平台数据不好的原因归结为受众年龄跨度太大,创作者和用户之间的层级关系过于明显。
相比之下,在B站发视频会让他更有“压力”,会更看重和用户之间的反应。因为B站年纪相仿的用户会更多的缘故,创作者和用户更像朋友,“当你和用户一旦形成类似于朋友的关系的话,对于内容的要求也会更严格一点。如果没有认真做视频,很可能就会破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你就会有所失望。”
凌十七也有同感。“对于像我一样希望能够呈现一些内容、做出一些有含金量的视频的创作者,其他那些偏向很爽的短片、快餐视频的平台其实并不适合。”凌十七很明确自己视频的第一目标群体是学生用户,这是B站能够带给他的,“B站很多观众都非常友好,同龄人彼此之间也会相互欣赏一下,这个可能是很多平台没有办法做到的。”
大谷最早在B站建账号的原因,正是因为创作者和用户之间更像是朋友之间交流的状态,不像是一个对外的平台,感觉更像是“在家里”。大谷说,自己视频的受众年龄,一大块是10-20岁,另一大块则是40岁左右,即便是这样年龄跨度巨大的两个群体,也能够在自己的视频下互相交流和学习各种知识,“这就是互相进步的一个过程。”

为爱发电?
尽管B站令很多科技UP主感到亲切和舒服,但真正愿意做一名全职UP主的,还是少数。
林乃卫几乎已经确定自己不会做一名全职UP主,因为太耗时间。“像做这种视频的话,有可能一年才出一个,快的话可能也需要两三个月,如果全职去做其实不太现实。”他说。
刚刚花了半年时间造出一个机器人的凌十七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为了造这个机器人和制作视频,他去年已经向大学申请了延期一年入学,平衡视频和学业,不是一件易事。
虽然19岁的他通过做UP主获得的收入已经能够支撑他的日常拍摄。他还记得自己接到的第一个商单来自拼多多,赚了6000块,这对当时还在读高中的他是个不小的数目,“还挺有成就感的,第一次赚钱还挺爽的,虽然视频做得没有特别好。”
据B站介绍,目前科技区UP主的主要商业化方式是商业合作,即广告。而承载了B站促进UP主与品牌方合作的官方平台“花火”今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数码3C已经是目前B站的前五大广告品类之一。
去年年底,Ele实验室辞去了在北京的程序员工作,尝试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UP主。
契机来自他和B站确定了的一个合作项目——开发一套人工智能原理相关的付费课程,由B站提供稿费和资源支持。B站给到的报酬,基本和他上班时的收入持平,而能拿到确定的收入,几乎也是Ele实验室会选择成为全职UP主的全部理由。
“就是因为看到会有一些确定的项目,所以才敢辞职了。”他坦承。实际上在B站有了十几万粉丝的时候,他就曾想过要不要辞去工作做全职UP主的问题,但最终还是没有跨出这一步,“当时还是有一些顾虑,但如果是有一些确定的项目的话,其实也就无所谓了。”
这个和B站合作的付费课程项目,Ele实验室做了大半年,并最终命名为《小白也能听懂的人工智能原理》。上线后的效果还算令人满意,尽管在收益方面没有特别高,但从课程答疑群里用户的反馈来看,大家的回应还是非常热情,“感觉它产生的价值已经超过它本身的课程价格了。”

课程做完,效果达到了,但因为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项目,要不要继续做全职UP主的问题再度摆在了Ele实验室面前。下一步他打算回到老家杭州,一方面的考虑是杭州也有不少互联网人才,想看看是不是能拉到一个团队来实现全职做UP主的事;而另一方面,在杭州各方面的经济成本会小一些,“一旦以后不全职做UP主了,我可能也会去那边上班。”

Ele实验室或许代表了现在许多科技UP主目前的处境——虽然可能有成为全职UP主的条件,商单也不缺,可真正将之付诸实践,又免不了会有各种顾虑。
而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在多个平台都在大力抢夺创作者的同时,B站上的许多人却多少依然有早期B站UP主为爱发电的感觉。
“不知道别的UP主是什么样子,如果我全职了,万一到了一个时候,想法枯竭了怎么办?”大谷说。
他满足现状,如今在B站取得的收入基本能够支持自己去买一些制作和拍摄视频需要的设备。“付个电费还是可以的。”他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