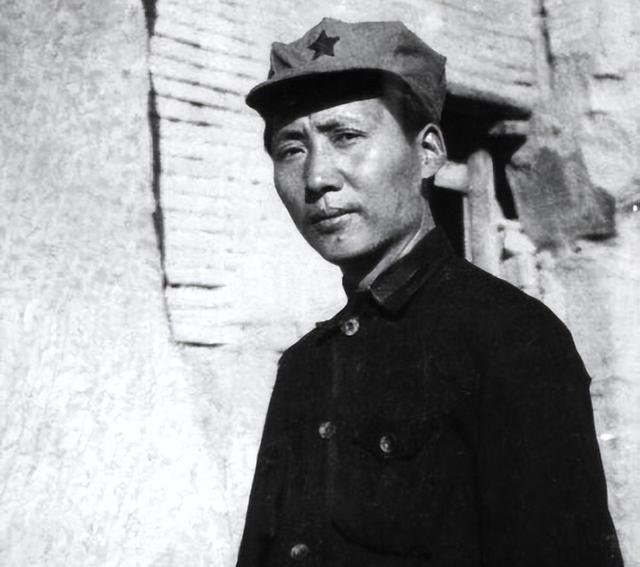参军后的母亲
1936年,母亲已经10岁了。
那时候的旧城村没有中学,只有一个官办的高小,周围四里八乡村子里的孩子们都要走到旧城来上学。
母亲家里穷,正规的学校上不起,后来村里又办了一个短期小学,有点像现在的公益事业,不收学费,专门招收穷人的孩子,母亲这才能够上了学。
那时候,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上旧城村里的正规小学,剩下这帮穷孩子就在这个“义务教育”小学里上课认字。每日只上半天课,不用交学费,男女生合班。
学校里教书的先生也算是那个年月的“志愿者”,母亲说是从北京房山来的两个女老师,大个子的叫房从真,另一个个子矮点,叫段凤亮,两个人都吃住在学校里。
想想那时农村学校的老师也真是不容易,年纪轻轻就不远百里的来到一个荒僻的乡下教一帮四六不懂的农村娃娃,人生地不熟不说,还要自己起火做饭,这肯定能算得上是师德高尚吧。
白天和一群孩子厮混还好说,到了晚上,黑灯瞎火的农村,两个年轻的女老师害怕,母亲就自报奋勇地去和她们作伴。当然,勇敢也是有报酬的,老师给她的好处是每天晚上给自己加课,吃点“小灶”,所以据母亲说,她的数学一直都还不错。
母亲她们上学时已经远离了私塾,用的是民国以后的“文明课本”,她还记得一开始学的是 “人手足刀尺,今年几岁,今天天气好不好”等通俗的内容,现在看起来倒也挺人性化的。
等到后来,母亲认了一些字,就帮着老师教一年级的孩子们,教他们认生字,读拼音,有时还教一加二等于三一类的简单算术题。
姥爷家正好坐落在旧城村的十字街上,院子门口还有个挺大的稍门,也算得上是旧城的“市中心’了。
抗日战争初期,鬼子在冀中农村经常到处“扫荡”,每逢此时老百姓就得外出躲避,俗称“跑反”。有次“扫荡”过后,姥爷一家人返回后看到,自己家里也住过日本人,锅里还剩下一些吃剩的大米饭和锅巴。母亲她们一连几天在外面奔波,饥饿难耐,也顾不得其他,铲下一块就吃了起来。后来她说挺香的,尤其是米饭里面还掺有杏脯,黄黄的很甜。
日本鬼子在姥爷家里还养过马,拉了一院子的马粪。母亲在打扫时发现马粪里面有好些没有消化的粮食粒,人们为了度日,就把马粪里的粮食拣出来用水清洗后再吃。母亲说,那东西老有股子马粪味,怎么洗也洗不掉。可见,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
冀中“五一大扫荡”过后,旧城村成了日军的据点,十字街中央建起了鬼子的炮楼。和姥爷的院子只隔着一家,母亲在房上晒高粱时经常能看到拿着枪站岗的日本鬼子。
有时候鬼子的汽车给据点送来慰安妇,母亲看到过她们从卡车上跳下来,穿着和服一扭一扭的走进炮楼,心里说日本人里头也有长得俊的。
一次,有个高丽(朝鲜)鬼子喝多了来姥爷家里闹事,拿着个棍子砸院门,没砸开就爬墙头上房,跑到隔壁婶子家院子里折腾。所以大姨经常为了躲避鬼子,去到外村的姨姥姥家住。
还有一次有个鬼子喝醉了,闯到邻居家,正巧碰到母亲在哪里玩。他就掐着脖子把她举起来,说:“小孩。”把母亲吓得够呛。幸好那家有人在炮楼里做饭,于是和鬼子说:“小孩子害怕。”鬼子才把她放下来,还掏出一块糖给她,母亲吓得够呛,哪里还敢要糖,赶紧跑回家了。
日本人在村里办了个小学,不用交钱,但是女孩子都不敢上。有个家长找到姥爷家里,让母亲和另一个女孩子结伴去上,最后勉强去了,也就一年左右又不上了。
后来八路军也在村里办了个学校,母亲又哩哩啦啦上了一段。后来她才明白,学校里的两个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叫张浦路的老师发展母亲入的党。她入党后由于投身抗日工作,也就顾不上再上学了。
母亲的叔叔,也就是我的二姥爷,有过两次婚姻,真应了“小白菜”里的唱词,后妈和原来的儿子闹不到一起。我的表舅有些残疾,一只眼看不清东西,平素受二姥姥的虐待,不但自己住在小南屋,吃饭也不让一块吃。
但是表舅找了个媳妇特漂亮,结婚后两口子在外面单过。后来表舅参加了八路军,上午参的军,下午随部队转移时就跟日本鬼子遭遇了,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就这样,表舅的母亲依然比较霸道,烈属的抚恤金不给人家媳妇和孩子,一个人独自占有了,母亲到现在一提起来还忿忿不平。
母亲说抗战初期,旧城村里出去参加抗日工作的只有两个女的,还都是地主出身,以后再也没有出去过的。
1943年,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
日寇为了达到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继“五一大扫荡”后,在1943年又开始实行新一轮的阴谋。他们计划在华北推行所谓“新国民运动”,并决定把冀中9分区辖区内的高阳、任丘两县设定为“突击示范区”,也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家乡。
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专门抽调特务团30分队和“剿共委员会”、“新民会”属下的5 0多名日本特务,经过严格训练后,由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重三郎山崎少佐和他的助手恒尾率领,组成“突击示范队”来到冀中。
他们一伙人自1943年8月开始,在日军63师团66联队137大队的配合下,亲自坐镇高阳、任丘县城,开始推行罪恶的“新国民运动”。
日寇“新国民运动”的目的就是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内的群众和八路军分开,日本侵略者也清楚老百姓与共产党、八路军是鱼水关系,老百姓是水,共产党、八路军是鱼,于是认为只有把“水”掏干,才能把“鱼”捉尽。
所谓“新国民运动”实行的主要办法是:首先强迫“示范区”内的群众背诵“反共誓约”6条,6条的大致内容就是不听从八路军的指示和要求;日伪军问话要如实回答;随时向日伪军提供情报等等。他们认为凡是背不过的或不检举他人就是对日军不满,不是“东亚解放的新国民”,要立即处罚。
在强力推行“反共誓约”的同时,日伪政权还在根据地内的各个村庄组织“联庄会”,建立伪自卫团、情报站等,大搞村村联防,用来监视、封锁、捕捉抗日人员。同时他们还强迫群众在任丘至高阳长达30公里的公路上设置“人电杆”,每隔10米就安排一个“新国民”站岗,整夜防守,以达到监视封锁八路军活动的目的。
1943年8月下旬,山崎及其助手恒尾带领“突击示范队”先期到达高阳,纠集当地日伪头目部署“新国民运动”突击示范的计划。
恒尾首先来到距旧城村几里地的李果庄,强制群众跪在地下背诵“反共誓约”,背不过的,就用刺刀逼着扒房沿,谁掉下来就杀谁。村民齐亭章等4人掉下来了,恒尾狂叫:“大日本皇军到中国就是来杀人的!”说着,将指挥刀往水里一蘸,把4个人的头颅砍下。为了显示残忍,他还把鼻子凑到刀上嗅血腥味道。
旧城村是鬼子的重要据点,也是高阳日寇开展新国民运动的试点。日军把村里人们集合到一块,强迫每个人背诵反共誓约。
为了逼迫群众背诵反共誓约,日寇把旧城的老百姓关在一个大院子里,不让吃饭也不许喝水。八月正是三伏天,大家又热又渴,实在受不了了,连鬼子洗过杀人刀的水都喝下去了。
姥姥年纪大了,是个文盲,加上记性不好,对着那么多条文实在是背不出来。有个鬼子上来就是一刺刀,把姥姥肚子上划了一道口子,幸亏大家抢救及时没出生命危险。
母亲有个本家叔叔在村里当日伪的保长,平时没干过什么坏事,经过他的斡旋,才把人们放了出来。
姥姥回到家里,伤口感染发炎化了脓。有天晚上姥姥半夜疼醒了,推推身边的大姨,说你看看我肚子上怎么有虫子在爬,大姨起身点上煤油灯一看,原来是肚子上伤口里的脓水流出来了。后来经过村里土医生的治疗,家里人精心照料,姥姥才算闯过了鬼门关。
经过这次磨难,更加坚定了母亲参加抗日的决心。她一边上学,一边教小学一年级,向学生们宣传抗日。参加抗日工作以后,上级还派她去参加了区里在崔庄、辛桥附近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回来后在村里当上了妇女大队长,到家家户户去进行宣传,动员妇女们出来参加生产和抗日活动。
当时村里学校的老校长是母亲一个远房当家子,有投敌的倾向,母亲配合游击队把他抓出去进行了教育,回来后改正自新,不再做坏事了。
由于母亲的算术好,后来还担任过村里的粮秣会计,负责管理村里抗日政权的财政开支。
后来,旧城村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母亲的老师张浦路担任党支部书记,不但发展她入了党,还教母亲学习射击。母亲曾经自豪的告诉我,她用那种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的独撅开过一枪。
由于过去的旧城村党支部书记实行了“关门主义”,很长时间村里党组织一直没有发展党员,全村就只有4个党员,不但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后来还被开除出党了。
学校的张浦路老师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后,党组织活动多了,党员也发展的多了。母亲就是在这期间入的党,入党后她听说小学同学们也大都入了党。但是当时党组织还处于秘密活动,党员之间谁和谁都不通气,我的二舅参加了武委会,也是党员,但和母亲竟然互相都不知道。
也是在这一年,村里支部书记张浦路老师征求她个人意见,说部队上的学校在招人,去部队学校可以深造,有发展,你想不想去?在母亲同意后就到区里开了一封介绍信,走时还不让和家里人说,于是母亲自己打听着来到了驻扎在任丘县石门桥的抗大二分校上学。
就这样,母亲开始了她的军旅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