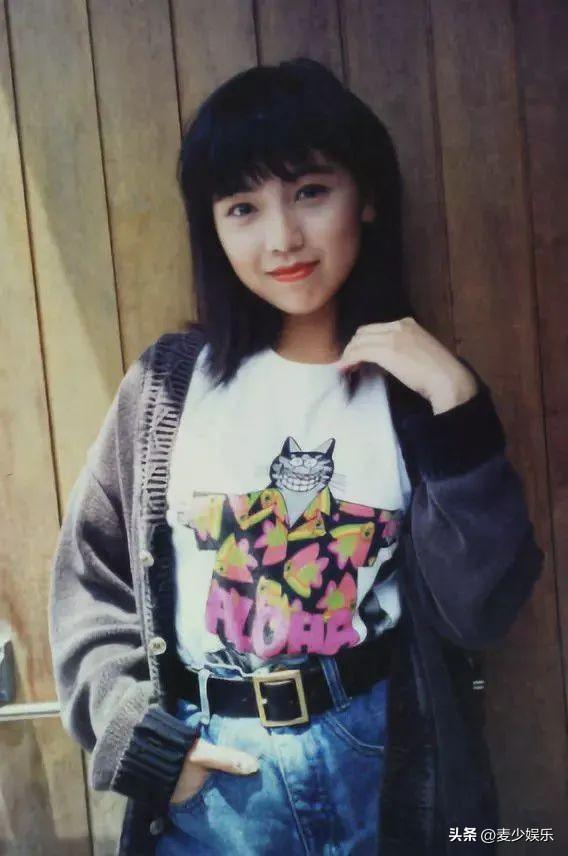洪启,词曲作家、诗人、歌手。1973年出生于新疆和田,1992年开始音乐创作。曾发表唱片《红雪莲》《阿里木江,你在哪里?》《九棵树》《谁的羊》《黑夜的那颗心》及《洪启自选辑1992--2011》。
2021年,民谣歌手洪启时隔六年后,重返深圳生活。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深圳定居。
曾经,作为中国民谣的代表人物,洪启来深圳,是为了创作和演出。
而如今,他来深圳主要为了两件事:一是咖啡,二是《山海经》。这两件事都和音乐有关。
两次来深,他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对于艺术和金钱的关系,已经有了新的理解……
洪启说过,自己有三个“故乡”。第一个是新疆,第二个是北京,第三个是深圳。
作为一名新疆人,洪启的音乐是代表新疆的音乐。1992年,他的歌曲《红雪莲》轰动一时,1997年创作的《阿里木江,你在哪里?》也被广为传唱……这些音乐,都与新疆有关。
红雪莲洪启 - 谁的羊

而北京,是中国音乐产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如洪启一样理想主义青年的“大本营”。2014年第一次来深以前,洪启一直在北京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他创作的一首知名歌曲《我想,我想》,表达的就是他在北京生活阶段的感受。
但是,洪启也热爱着深圳。他说:“深圳给我的感觉就是‘不颓废’。深圳人是清新的,有朝气的。所以我一直非常喜欢深圳。”
他第一次来深圳,是零四、零五年左右的事情。当时,他制作唱片《红雪莲》时候合作的歌手高樱住在深圳,和他合作的许多乐队乐手都在深圳发展。借着演出的机会,他终于实现了“来深圳看一看”的愿望。
关于深圳音乐,洪启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十分“商业”。当年,北京的艺术家还抱有“以商业为耻”的观念,而深圳,却早就“以商业为荣”。
那时深圳人的夜生活,是“酒吧听现场”的模式。和他认识的乐手,为了赚钱,居然一个晚上能跑三场甚至四场演出。而作为佛系青年,洪启一般一晚演出一场,最多就跑两场。
他还记得当年巴登街最火的根据地酒吧,本色酒吧等等,都主要通过商业包装来吸引听众。当然,那一批深圳的听众能对表演者保持尊重,也有一定的审美基础。
尽管一直以来,深圳人崇尚“商业”,以搞钱为荣,但是洪启的民谣歌曲,在当时的深圳依然有大量受众。作为新疆音乐代表人物,他的表达方式是纯粹而质朴的,但是其中包含的审美却又是能被人广泛理解的。
这或许与时代有关。洪启形容他们那一代人是“钻洞”的人——他们的前半截身子已经钻进了网络的世界,战战兢兢地窥探着关于网络的一切,而后半截身子却还留在了过去,留在了那个属于磁带和唱片的世界。
曾经的深圳,在音乐方面是“二元的”。它一方面是世俗的,另一方面又是有情怀的。许多对音乐抱有情怀的深圳人,既会在白天会拼命工作,也能理解洪启的音乐,在夜晚的酒吧里安静地聆听洪启的歌声。
然而洪启说:“现在,这些人基本都离开深圳了……”

长久以来,深圳的音乐产业是“商业”的,也是“地下”的。许多从深圳走出的音乐人,曾经都有在深圳酒吧驻场表演的经历。他们的愿望就是一炮而红,将来能够去北京发展。
然而,洪启却反其道而行之。201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从北京搬家到深圳生活。
那时洪启的态度与一般的来深“打工人”不一样。对一般人来说,深圳是一个“搞钱”的地方。洪启当年却不是为了搞钱而搬来深圳。当初他来深圳发展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在北京呆太久了“像闷在罐子里”,就是想换个环境。对他来说,深圳这座快节奏的城市,就像一根鞭子,可以鞭策他进行艺术创作。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他的目的达到了。在深圳生活的那段日子,他的创作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比北京时期更加丰富。另外,他在深圳大大小小的演出也是接连不断,他曾经很自豪地说过“自己基本把深圳所有能演出的地方都演了个遍”。
不过,洪启在深圳的生活也遇到了不少阻碍。
首先,深圳生活的快节奏也意味着深圳音乐审美的快餐化。
如今的年轻人,听音乐的模式是“碎片化”的。他们用手机就可以随意地听歌,根本没时间听一整张唱片。另外,比起去酒吧听驻唱的歌手唱歌,蹦迪时候听得简单粗暴的音乐也更能解压。
然而,事实上,最纯粹质朴的音乐就是“最难”的音乐,因为不论对于创作者还是聆听者来说,歌曲中包含的美学需要用心去体会。在一个不再关注音乐内涵的时代,洪启的音乐在以年轻人居多的深圳注定会变得十分小众。
此外,对于艺术家来说,深圳的生活成本也实在是过于昂贵。
“在北京还可以住在六环。但是在深圳,想过上文艺的生活,假如只搞艺术创作的话,连房租都交不起。”这就是洪启在深圳生活两年的感受。
由于经济压力,2015年,洪启离开了深圳,到了成都生活。不过,即便离开深圳,他还依然挂念着深圳。
2019年,他与打工诗人郭金牛合作,创作出了唯一一首以深圳为背景的音乐《在外省干活》。或许,这首歌也反映了他的心境:想做一个深圳“打工人”。
还记得《在外省干活》发布后,洪启在深圳的本色酒吧举行过一场小规模演出。
当时,台下稀稀落落地坐着几批听众。其中有个姑娘一边看手机百度搜索,一边扯着嗓子喊:“唱《阿里木江,你在哪里?》!”
还有个姑娘看着手机的搜索结果喊:“唱《红雪莲》!”
在一片嘈杂中,洪启开口唱歌。那天,洪启的嗓子状态不够好,台上的他一直憋足了劲唱歌,歌声却被鼓声贝斯声淹没。
台下的年轻听众们则是一脸茫然。他们不仅仅听不清这位歌手的歌声,也无法理解他的歌声中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故事与内涵。
“唉,不唱了,不唱了……”演出结束走出本色酒吧后,洪启一直无奈地摇头。
对洪启来说,现在的深圳早已是今非昔比。

在深圳生活的经历,让洪启意识到:搞钱和搞艺术其实并不冲突。
作为艺术家,他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这是个所有人都需要用钱来生存,每个人都必须搞钱的时代,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这一点我绝不矛盾也丝毫不纠结。来深圳,就是搞钱!文化永远是个好生意。”
从文化产业出发,是他现在的思路。毕竟,与其让艺术做消费的附庸,不如让艺术直接拉动消费。
从唱片时代到网络时代,当下年轻人对待音乐的态度已经变了。曾经的深圳人买唱片,去酒吧听歌,追逐的是聆听音乐本身;反观如今,更多的深圳人不再直接为艺术消费,而是更加看重艺术的附加产物。
“你去深圳各大创意园看看,就会发现,深圳的文艺青年,是看不到特征的。”对于深圳的“文艺”现状,洪启如此评价,“但是深圳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又很强,愿意为艺术买单。”
“成都的咖啡店就不一样了,从举手投足之间,你就能从顾客中辨别出哪些是成都的文青。”洪启十分欣赏成都的市井文化与生活态度。他现在的目标,就是将成都的文艺氛围融入深圳。而咖啡,就是“连接点”之一。
除了咖啡以外,洪启目前专注的另一项文化产业是做《山海经》相关的音乐。
《山海经》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本原经验。现代科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艺术,但是也激发人类反思艺术。艺术的最终目标,或许就是让人类回归本原。
“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读经’。所谓的‘经’,其实就是‘经验’。《山海经》也是‘经’,值得我们去仔细品读。”他如此解释道。
他认为,自己从代表新疆文化的歌手,转变为《山海经》音乐文化的推手,正是因为时间的沉淀。如今四十八岁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愿望。
对于自己如今在深圳的生活,洪启感到十分满意和惬意。深圳有山有海,在深圳搞《山海经》的文化产业,再适合不过。
他曾经在自己的日志中写下过:“我的窗外有海,那是深圳湾;我的背后有山,那是安托山。山海里有人间所有的情,在自古以来的每一天每一刻里。”
从大部分深圳人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话只会被理解为一段房地产广告词。
然而对于艺术家洪启来说,它却意味着又一段深圳诗意生活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