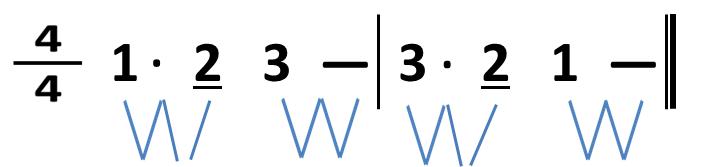(节选自《敞开:人与动物》/吉奥乔·阿甘本著/蓝江译)
甚至云雀也看不见敞开。
——马丁•海德格尔
在课程中,关键在于将“敞开”的概念确定为存在物与世界的诸多命名之一,就像杰出(kat' exochen)的命名一样。十多年之后,即“二战”全面爆发的时候,海德格尔又回到了这个概念,并追溯了概念的谱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概念明显是从《杜伊诺哀歌》的第八首哀歌所引出的,但在被用作存在之名(“在敞开中,所有存在物都得到了解放……敞开就是存在本身”)时,里尔克的用词经历了根本性的颠覆,海德格尔想通过一切方式来强调这一点。因为在第八首哀歌中,是动物(die Kreatur)用“它的眼睛”看到了敞开,这完全不同于人,人的眼睛反而“向后转”,在他周围设置了“陷阱”。但人面前总是有世界——总是仅仅“面向反方向”,而不会进入外部的“纯粹空间”——动物却在敞开中运动,“任何地方都不置臧否”。
对人与动物等级关系的颠倒,正是海德格尔所追问的问题。首先,他写道,如果我们将敞开视为哲学中所说的无蔽(aletheia)的名称,即对存在遮蔽的去蔽,那么这里就不是真正的颠倒,因为里尔克所引出的敞开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试图归还思想的敞开毫无共同之处。“里尔克的敞开并不是揭示意义上的敞开。对于无蔽,里尔克并不比尼采知道得更多,也没有怀疑过任何东西。”在尼采和里尔克那里,正是对存在的遗忘起着作用,这是“19世纪生物主义的基础,也是精神分析的基础”,其最终后果就是“动物怪异的人形化和与之对应的人的动物化。”只有人,事实上,只有本真思想的根本性的凝视,才能看到敞开,命名了存在物无蔽状况的敞开。相反,动物看不到这种敞开。
因此,动物不仅不能在这种封闭中运动, 也不能在遮蔽中展示自己。动物被排斥在无蔽和遮蔽的冲突的基本领域之外。而这种排斥的标志就是没有动物和植物“拥有词语”。
在这里,海德格尔用了一页极为凝练的文字,清晰地提出了动物环境和人类世界的区别,而人类世界恰恰就是1929—1930年课程的核心:
对于动物而言,它处在与它的食物、猎物、它自己同类的其他动物的关系中,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关系不同于石头与它所依赖的大地的关联。在植物和动物的生物圈子里,我们发现了某种特殊运动的萌芽,借助这种运动,生物被“激活”,进入一种兴奋状态,在这种兴奋的基础上,它将其他东西囊括在它所萌生的圈子里。但是,植物或动物的运动或兴奋都无法用某种方式让生物获得自由,也就是说,被刺激的东西无法让刺激性的东西如其所是,甚至在导致兴奋状态时也不行,更不用说在兴奋之前和毫不兴奋的时候。植物与动物依赖于某种外在于它们自己的东西,却未曾“看到过”内部或外部,也就是未曾在自由存在中看到过无蔽状态。石头和飞机一样,在面对太阳时,都不能像云雀一样欢呼雀跃,但是甚至云雀也看不见敞开。
云雀(在我们的诗歌传统里,云雀象征着最纯洁的爱的冲动——例如,伯纳特•德•文塔顿[Bernart de Ventadorn]的《我看见云雀飞翔》[Lauzeta])没有看到敞开,因为即便在那一刻,它以最深的决绝冲向太阳,阳光也让它盲目。云雀不能将太阳揭示为一个存在物,也无法在太阳的遮蔽中以任何方式来展示自己(正如尤克斯考尔的蜱与其去抑因子的关系)。正是因为在里尔克的诗歌中,“生物(植物与动物)的奥秘和历史之物的奥秘之间的根本界限”既不能被体验,也不能被追问,所以诗歌的言辞无法做出“建构历史的决定”,而诗歌不断地被暴露在“让动物无拘无束地与毫无保留地化身成人”的风险当中,甚至将动物凌驾在人之上,并以这种方式制造了某种“超人”。
那么,如果问题在于界定动物与人的边界(区别与相似),或许在1929—1930年的课程中,这个因素被用来确定动物环境的悖论性存在论状态。动物同时是敞开和未敞开——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既非此,亦非彼,在非揭示状态中敞开。一方面,在它的去抑因子当中,以非比寻常的强烈程度,让自己沉浸和迷失于其中;另一方面,它绝对没有将占据着它、让它沉浸于其中的东西揭示为一个存在物。海德格尔在这里似乎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想起了奥秘知识——或者说非知识——的悖谬。一方面,沉浸有着比人类知识更具魔力和更强大的敞开,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揭示自己的去抑因子,它被封闭在一个蒙昧的总体当中。这样,动物的沉浸和世界的敞开,就像否定神学和肯定神学一样,彼此相关,它们的关系模糊不清,仿佛一个神秘的线索将奥秘的黑夜和理性知识的白昼同时对立和结合起来。
或许这里心照不宣地反讽地指向了这种关系,海德格尔在某一点上感觉到需要用奥秘联盟(unio mystica)最古老的象征来说明动物的沉浸,即飞蛾扑火,火吸引着蛾,但蛾直到最后都顽固不化地不知道这一切。在这里,这个象征是不充分的,因为按照动物学家的说法,蛾看不见的,正是去抑因子的非敞开,即蛾自己还沉浸于其中。而奥秘知识在本质上就是非知识的体验,也是这样的遮蔽的体验,动物不可能向非敞开展示自身,它仍然被排斥在去蔽和遮蔽的相互冲突的基本领域之外。
然而,在海德格尔的课程里,动物的贫乏世界多次被倒转为一种无法比拟的财富,据此,动物在世界上是贫乏的这个论点会遭到质疑,因为这仿佛是将人类世界过度投射到动物身上。
问题的麻烦在于,在我们的追问中,我们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贫乏世界和动物的圈子,最后我们说得就仿佛与动物相关的东西……是一个存在物,仿佛这个关系是一种向动物展现出来的存在论关系。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这迫使我们走向这样一个论点,即只有通过毁灭性的观察,才能接近生命的本质,这并不意味着,在同人的此在相比较的时候,生命是更低级或者处在较低层次上的东西。相反,生命是拥有敞开财富的领域,人类世界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当这个论点似乎要被毫无保留地放弃,动物环境和人类世界似乎要合并为一个彻底异质的总体时,海德格尔通过参考《罗马书》8:19中的著名段落,再次提出此论点,在这个段落中,圣保罗唤醒了造物渴望救赎的祈盼,这样动物的贫乏世界现在似乎反映了“内在于动物性本身的问题”:
那么,我们必须敞开这种可能性:对世界本质的本真的和显然是形而上的理解迫使我们认为,动物并不拥有世界就是完全不相干,即在动物这样的存在方式中找到一种贫乏。生物学完全不认同这些东西,并不是形而上学思考的反例。或许只有诗人偶然谈到了这个论断,即不能任由形而上学飘荡在风中。最后,要理解圣保罗(《罗马书》8:19)文字中涉及“造物的热切渴望”(apokaradokia tes ktiseos)的某些东西——正如《以斯拉记》(7:12)第四章所说,在永生中,其道路变得狭窄、阴郁、无聊——基督教信仰不是必要的。发展作为内在于动物性本身的问题的动物的贫乏世界,并不需要任何悲观论调。由于动物因其去抑环境而敞开,沉浸之中的动物在本质上持守着某种并非它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可能向动物展示为一种存在物或者非存在物,而是因为动物的去抑……为动物的本质带来了根本性的断裂(wesenhafte Erschutterung)。
在圣保罗的书信对弥赛亚救赎的观点中,这种渴望迅速地让造物接近了人,在非揭示状态中暴露出来的动物经验中的根本性断裂,大大削减了该课程标示出来的人与动物之间、敞开与非敞开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贫乏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动物在其中感受到了自己的非敞开)已经具有了一个策略性的作用,保证了从动物环境到敞开的过渡,从某个角度来看,作为动物本质的沉浸“是一个适当的背景,可以由此来区分人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可以回到对烦的讨论(他课程的第一部分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将动物的沉浸和他称为“深度之无聊”的基本情绪(Stimmung)出乎意料地协调起来:
我们会看到,这种基本情态和与之相关的一切,是从我们所谓的动物性的本质,即沉浸区分出来的。这个对照对我们来说将是决定性的,作为动物性本质的沉浸显然非常近似于我们界定为深度之无聊的根本特征,近似于我们描述为在总体的存在物之中此在被禁锢的魅力(Gebanntheit)。当然,可以看到,两种基本架构最紧密的近似性不过是一种表象,两者之间有一道任何中介都无法跨越的鸿沟。在那种情况下,二者的根本差异,因而也是世界的本质,对我们来说会变得异常清晰。
在这里,沉浸表现为一种基本情绪,在这种情绪中,动物并没有敞开自己,正像此在一样,在一个世界上,却在暴露中绽出地脱离自己,这种暴露切断它自己所有的纤维。唯有我们体验到与这种没有去蔽的暴露“最紧密的相似性”——即便是表面上的相似——我们才能理解人类世界。或许并非这样的情况,即存在物和人类世界已经被预先设定好,以便通过抽离——即通过“破坏性的观察”——就能触及动物。或许恰恰相反,或许这更为真切,即人类世界的敞开(因为它最初也是对去蔽和遮蔽之间根本冲突的敞开)只能通过施加在动物世界之上的非敞开的操作来实现。这个操作的地方——在这个操作中,人在世界上的敞开和动物向其去抑因子的敞开似乎暂时重合了——就是无聊。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许文静
图源 | 网络
欢迎合作 | 投稿
pcsdpk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