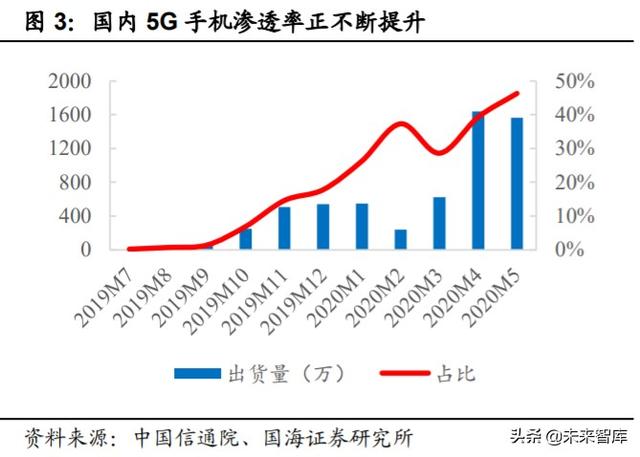《礼记·祭义》篇载宰我问鬼神之义,孔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
所谓“报本反始”,即传统祭礼精义之所在。儒学经义的逻辑性是极其严密和完整的,人间秩序由家庭为起点而推演之,社会之秩序方能建立、邦国之文明方能推演。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或曰中国文明的要义皆本乎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和儒学义理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中心,这也更是抟系中国民族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论语·学而》篇记载曾子之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指的是丧礼,追远则是就祭礼而言。此二礼的形式及目的虽有差别,但本于人的真情和伦理孝思却殊无二致。祭礼除了寄托和表达对故去亲人的追思怀念之外,更有教育后人的重要意义。对祖先的祭礼,正是在具体形式化的仪节中,让人们潜移默化的接受了许多应有的生活观念、以及生命意义的体认,其所寄托的德目之教育,实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方式之一。而《诗经》里的颂诗部分,也实际正是古代宗庙祭祀中对祖先赞美的篇章。
古者庙则有主以依神,祭则有尸以像神。由于已故亲人毕竟处于渺茫之间,是以古代宗庙之祭有“主”的设计用以供神灵的栖息和祭祀的对象。是以许慎《五经异义》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无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钱宾四先生《论古代对于鬼魂及葬祭之观念》一文述曰:
今考春秋以来,中国古人对于魂魄之观念。《易·系辞》有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小戴礼记·郊特牲》篇谓:“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此谓人之既死,魂魄解散,体魄人土,而魂气则游飏空中无所不属。《小戴记·礼运》篇有曰:“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熟,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此处魂气又改言知气。时人信人既死,其生前知气(即魂气),则离体飘游。故升屋而号,呼而复之。而魂之离体,则有不仅于已死者。故宋玉《招魂》篇云:“魂魄离散。”……则古人谓人既死,魂即离魄而游,其事岂不信而有征。……人死魂离,于是而有皋号,于是而有招魂,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像神,凡以使死者之魂得所依附而宁定,勿使飘游散荡。春秋以后,尸礼废而像事兴。主也,尸也,像也,此皆所以收魂而宁极之也。
“主”又称为“神主”或“木主”,先秦即有之。《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周礼•春官·司巫》云:“祭祀则共匰主。”郑注:“匰,器名。主,谓木主也。”贾疏:“云‘匰,器名’者,《说文·匚部》云‘匰,宗庙盛主器也’。《广雅·释器》云‘匰,笥也’,凡主藏于庙中,以石为室,谓之祏。《说文·示部》云‘祏,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御览·礼仪部》引《五经异义》亦云‘《左氏传》曰,徙主祏于周庙’,言周庙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云‘主谓木主也’者,《说文·宀部》云‘宔,宗庙宔祏’,经典通作主。木主谓桑木、栗木也。”孙诒让《周礼正义》案曰:“郊宗石室,谓配郊及宗祀明堂之远祖在坛墠之上者,其主实于石室,藏之大祖庙也。其实五庙二祧之主,亦藏于石室,当祭时出主于室,则以匰盛之,以授大祝,不敢徒手奉持,恐亵神也。匰即筐笥之属,每祭则司巫共之。逮祭毕,主复归于室,即去匰别藏之,主盖不常盛于匰也。”
《公羊传•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练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主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天子长尺二寸,诸侯长一尺。虞主用桑,期年练祭,埋虞主于两阶之间,易用栗也。”孙诒让《周礼正义》云:“主之形制,《谷粱·文二年》范注及杨疏引徐邈说,并与何同。”孔颖达《礼记·曲礼下》疏引《白虎通》说:“所以有主者,神无依据,孝子以继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终,又与人相似也。盖记之为题,欲令后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宗庙祭祀是以“主”为祖先“精气”之所藏、灵魂之所依附的。换言之,“主”,即象征着死去祖先的灵魂之所在。
根据上文所引,先秦神主式样约略可知,其神主亦有两种之别,即:一、虞主(丧主),以桑为之,死者埋葬之后所制作,根据礼的分类,此为凶礼之用;二、练主(吉主),以栗为之,小祥一周年练祭、即死后第十三个月时制作,根据礼的分类,此为吉祭。另据何休《公羊传·文公二年》注引《仪礼·士虞礼记》所说“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谥之,盖为禘袷时别昭穆也”,可知其二者之别。宗庙祭礼属于吉礼,是以后世宗庙的神主,以练主(栗主)为是。
唐杜佑《通典·卷四八》中记载了先秦至汉唐之际的神主规制:“(先秦)主之制,四方,穿中央达四方。天子长尺二寸,诸侯一尺,皆刻谥于背;《汉仪》云,帝之主九寸,前方后圆,围一尺。后主七寸,围九寸。木用栗;晋武帝太康中制,太庙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与尺二寸中间,木以栗;大唐之制,长尺二寸,上顶径一寸八分,四厢各剡一寸一分。上下四方通孔。径九分。玄漆匮,玄漆趺。其匮,底盖俱方,底自下而上,盖从上而与底齐。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寸。以光漆题谥号于其背。”《通典·卷一三九》“虞祭”条又载《开元礼》之说,记唐代制度云:“先造虞主,以乌漆匮匮之,盛于箱,乌漆趺,一皆置于别所。(虞主用桑,主皆长一尺,方四寸,上顶圆,径一寸八分,四厢各刻一寸一分,又上下四方通孔,径九分。其匮,底盖俱方,底自下而上,盖从上而下,与底齐。其趺方一尺,厚三寸。将祭,出神主置于座,其匮安于神主之后。四品以下无。)”匮,即用于收藏木主的黑漆箱子,亦即《周礼·司巫》所说的“匰”的演变形制。由此可知,神主的式样,大体经历了由正方体向前方后圆、长方体等不同的形制的演变过程。而先秦之时的神主还要在中央部位穿凿一孔,用以祖先灵魂的出入或依附。而唐代的神主已极为接近后世神主的式样,换言之,后世神主之形制即由唐代制度而来。
《通典·卷四八》又引许慎《五经异义》云:“后汉许慎五经异义: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说,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无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结茅为菆。慎据《春秋左氏传》曰:‘卫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为主。’郑驳云:‘少牢馈食,大夫祭礼也,束帛依神;特牲馈食,士祭礼也,结茅为菆。……礼,大夫无主而孔独有者,或时末代之君赐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诸侯不祀天而鲁郊,诸侯不祖天子而郑祖厉王,皆时君之赐也。’”据郑玄之说来看,古代只有天子诸侯才有“主”之设,大夫及士则无之。杜佑则不赞同此论,认为“经传未见大夫士无主之义,有者为长。”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亦明显反对此说:“郑《祭法》注谓大夫无主,《通典·吉礼》及《左传·哀十六年》孔疏引《五经异义》:‘《公羊》说,大夫士无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结茅为菆。许慎据《左传》卫孔悝反祏于西圃,大夫以石为主。’郑驳从公羊说,谓‘大夫无主,孔悝反祏为所出公之主。’案:《说文》祏字注引别说,亦云‘大夫以石为主’,今考祏为主室,非即以石为主,许义不足据。然谓大夫士有主,则于义得通。《通典》又引徐邈及魏清河王怿议,并谓大夫士当有主,亦从许说也。”
同时,即使真如郑玄所说,古代礼制中“主”只为天子诸侯所有,而后世卿大夫士供祖先灵魂所依附的神主则也有了“变通替代品”——“神版”的出现。《通典·卷四八》“卿大夫士神主及题板”条又记载了西晋开国功臣荀勗的祠制云:
晋刘氏问蔡谟云:“时人祠有板,板为用当主,为是神坐之榜题?”谟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礼之奉庙主也。主亦有题,今板书名号,亦是题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长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书讫,蜡油炙,令入理,刮拭之。”
再至宋代,程伊川先生云:“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理会。豺獭皆知报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养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旧尝修六礼,大略家必有庙,庙必有主。”(《近思录·卷九》)程子此处所倡言之“家必有庙,庙必有主”,实为中国礼制史上一划时代之大事,更为后世祠堂的普及做好了“准备工作”。私庙及神主,由先秦而至伊川,此乃天子诸侯公卿之礼制,庶士庶人则无,即便就唐制来看,亦唯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方可于其私庙设立神主。朱子云:“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益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朱子语类·卷二十四》)“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在坚守礼“义”这一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损益,正是礼之本义,更为程朱礼学思想。程子非但倡言修庙立主,更依据唐以来的形制,为后世设计了神主式样制度,后来朱子将此形制记入《家礼》,成为宋代以后中国及东亚泛儒学文化圈国家的共同范式。四库本《二程文集·卷十一》载:
作主式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于时月日辰。趺方四寸,象岁之四时。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为首,寸之下勒前为颔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后。前四分,后八分。陷中以书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陷中长六寸,阔一寸。一本云长一尺。合之植放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窍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之三分之一,谓圆径四分。居二分之上。谓在七寸二分之上。粉涂其前,以书属称,属谓高曾祖考,称谓官或号行,如处士秀才几郎几翁。旁题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赠易世,则笔涤而更之。水以洒庙墙。外改中不改。
朱子对伊川的神主设计极为推崇,并作为《神主式》列入《家礼》卷首。朱子赞伊川曰:“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开窍处,皆有阴阳之数存焉。信乎其有制礼作乐之具也。”(《朱子语类·卷九十》)根据伊川《作主式》原注“周尺(古尺)当今之省尺五寸五分弱”,朱子《家礼》卷首图《尺式》亦载“神主用周尺”,据此换算,即一尺23.1厘米。由此可知,包括底座在内的木主整体高度为27.7厘米,宽度6.9厘米。
朱子《家礼图》中的神主式样:
明代《性理大全》依据朱子《家礼》所载神主式样:
换算后程子所制神主式样应为:
今存民间神主式样:
由明讫清,伊川神主之制随着朱子《家礼》的推广得到广泛普及,后世民间常行式样,莫不本乎程朱之说。清人朱彝尊亦云:
涑水司马氏、伊川程氏定为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时,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准此。(《曝书亭集·卷三三》)
兹考前人之文,整理神主作法如下:
作神主之法:
神主之造法,以木为之,元方四寸以象四时,高一尺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三旬,厚十二分以象日之时。神主有内外之函:
外面式:
内函式:
题主之法,内外字须单数,出“生老病死”。若遇生遇老,皆可用爵高者。
1、朝廷赐谥,用朱漆金字。大夫以下无谥,书皇朝,或赐进士、或敕封、或诰赠、或待赠:
举人称向进士,贡生称岁进士,生员称郡庠生或邑庠生,监生称太学生。
2、爵卑者用乌地绿字,士庶用粉底墨字题之:
3、若早亡子幼,题曰:
俟子长成,婚娶之日方改为“考妣”称公及孺人。
(今按,自古凡婚祭之事,礼有摄盛之习,良有以也。是以若今之人所造祖先神主,无论功名与否,倘以朱漆金字者,似亦不当谓之以违礼也。)
4、妻题夫主。妻题夫主曰皇辟。皇辟者,君也。妻则自称未亡人。夫题妻主曰细君,细君者,贤助也。
凡神主,有诰封官职者先填。其次接头衔、考妣。再次某号某府君夫人云尔。
“显”者,有功名者用之。“先”者,士庶用之。
下列几例:
1、承重曾孙主曾祖父母丧主式:曾祖严某谥老太府君之灵位、曾祖慈某太老太君之灵位;先曾祖考某谥老太府君神主(之神位)、先曾祖妣某太老太君神主(之神位)。
2、承重孙主祖父母丧主式:祖严某谥太府君之灵位、祖慈某老太君之灵位;先祖考某谥太府君神主(之神位)、先祖妣某老太君神主(之神位)。
3、子承父丧式:严亲某谥府君之灵位、慈亲某太君之灵位;先考某谥府君神主(之神位)、先妣某太君神主(之神位)。
4、有功名式:显考清邑庠生某谥府君之神位、显妣清例赠孺人某太君之神位;某职头衔显考字某某府君神主、例(应)赠孺人显妣某太君神主。
5、内函另式:
附:传统题主仪
行成主礼。鼓初严,鼓再严,鼓三严。大吹,细吹,合吹。奏乐。鸣炮。介宾引大宾升堂,行相见礼。大宾至盥洗所,盥洗毕,授巾。整冠。束带。升公座。介宾各就位。孝子等众拜大宾前,求鸿题。四拜四兴,入帏捧主出堂。至大宾前,跪,拱主。左介宾接主,安主,去魂帛。启椟,出主,卧主,分主,拂主,送大宾前。右介宾染朱笔,授孝子。孝子接笔,拱笔,求大宾鸿题。左宾接笔,送大宾,大宾接笔,面东向,受生气,题主。先题粉面,次题函中,卧笔。右宾染墨笔,授孝子。孝子接笔,拱笔,求大宾墨笔增辉。左宾接笔,送大宾。大宾接笔,盖主。先盖函中,次盖粉面,卧笔,读主,祝主。右宾起立,合主,树主,入椟,合椟,覆魂帛,授孝子。孝子捧主,起,至安主所安主。孝子复位,拜谢大宾介宾。四拜四兴。礼成。
,